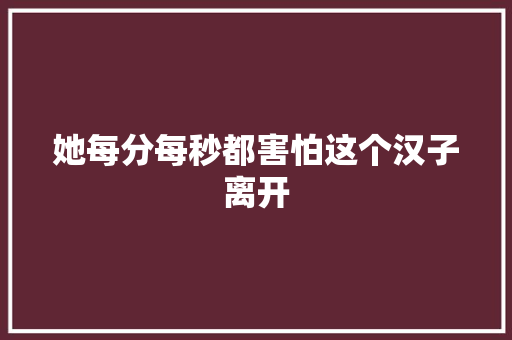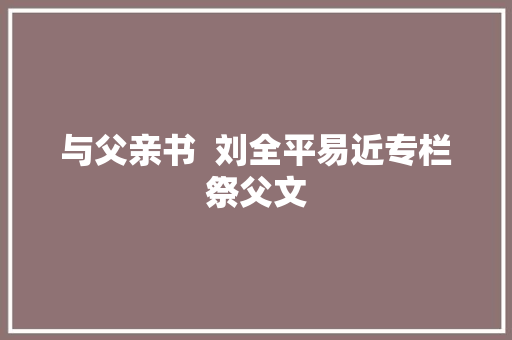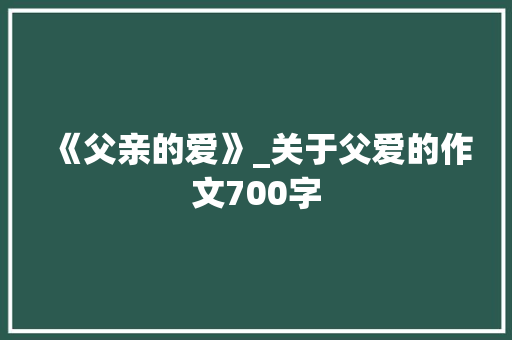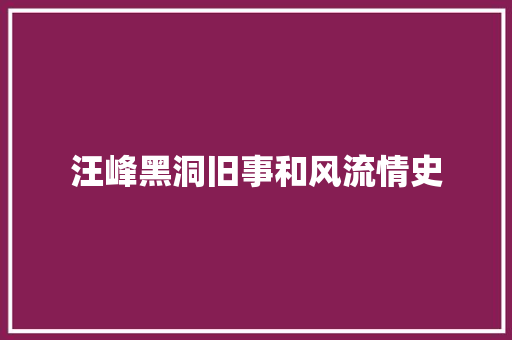文:绻绻
我生在80年代,那是一个大时期。

那时的父亲是一名民办西席,在村落里有一定的身份和地位,这是我的骄傲,也是略大一些时我娇纵和跋扈的后盾。
一九八四年 庄稼还没收割完
女儿躺在我怀里 睡得那么甜
今晚的露天电影 没韶光去看
妻子提醒我 修修缝纫机的踏板
来日诰日我要去 邻居家再借点钱
孩子哭了一整天呐 闹着要吃饼干
蓝色的涤卡上衣 痛往心里钻
蹲在池塘边上 给了自己两拳
这是我父亲 日记里的笔墨
这是他的生命 留下留下来的散文诗
——许飞《父亲写的散文诗》节选。
影象里,儿时的父亲爱穿军绿色的衬衫,会在衬衫口袋里插两支钢笔,一支蓝色的,一支赤色的。
他离开我有十二年了,音容笑脸犹在,恍若隔日。
父亲很激情亲切,村落里人都尊敬他,逢年过节总会送来各种各样的礼物。父亲会将这些礼物打乱,再整理好,然后让我挨家挨户回礼。
我总是在回礼时留在对方家里用饭,儿时的我,总是陵暴人,现在想起来,无比汗颜。
父亲会拉二胡,夏夜时,他会在院子里拉,我总蹲在他身边看。
他特殊心爱那把二胡,不让我碰,他乃至都没有拿到过学校,更没有在学校拉过。
就像他明明会弹风琴,唱歌也很好听,可从来没有教过音乐课一样。
有一天我恼了,把父亲的松喷鼻香藏了起来。
后来,我就再没听过他拉二胡。
那把二胡也就顺理成章成了我的玩具,不用傻到等他去世后再给我。
后来我才觉醒,他的故事,跟他的二胡一样,在我这里断了弦。
我挺恨那时的自己。
儿时陪着父亲下地干活的时候,他会给我编一个大大的蝈蝈笼子,让我去捉蝈蝈。
会把地里的植株先容给我,也会跟我讲什么样的庄稼收成什么样的粮食,却不让我帮忙干农活。
他干活渴了,会大声喊我一起喝水,会把带出来的干粮大半给我吃。
那时家里养了一头玄色的老驴,是农忙时,是我家仅次于我父亲的劳动力。
老驴的动作很慢,力气很小,拉空车的时候,我会在父亲铺满车厢的垫子上躺着看天空,问父亲各种各样的问题,会指着云彩愉快大叫:“爸爸,你快看,那朵云彩像不像咱家老母鸡?”
这个声音我已经喊不出来了,只由于他再也听不到了。
夜里驴车上会装满收割的庄稼,我趴在庄稼垛子上,老驴拉着吃力,父亲会帮着一起拉,他脚步沉稳,手臂上的肌肉黝黑健硕,这时我会调皮的喊“驾……驾”。
父亲会给我讲历史,讲地理,他见告我,山的那一边没有山。
他会拍动手给我唱《十五的玉轮》,唱《渴望》,也会拿着身体唱《智取威虎山》,这些声音犹在耳边,只是再不见“曲中人”。
父亲这生平很幸福,他说他没有遗憾,可我明明看到了他混浊双眼中的晶莹。
这是我父亲 日记里的笔墨
这是他的生命 留下
留下来的散文诗
几十年后 我看着泪流不止
可我的父亲已经老得像一张旧报纸
旧报纸
那上面的故事 便是一辈子
——许飞《父亲写的散文诗》节选。
西席的假日很多,可是放假不放假的,对付我父亲来说,都是一个样。
他每天都很忙,忙着给村落委会写材料,忙着下地干活,忙着写教案,忙着给我判作业。
忙着忙着,他就没了故事!
忙着忙着,我谈起了恋爱!
父亲病倒的时候,我刚刚结婚。
现在想起他当时的笑颜,不仅仅是欣慰,更多的是对迟晚韶华的感叹,也或许有对昨日遗憾的放下吧!
父亲因肺癌离世,也不知道是不是由于职业缘故原由,他那一辈的同事,有好几个都是患肺癌离世的。
#万能生活指南#
一九九四年 庄稼早已收割完
我的老母亲去年 离开了人间
女儿扎着马尾辫 跑进了校园
可是她最近 有点孤单瘦了一大圈
想一想未来 我老成了一堆旧纸钱
那时的女儿一定 会美得很惊艳
有个爱她的男人 要娶她回家
可想到这些 我却不忍看她一眼
——许飞《父亲写的散文诗》节选。
#民谣与故事#
末了一眼,一眼万年!
爸爸,西席节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