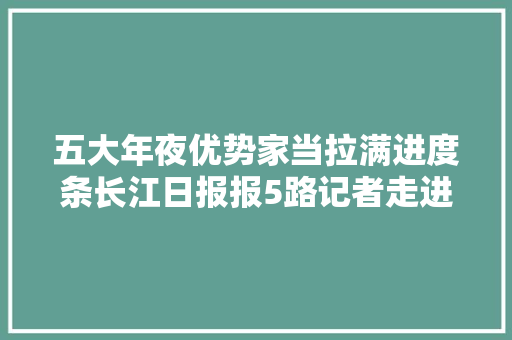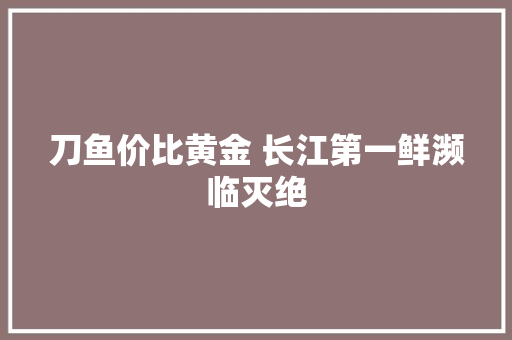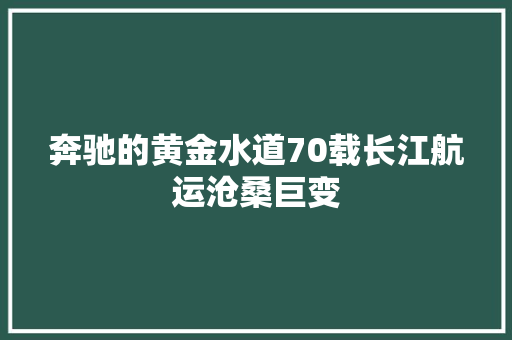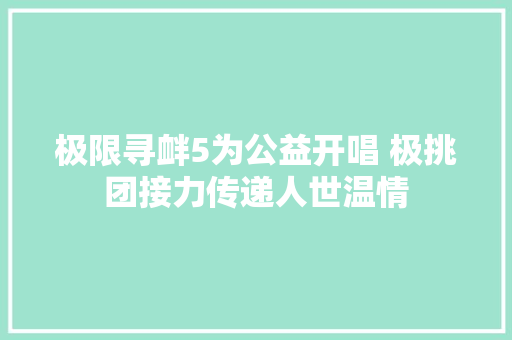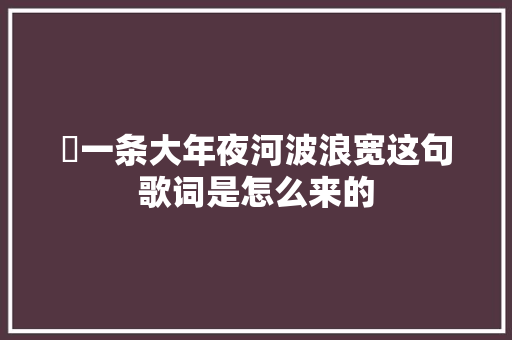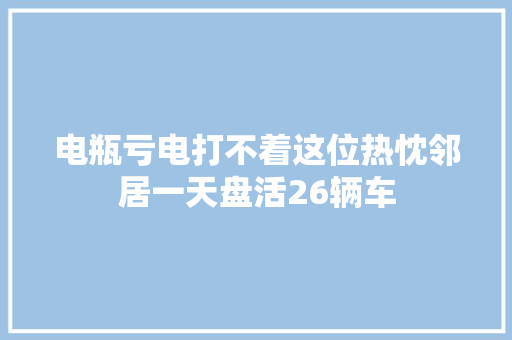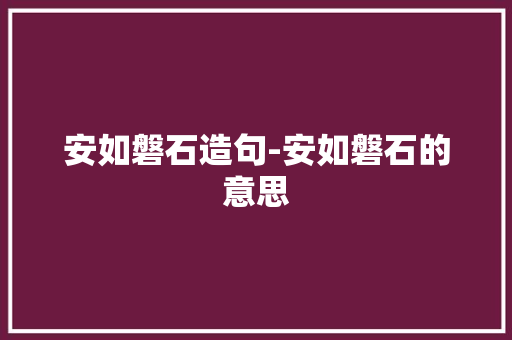文/冉前锋
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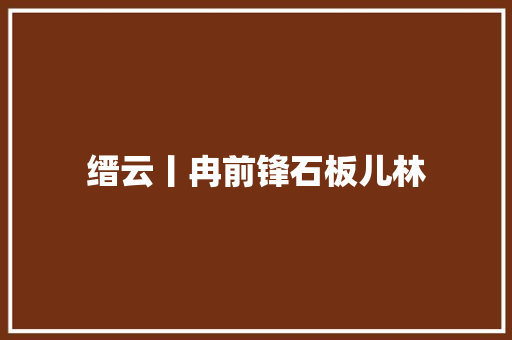
磐石的石板儿林已经不存在了!
这些年,它每每涌如今我的脑海里、睡梦中和偶尔翻出来的老照片上,磐石的那些原村落夫,总是对着一江大水发愣,辩论着它在水中到底是哪个位置。只管滨江公园那片怪石林景点的石头,是从磐石石板儿林切割迁运来的,重新拼接安顿布局,但老磐石人看过之后总是摇头说:“差远了!
差远了!
”
云阳的盘石镇原是一个古镇,坐落在川江之滨,明清期间就已经初具规模,十里长街,店铺林立,祠堂寺院,飞檐翘角,前庭后院,吊脚木楼,参差嵯峨,点缀其间,百年黄葛古树,亭亭如巨伞,遮着漫长的光阴,一条泛着岁月光影的青石板路从河边码头一贯延伸到上街尽头,然后分叉成多条道路,连接起凤鸣、院庄、革岭等州里,是运营县南边的主要水陆中转站和商埠。在古镇东侧,与下岩寺隔江相望处,有一处巨大的江滩:“……广四百丈,长六里。壅塞江川,夏没冬出,基亘通渚(郦道元《水经注》)。”据专家考证,这处江滩天生于距今两亿年旁边白垩纪晚期,长达三点五公里,总面积四平方公里,风浪吞吐,水石相搏,风雨侵蚀,大江冲刷,形成了怪石林立,千奇百怪,如梦如幻的自然奇不雅观,是长江水与江滩石亿万年和谐共生、相爱相杀、雕琢造化形成的石雕侏罗纪公园,是全体长江沿岸唯一的水下石林(万年巢)景不雅观。这便是石板儿林,磐石人的称谓。
石板儿林滨江而下四公里,从盘石镇西沙坝一贯向东延伸到马岭,其精华部分在前面三公里,有石钟、石锣、石鼓、牛尾石、万年巢、关塘、野鸭滩。这些景点冬夏没冬出,天然巨石,首尾相连,乃至相互重叠,其间便是广袤的长江石林,石林里的鹅卵石,现在被叫作长江石,我们本地人叫作石板儿。大小不一,形态互异,色彩斑斓,尤其是浸泡在水凼中的小石子,在阳光的照射下还金光闪烁,熠熠生辉,色彩斑斓的卵石呈现着艺术的原色,赤若朝阳,黑如碳墨,白似天光,绿如春水,橙如柑橘,黄似稻麦,青若翡翠,蓝似碧天,在大小不一,形态互异的石板上挥毫泼墨,涂染着色,杂色渲染,残酷若霞,把大自然的绚丽色彩,印在这方的石板上,这便是后来奇石爱好者取名的“长江石”。多年往后,我参不雅观一些收藏家的奇石展览,看着玻璃展柜里的几颗寂寥的长江石,我像一个前朝遗民,呆呆地看着我不知道的天下,愣愣地听着对这些所谓的奇石夸年夜的讲解,它真的不及我小时候看到的那些奇美,那时,我们见到的长江石,不但俊秀,而且多得不可胜数,用老百姓的话说,叫“用箩筐随意装”。
可是,它们却消逝了,而面前这些,还在!
二
影象中的石板儿林最著名的景点是巨石中部的石钟、石鼓。《天地记》也讲到这处胜景:“夔州东乡西北岸壁间,悬二石,左类日,右类月,名曰日月。” 《民国云阳县志》载“在城西六十里盘沱。中流耸石,水落时,堆积成山,其迤然朝对市衢者,削壁方正,高十余丈,阔两丈有奇,未审何时一分为二,有二圆穴。相隔尺余,空围各八九尺,周环光莹,约七八尺厚,一如铜锣、一如巨鼓之未施皮革者,故咸以石钟、石鼓之名。”老家人叫它“盐罐石”。这里亦是磐石人的乐园,尤其是春节,男女老少,相携同游,鱼贯而入,爬石玩耍、捡心仪俊秀的石板,这里也更是孩童们捉迷藏、放鹞子的娱乐天地,乃至还会带上丰富的食材搞野炊。
我小时候也常常攀爬进“盐罐石”去玩,用随手捡起的长江石敲打洞壁,锵然有声,传习良久,或呼叫差错姓名,盎然有声,如喇叭传声,反应久久不绝。有的小朋友爬上“盐罐石”,还在里面点燃鞭炮,声音可以传到对面的下岩寺。从洞内远眺长江,浩浩江水,波涛彭湃,从天涯向我涌来,浪拍底部,巨石连绵,大小不一,水风吞吐,沟通澎湃,年夜声鞺鞳,下声呜咽,如怨如慕,如泣如诉,似寡妇夜哭,如羁人寒起。盐罐石阁下,有一巨石直直延伸,直抵江面,如河马饮水,过往船只,从罅隙中来,俨然可手引其帆。阁下又有经由江水冲刷打磨光滑的两块巨石,下厚上薄,薄薄伸展,形似雄鹰展翅。这两处后来被切割,运到新县城的滨江公园,成了现在公园里的“鹰马石园”。
倘若从盐罐石下来,沿江边行走,便是一望无垠的鹅卵石,由各种长江石组成的卵石阵,平铺漫延,豁然伸展,长江石铺满脚下,长二三公里、宽四五百米,层层叠叠不见底,卵石大小不一,形态互异,错落有致,色彩斑斓,有的细如米粒,有的大如竹筛,有的洁白如玉,有的漆黑如墨。世间万物,波澜再现,花鸟虫鱼,大地星辰,飞禽走兽,日月山川,都会在小小的长江石纤毫毕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寥寥数笔,就使任何一个天才画家望尘莫及!
这便是我们心中念念不忘的那片石板儿林,磐石人多年约定俗成的称谓。
在石板儿林的尽头,江边簇拥着一大片石林,成百上千块石头耸立江边,经由亿万年江水的冲刷洗礼,已经用站立的姿势、固态的形式再现了川江的波澜壮阔,那些石头全部是波浪的印记,表层是漩流冲刷成的千奇百态,底部留下了波浪的印迹,层层荡漾、荡荡江涛就这样瞬间凝固,如冰雕雪凇,留住了大雪的样子容貌,我们叫她——石浪。层层荡漾被固化下来,铺展成浪花的样子。那些川江的惊涛骇浪以同样的办法留在了“石浪”的上面,那些站立的巨石在波浪的冲刷下高高耸立,立正排列,像森林树干,似列阵兵士,成为一群兵马俑般的战阵,她们圆润光滑,高低错落,长短不一,如美人出浴、炎火盛开、珊瑚出水、猛兽下山;似海豹探头、大象溜达、巨龟出水;如雄鹰展翅、河马饮水、犀牛望月。密雪碎玉,水邑平沙,巨浪漩涡,勒石为铭,万里长江,终有了这一处,而且是唯一的一处,大自然用它独特的办法,固化了波浪,凝固了漩流,再现了波澜壮阔的川江之水,在冬日暖阳的照射下,熠熠生辉。磐石人同样也授予了它一个形象的名字——万年巢。是的,倘若没有亿万年与江水的亲密打仗,搏击鲸吞、风吹雨打,日晒夜露,旋流浩荡巴山月,沧海洄流兴隆滩,石头与江水又怎么能共同谱写这绝世无声的凝固交响乐!
石板儿林不仅有瑰丽的自然景不雅观,而且还有丰富的人文历史。据《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记载,我们最早的先人是母系氏族——盐水女神,他们结网捕鱼,熬盐佃猎,石板儿林是公元前三千五百年盐水女神部落最早的栖息地之一,为了抵御沿清江而上的癛君巴人部落的蚕食,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保卫家园的斗争,“浮血漂杵,遮蔽日光天地,积晦明十余日”;明末张献忠与明军在此多次征战,战鼓铮鸣,杀声震天,樯橹碰撞,箭矢如雨;抗战期间,日军轰炸磐石伤病医院,大部分的航空炸弹落入长江及石板林,火光迸裂,水石横飞,弹痕累累,被江水冲刷后还有着硝烟的印迹。还有罅隙中数不清的“石板材”和撑船籇杆留下的圆形“籇杆”洞,无不记录着先人们在这片石板滩上凿井煮盐、搏击风浪、仰取俯拾、热血长歌的高光时候。这统统尤其以“牛尾石岩画”为主要标志,佐证了那个刀耕火种、结网捕鱼的盐水女神时期,牛尾石岩画是盐水女神部落留下的一幅岩画,镌刻在牛尾石朝石板林方向,单线阴刻,细腻写实,通过最原始的岩画,展现了我们先人在此地捕鱼、佃猎、煮盐、居住的生活场景,生动形象、维妙维肖。如今,这幅岩画的水上部分,在库区疏水前被切割搬运,保存在云阳三峡文物园中,成为最古老的文物遗存。除这幅岩画外,还有散落在石罅隙和石板林中的石斧、石刀、石纺锤以及青铜弩机,无声地诉说着那段辉煌的文明史。二〇〇二年,时任重庆市政府特聘考古专家、博士生导师,安徽考古队队长、卖力晒经村落汉墓发掘的云阳籍张钟云师长西席,看过石板儿林,特殊是随手捡起的石制工具后,大为惊叹,曾经在专家组会议上据理力争,发出对石板儿林进行水下保护的发起,终因各类缘故原由,没有履行。
牛尾石岩画位于牛尾石上,牛尾石是石板林前出长江有一个巨大的礁石,与石板儿林隔水相望,相距百余米,水道狭窄,江流湍急,是江中一巨大礁石,行船基本无法靠近。夏没冬出,形似牛尾,十丈见方,冬天时立有航标灯塔,磐石人只要一见客船经由牛尾石,就会赶向江边乘船,而客船也会在牛尾石拉响第一声“威斯”(英语whistle,指轮船鸣笛),可见它不仅是历史遗存,还是地理和旗子暗记标志,由于阵势险恶,鲜有人迹,以是古老的岩画得以保存至今。
三
在石板儿林的尽头,长江的南侧,对着万年巢方向,有一个1000平方米的深水塘,水极深、本地人称“十二匹腊蔑达不到底”,人们叫作“官塘”,他和长江上游浩瀚因江水涨落形成的堰塞湖一样,是长江鱼的天然宝库和产卵地,历史上长期被官府掌握:“县吏先渔,以供官厨,始由民取,盖累朝之旧制也”,1949年后才真正回到公民的怀抱。每到冬季退水后,碧水蓝天,朵朵白云倒映在湖面,波澜不惊,水平如镜,与澎湃的江水形成光鲜的比拟,隔着石板林,有着“屏开两面之镜,壁碎中流之月”的意境。由长江涨水带进来的长江肥头儿、鲢巴浪、水米子、翘壳儿,辣子鱼(中华鲟),箭鱼、江团、乌龟、桃花鳊胭脂鱼等,随着冬季退水留在了官塘,她们随遇而安,以塘为家,游弋其间,往来翕忽,江团还在塘边的沙坝里产卵。春节前夕,渔民们撒网捕鱼,大人小孩拖鞋下水,伯仲并用,收成颇丰。这里,还时时有数百只野鸭成群结队飞来,在此产卵下蛋,嘎嘎的野鸭漫天翱翔,有序降落,白茫茫一片,天地相连,形成巨大的鸟阵,蔚为壮不雅观。时而又飞往牛尾石下贱的江滩,迤逦排开,在江边觅食,磐石人将这江滩叫做野鸭滩。我儿时常在野鸭滩的罅隙中“捡石板柴”,当时不知道为什么那些罅隙中有那么多的木材,光滑圆润,是非大小不一,一样平常要用铁制的长钎,捅进木材,然后拉拽出来,放进背篓,晒干后,那些柴极易燃烧而无烟,是煮饭的好燃料,大人们也默许了我们的行为,只是告诫我们:把稳安全,不要离水边太近。有时,我们用拾掇的“石板柴”烧烤食品吃或者烤冻僵的手脚。记得有一次,我们捡完“石板柴”,只见一条上岸艇从下贱上来,我们清晰地瞥见船上的船员,于是我们齐声高喊:“一领江、二领江,三领江的X眼痒,四领江是个咬X匠!
”话音没落,一条被上岸艇巨浪惊起的长江鲢鱼掠出江面,径直飞到我们面前的石槽中,我们蜂拥上前,捉住了这条大鱼,足足有七八斤。那个活蹦蹦的童年,至今还在梦中萦回。
那个年代的船多为木船,实在我们捡的石板柴,绝大部分是川江沉船的残骸,那时的川江,惊涛骇浪,而磐石上接一里峡,下迤兴隆滩,漩涡密布,暗礁纵横,片帆稍有不慎,就可能触礁沉没,川江“桡胡子”(船工)便是过着浪头出没、步步惊心的日子。一旦发生事件,只好葬身川江喂鱼,而沉船就解体,木材因水流嵌入了石罅内,便是我们后来看到的石板柴。难怪大人们都讳莫如深,原来在我们这个水码头上,险些家家都有转弯抹角的亲人当过“桡胡子”(船工),也有人因水难事件再也没有回来。那些散落在滩上大大小小的圆洞,是行船的前驾长用籇竿撑船留下的印记,船行高下,探水路、避风浪、躲漩涡、搏激流,在那个靠纯粹人力的时期,籇竿便是方向和雷达,担保着一船人的安全。籇竿洞小的直径寸余,大的数米,那些星星点点的籇竿洞要多少年、多少代的船工们手撑长杆、点击礁石,在坚硬的礁石险滩上留下微不足道的印迹,经由风浪漩涡的洗礼,逐渐扩大和加深,这中间一定有船毁人亡的捐躯;折戟沉沙的过往;碧血长歌的故事;血汗淋漓的坚持,于是,这片石滩就成了船工们的画布,他们以籇杆为笔,以石为纸,沾上江水,籇杆如弯弓,身体似强弩,在险滩上凿下了这无字天书,像勒石为铭的古代战将一样,谱写了一曲曲澎湃的生命壮歌。
四
石板儿林里的石板不仅可以烧制石灰,它的沙石里,还可以淘金呢,一些闲时的人们,总是三五成群或者一家一家的人,带着淘金工具劳碌在石板儿林里,等过段韶光,就有人来出价收购。当然,也有一些专业淘金者,年年冬天都从远处到来,食宿在石板林,不分白天黑夜在此外淘金,但技能一样平常都不外传,与本地人保持着间隔,他们的收入多寡、发卖渠道、生产流程都不得而知,但是大度朴实的磐石人并没有欺生,还瞟学(偷学)了一点技能。
在石板儿林的中央地带,有一个石灰窑,有时还会有另一班子民工过来挑选白石板,堆放码好,那一堆堆的白石,等待木船过来装船,运往万县、云安等地的陶瓷厂,听说是生产白瓷碗的主要质料。哦!
原来我们小时候吃的白瓷碗,晶莹剔透,洁白如玉,竟然也是石板儿林的白石板儿,经由敲击打碎,水火交融,浴火再造!
真可谓:九天风怒石窑开,夺得白云下凡来!
每到入冬退水后,谭伯伯就来此地扼守石灰窑,他在一处环形的石头间搭建“屋子”,上面用牛毛毡盖上,遮风避雨,石屋里还很暖和,一贯到第二年春末暴雨涨水前才搬走。寂静的石板儿林晚上总是有一堆熊熊的窑火,烧窑的质料便是在石板儿林中挑选碳酸钙含量高的优质石灰石、白云石、贝壳等,经由900至1100°C煅烧而成,出窑的时候还需大量喷水。全体烧制过程,除了煤炭,可以说这里原材料充足,烧出来的石灰又白又黏,黏合度极好,是磐石周边人们建房的主要胶凝材料。我曾经在谭伯伯的这个石屋里住过一个晚上,石屋位于万年巢,利用一圈天然形成巨石围成,上面盖上茅草做屋顶,那晚江风怒号,半夜雷雨交加,我靠在大略单纯的木床上,烤着石板柴煨起的火苗,喝着白天谭伯伯垂钓熬制的鱼汤,看大江东去,听下岩梵音,近间隔做了一回守江人。当我走出石屋走到江边准备小解时,遭到在川江上行走一辈子的谭伯伯的严厉呵斥,我匆忙落荒而逃,走到背对的方向十来米才得以解急。那晚月色皎洁,我在小解的地方瞥见了两只江团,摇摇摆摆,左顾右盼,一贯在前爬行,一贯在后鉴戒,产完卵后,她们又沿着原路返回,后面那只江团把脚迹掩埋,我立在那块仄石块后面,屏住呼吸,目睹两只月光下一公一母两只江团,扇起脚蹼,刨洒砂粒,掩埋走过的脚印,那嘘嘘嗦嗦的抛沙声,淹没在江流澎湃中,两只江团随着夜潮,没入长江,仿佛它们没有来过。对岸的下岩寺,传来梵呗声响,如上古清音,穿过午夜长江和月光下的石板林,一贯传到我和谭伯居住的石屋,颤若游丝,声入太霞。谭佰提起水桶给石灰窑熊熊烈火降温,升起的白色烟雾袅袅散开,逐水而居的石板林在水火交融、明月朗照下成一帘幽梦,装扮了我少年的天空。
我后来才明白谭伯伯为什么发火,我准备小解的地方正对着江对面的下岩寺。下岩寺建于唐代,唐末定州人刘道带领徒众在江边的陡岩上开凿成寺,里面是一个洞天福地,供奉着弥勒诸佛,保佑长江行船船工们安全行走的燃灯菩萨,还在洞内崖壁上雕有八百罗汉,一条白练般的瀑布悬挂洞口,表面是依壁而建的巍巍寺院。公元1172年暮春,著名墨客陆游任四川制置使范成大幕府参议,帮忙谋划其北伐中原并担当后勤粮草的组织押运,他犹豫满志,溯江而上,夜宿下岩寺,眺望石板林,他写下了《忆昔》一诗:
忆昔浮江发剑南 夕阳船尾每相衔
楠惨淡处寻高寺 荔枝红时宿下岩
峡口烹猪赛龙庙 沙头伐鼓挂风帆
区区陈迹何由记 惟有征尘尚满衫
那个时候正是端午节,长江的春潮已过、夏汛即将到来,齐心专心北伐中原的陆游只管军务在身,仍旧记录了对岸的磐石人正在伐鼓赛舟、烹猪敬拜,赛龙舟的热闹场面,峡口和龙庙是先辈们聚会比赛的地点,峡口便是一里峡,龙庙便是一里峡岸边的龙王庙,我小时候还瞥见过他巍峨的背影,而沙头,便是因时令“夏没冬出”的石板林。墨客虽然器重面前的美景,却没有忘却北伐中原的义务,以是有令在身,不得不发出“区区陈迹何由记,惟有征尘尚满衫”的感慨,在这位矢志北伐的墨客面前,龙舟赛、龙王面、下岩寺、石板林只不过是他热爱祖国万里江山的“区区陈迹”而已,他有更加主要的义务和沉甸甸的任务,保卫包括石板林在内的祖国如画江山。
磐石石板林,犹如一组立体的立体画屏,悬挂在古镇的东北方,耸立在古老的长江边,与流水相伴、和古镇为邻,参差嵯峨,气候万千,岁岁年年,岁岁年年,石头在江风漩流中与大自然雕琢发展,精益求精,触浪而生,造诣了如梦如幻的自然奇不雅观,重新授予它生命的力量。那些被江风骚水洗刷、被阳光雨露青睐的江石,在亿万年的漫永劫间中破茧成蝶,凤凰涅槃,化成千奇百怪的石林,残酷在大江之滨,绽放在冬阳之下。石板林是波浪之涡、石板之园,江滩之魂、精神之林,石头在与波涛的搏击中相爱相杀,百炼成钢,她是绝望中的叫嚣、急流中的砥柱、重压下的抗争、出水后的坦然。纵然伤痕累累,也要出头见日;纵然饱经风浪,也要笑傲江湖!
石板林是峡江人发达生命的象征。
作者简介:冉前锋,重庆市云阳县人,作品散见于《延河》《野草》《红岩春秋》等杂志,曾得到缙云精良作品(月度)奖。
(编者注:文中由于引用了部分民俗习语及传统文化的先容,编辑作了分外处理,并尽可能保持作者的写作风格及地方文化留存。)
本文部分图片由解维明师长西席供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