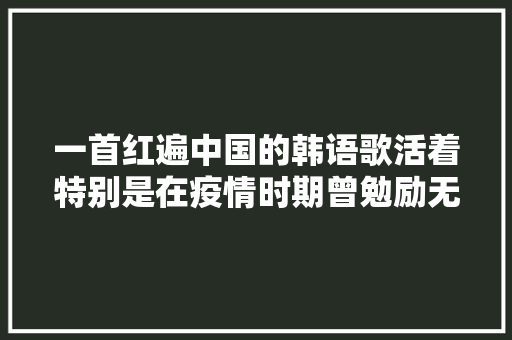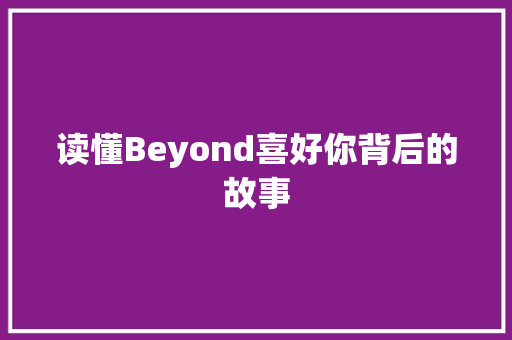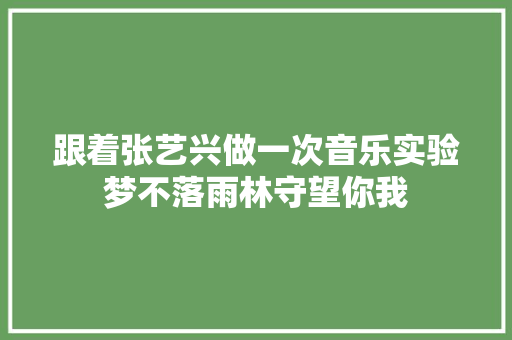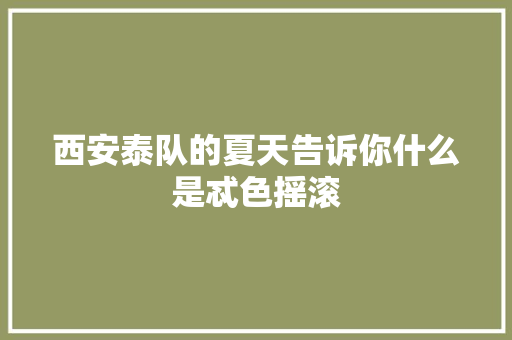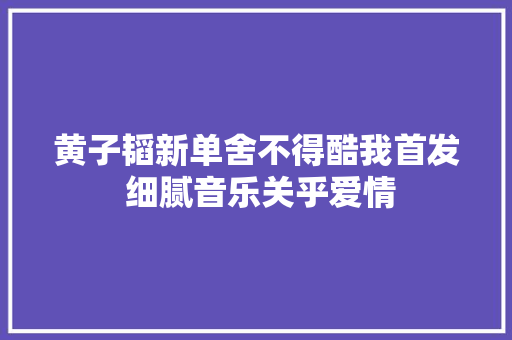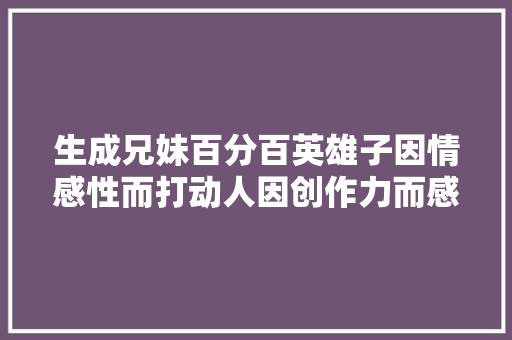上世纪80年代,张蔷的迪斯科歌曲像一个闯入者,带着一股自由的力量。
含羞的女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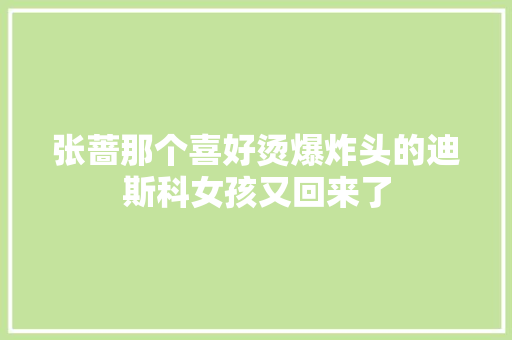
很多出生在上世纪80年代之前的人印象中都有这么一段唱词:“自从在相思河边见了你,就像那东风吹进心窝里,我要轻轻地见告你,不要把我忘却……”这是1962年问世的一首台湾老歌,曾经被凤飞飞、陈淑桦、蔡琴、陈百强等浩瀚歌手演绎,但是人们彷佛更熟习的声音则是来自张蔷,这首歌来自她1985年初发行的一张名为《如果》的专辑。
80年代初期,邓丽君、刘文正、张帝的音乐风潮刚刚刮过,这些曾经一度被批驳,“只敢在家里偷着听”的音乐开始被社会大众所收受接管,人们开始正视这种当代的情绪表达。1980年,“立体声”逐渐成为一种音乐标志,那时候中国家庭的录音机数量开始多过收音机,常见一些穿着喇叭裤戴着墨镜的年轻人肩扛着录音机从胡同里招摇过市,他们是中国的第一批盛行音乐收受接管者,他们在歌曲里为自己的青春探求答案。那个时候的张蔷还是北京市海淀区205中学的学生,和很多年轻人一样,听盛行歌是她生活中的一部分。
张蔷出生在北京的音乐家庭,母亲是中国电影乐团的小提琴手,上幼儿园的时候她便开始学习拉琴,小时候的她很难投入,练起琴来也是断断续续的。她记得自己常常跟随母亲去影棚录音,在那里见到了德德玛、朱明瑛、李谷一、指挥金正平做录音,那个录音棚彷佛让儿时的张蔷充满了某种期待,期待自己某天可以录一张自己的专辑。
张蔷
“我那会儿看演出的机会比同龄人多。”张蔷至今还能细数出一些演出,例如佐田雅志、杨百翰大学、跳健美操的关西艺术团、日本松山芭蕾舞团、小泽征尔,以及俞丽拿、盛中国的小提琴演出等。小时候的张蔷看演出很投入,这些演出冥冥中为她打开了一种音乐的界线和演出的思路,正是在这些演出中,她开始探求一种属于自己的声音,属于自己的演出办法。
小学毕业前,她想报考中心音乐学院附中,于是带着小提琴去口试,一入考场,她给老师鞠了个躬,说了句“不想在提高小学念书了”,随即拉了一曲“火车向着韶山跑”,之后被拉帕格尼尼的同学们“淘汰出局”。不久,她又在唱歌中找到了一种快乐,她说:“我很早就有方向了,那时候就特清楚自己想唱什么。”
卡彭特(Carpenters)的《昨日重现》(Yesterday Once More)是少年张蔷每天早上起来闭着眼打开录音机听到的第一首歌。那时候,十二三岁的她总是待在家听电台节目,无论播到哪种措辞的电台,只要里面有音乐,就能和她产生共鸣。1984年的某个冬天,放学回家的张蔷听到了一首贝斯开头的歌曲,随着鼓点节拍的进入,她随着脱下毛衣在家跳起舞来,很长一段韶光,那个旋律都在她脑筋里徘徊,过了良久她才知道,那首歌是迈克尔·杰克逊(Michael Jackson)的《Billie Jean》。
凭借着“外洋关系”带来的大量音乐和自家转录的各种音乐磁带,张蔷开始在这些音乐参考中学习,年轻的她接连爱上了刘文正、杰克逊等好看的男孩,也逐渐在那些充满活力的音乐中找到了喜好的声音。“五轮真弓、大桥纯子我都非常喜好,只管我后来也唱过松田圣子的歌,但始终不算最喜好的一类,由于她的音乐便是那种偶像声音,虽然我在80年代唱的也是这种东西,但始终不是我仰视的那种歌手。”张蔷说,“我最喜好的还是辛迪·劳帕(Cyndi Lauper),她的嗓音非常有辨识度,天真甜美,但是也有张力,可以从童声变到粗犷,那个时候我想留一个劳帕的发型,我妈说那可弗成,你这不便是‘文革’时候的阴阳头么?出门会挨揍的。”
迪斯科闯入者
此时在中国开始传唱的盛行歌曲已不再是“靡靡之音”,电视台上偶尔也会听到几首随处颂扬的港台音乐,很多人以为那便是“新潮”,却又说不上“新潮”到底是什么,对他们有若何的影响。1984年,央视播出了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只管当时只有美声和民族唱法两个品类的选评,但是仍有相称数量的年轻人准备了普通歌曲去参赛。
同年,北京也在海淀文化馆举办了一场歌手大奖赛,现场来了不少唱美声、民族,苏式民歌的选手,张蔷是人群中最标新创新的一位。那会儿与她互助的吉他手是一个牡丹电视机厂的职工,这个音乐爱好者上台时显得很紧张,张蔷却表现得很轻松。在四五个50来岁的评委大叔面前,她轻松地唱了一首卡彭特的《什锦菜》(Jambalaya),那是一首美国村落庄歌曲,评委推着眼镜不断打量着面前这个十几岁的女孩,迷惑道,你唱的这是什么啊?听不懂,听不懂。直到本日,张蔷讲起这段经历仍旧以为可笑。
比赛没有让张蔷落空,却意外地认识了郭传林,他曾经是黑豹乐队壮盛期间的经纪人,也是之后多个唱片公司的高管。“当时,他是个穴头(80年代晚会演出策划者),找了我两次,就带着我们一大票人去演出了。我印象中的第一个穴在三门峡,我们在北京站的东大钟凑集,那会儿北京站挤满了去外地演出的明星和团体,刘晓庆、蒋大为、孙国庆、丁武、秦齐,还有广播乐团和海政民歌的,也有演出曲艺的,我们坐在绿皮火车上,晃晃荡悠地驶向目的地。记得我当时穿了双玄色的丝袜,同车厢的大爷问我穿的是什么,像一腿的毛。”
80年代,这种拼盘式的演出比比皆是,它险些是当年老百姓唯一的娱乐生活项目,也是当年一众明星们起身的缩影。张蔷还记得《卡罗》《伤心的电影》《请到天涯海角来》是她的演出曲目,当台下穿着背心、卷起裤脚的上千人听到歌曲时,张蔷仿佛感到了一种强烈的气场,那是人们对付音乐的一种热爱,犹如某种本能的需求,它让很多人听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情绪。第二天,当地文化部门的人还是以为张蔷的歌里“有毒”,禁了一场,张蔷提及这段故事又乐了半天。“那会儿的演出票价也就八毛一块的,收上来的很多钱都是臭的,我的一场演出费差不多8块钱,一个月能有80多块,比我妈当时挣得还多点儿。”张蔷连续回顾道。
由于北方市场的闭塞,当时有人建议张蔷去广州的茶座唱歌,由于在港台文化的冲击下,中国的南方已经率先收受接管了盛行音乐,而张蔷所喜好的音乐彷佛也正对那里的胃口,或者说,这些人以为张蔷只有去了广州才有发展,才能挣到钱,但当时的张蔷并不想去广州。
在张蔷还不到18岁那年,她通过了云南音像的试唱,得到了代价1400元的唱片条约,随即和电影乐团的小乐队南下,在那里第一次见到最新的多轨录音棚。林述泰是张蔷的专辑编曲,作为大阮演奏出身的民乐音乐人,林述泰也同样受着日本盛行音乐的影响,此时他已经是海内较为出色的制作人,即便如此,张蔷总是对编曲不满意。张蔷喜好迪斯科,也喜好Funk音乐,她认为那种动律会让人舞动起来,然而林述泰所理解的舞曲并不足激烈,反而温婉了许多,实在此前二人在北京时,就由于音乐想法发生过争执,张蔷乃至直言:“您懂迪斯科吗?”每到这时,张蔷的吉他手刘麟就会站出来解围,用他的理解来连续编曲。
张蔷以为迪斯科是一种年轻的感情,一种快乐的声音,在当年却不被很多人理解,她光彩:“我的古典音乐没走太深,没走进悲悯的感情中,但是小提琴是我的根本,它让我对音乐有了触感,所幸我没有打仗过民乐,直接打仗到了盛行,我喜好迪斯科和Funk,做这种音乐不能是麻木冷血的,必须是很阳光、直接的。”
没过多久,一张名为《东京之夜》的专辑上市了。专辑封面上,张蔷穿着艳赤色运动衣系着赤色的头带,扮出可爱装,她斜看镜头,像是发出笑声。专辑的同名曲《东京之夜》有明显的日式风格,显然作为编曲的林述泰更强势些,张蔷的演唱如同一个青春的少女,讲述着快乐和忧伤的故事。整张专辑以重新编曲和填词的翻唱为主,在那个年代,这种“汉化”的外国歌曲是罕有的声音,也是某种精神上的奢侈品。
张蔷--《东京之夜》专辑封面
王洁实说,谢莉斯那时候唱歌稍加了一个滑音,一首歌曲就变成资产阶级腐烂歌曲,以是他们这对组合一贯都唱得很小心,只管即便端庄,然而张蔷一出来,就很生猛,彷佛没有什么顾忌一样。在那个年代,张蔷的歌声像一个闯入者,带着一股自由的力量。
专辑从起初的60万张,加印至250万张,很多经销商直接拿着现金在印厂门口等货,唱片公司乃至都没有想到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姑娘为什么竟会受到如此的欢迎。一个月后,张蔷的歌险些传遍大街小巷,很多人以为她是“女刘文正”,彼时很多商店为了招揽买卖,都在播放她的歌曲。云南声像的老板陈连丹决定再录一张,并且将录音的用度涨了6倍,张蔷计算着自己的这笔收入——再有1000块,便是万元户了。
在音乐人苏越的回顾中,那是一个险些可以一天录一张专辑的年代,录音机一开动就会赢利。只管当时的中国人还没有什么版权意识,很多人都是直接拿来翻唱或者填词演唱的,但它是中国最初盛行音乐的缩影。在那段历史中,张蔷当初那个娇滴滴的声音,乃至那个模拟《大众电影》里“美国演员”的造型,在当时都是一种颠覆。在音乐上,她颠覆了某种迂腐、乏味、虚假的宣扬式抒怀旋律,让人们听到了一种真实的情绪和新鲜的律动。
《爱你在心口难开》《我一见你就笑》《洒脱地走》《那天晚上》《含羞的女孩》《星期六》《请留下来》《好好爱我》等比及处颂扬的歌曲,如同一阵旋风刮遍了全体中国,从1985年初到1986年的两年韶光里,这个18岁的北京姑娘统共出版了15张专辑,售出2000万盘磁带。1986年,张蔷凭借她的人气成为那一年美国《时期》评比的“环球最受欢迎女歌手”,位列第三,排在她前面的两位是惠特尼·休斯顿和邓丽君。
1987年,张蔷已是中国一线红人歌手,此时的她却没有选择连续留在中国歌坛,而是决定去澳大利亚,组建自己的家庭。这个曾经让很多人弗成思议,因此关于她消逝、被禁的传闻不胫而走。一个最为普遍的谣言是“被封杀”,很多人推测她没有演出团依赖,是个独立歌手,因此唱这些“不康健”歌曲不被上面所接管。说到这里,张蔷摇摇头,自己也表示很费解。
重返地球迪斯科时期
在国外的日子里,她仍旧关注海内的乐坛,等她再次回抵家乡的时候,迪斯科已经不再是最盛行的音乐风格了。西北风、校园民谣、地下摇滚相继而来,张蔷那会儿以为自己就像一个高等票友,只要有闲钱就拿来录唱片,请人编曲,请乐手,总之拿录影棚当卡拉OK了。
张蔷记得,20年前在电影交响乐团的楼里,有人给她带来一个“迷弟”,不过令她没有想到的是,这个名叫沈黎晖,看起来有些羞涩的小伙子,末了会成为她唱片公司的老板。2005年后,张蔷谢绝了沈黎晖的两次演出邀约。2011年,她在保利剧院开了“醉蔷音”演唱会,很多人再次看到了当年那个浮滑岁月,如歌情怀一样平常的青春往事,不久,张蔷便被约请到了沈黎晖的摩登天空办公室。
沈黎晖希望张蔷能参与音乐节,但又不想让人以为这是一个歌手的演出,便问张蔷,你以为你在音乐节演出,不雅观众会买账吗?随后,他抛出新裤子乐队,说这个乐队玩的也是复古,张蔷的第一反应是,互助?我不谢绝啊。在听过新裤子乐队的《Bye Bye Disco》之后,张蔷彷佛对这次互助有了些期待。
新裤子乐队的《Bye Bye Disco》出自一张名为《龙虎人丹》的专辑,他们用时髦的装扮服装和北京市井草根文化混搭,用一种土酷和诙谐来诠释复古。在这张专辑的首颁发演上,乐队装扮成李小龙和功夫爱好者的擂台,来搭配他们好玩的音乐。新裤子乐队的两个小伙子彭磊和庞宽是北京小伙子,张蔷以为他们骨子里带有一种冷漠和伤感的东西,在音乐上的想法很同等。
当然,张蔷也有些不适应的地方,比如排练室的环境,她至今记得安定门的“蛇穴”,那个排练室位于某个老小区的地下室,进入排练室要穿过漫长仄仄的过道,那天张蔷穿了一件演出服,走到排练室一看,直接给气走了。张蔷说,自己在认识新裤子乐队成员之前从来没有去过Livehouse,她说自己一开始也不想唱《手扶拖沓机斯基》那首歌,但是这些琐事都在一次次的磨合之后不再成为问题。
“我们来自不同的音乐天下,但是我们有一个共同点,便是喜好较骚气的音乐。”张蔷说。2013年,彭磊写的《别再问我什么叫作迪斯科》成为张蔷的专辑主打歌,在专辑封面上,那个喜好烫爆炸头的迪斯科女孩又回来了,不过这一次,她的身边多了一个人,一个彷佛蕴含着科技能量的舞蹈机器人。
《我的八十年代》是庞宽专门为张蔷写的一首歌,歌词是:“我们的爱是少年维特的烦恼,我们的心是约翰克里斯多夫,还有一首诗,一首朦胧诗,还有一首歌,一首迪斯科。”张蔷以为这张专辑让她一下子找回了当年的青春和热血,她开玩笑,唯独占点儿不满意的事,便是专辑的名字,该当叫:“你就该当知道什么是迪斯科”。
前不久,一首名为《北京女孩》的歌上线了,这是张蔷全新专辑的主打歌。她邀来几十位不同身份的北京女孩演绎这首音乐的MV,作为“北京大姐”的张蔷,以为自己和这些姑娘们最大的特点便是洒脱、直接。在这张专辑中,庞宽又为她制造了一种新的迪斯科幻境,《两室一厅》《所有人都在玩手机》《弹吉他的少年》是张蔷喜好讲的那种故事,她以为自己之以是喜好迪斯科是由于它里面有快乐,也有伤心,音乐上奢华且落魄。“是一种丰富的情绪。”她说。
张蔷在全新专辑《北京女孩》首创造场
LIFE+演讲x 张蔷
9月22日(本周五)
松果“LIFE+演讲”酷女孩专场
来听张蔷聊聊“迪斯科女孩”
更多精彩好文,尽在中读APP,和会读书的人一起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