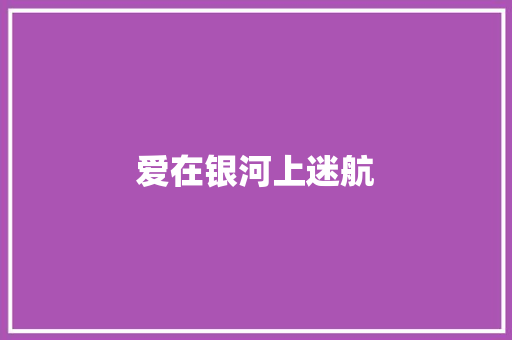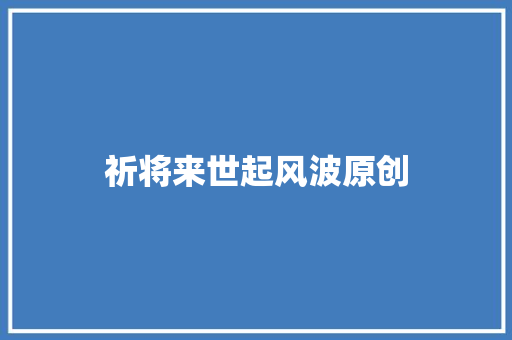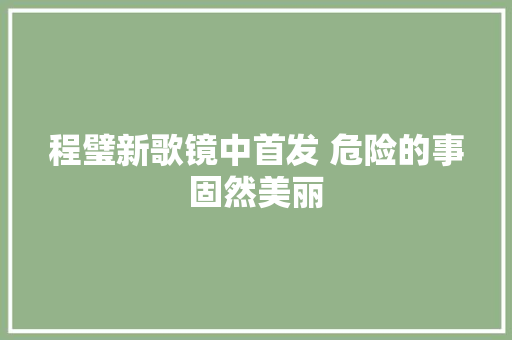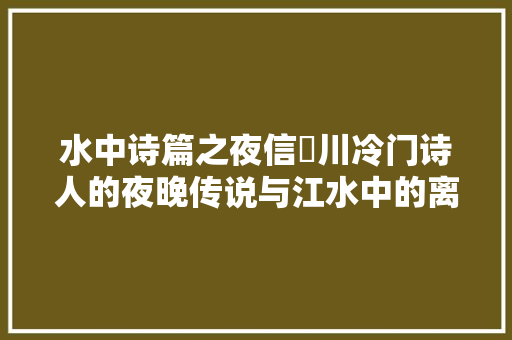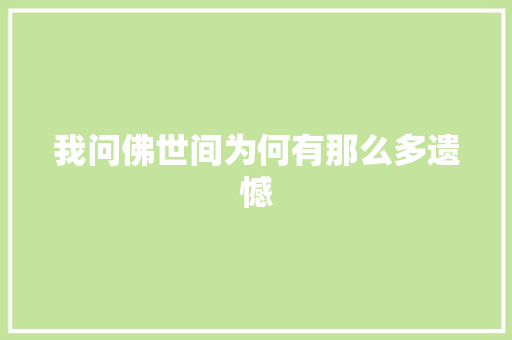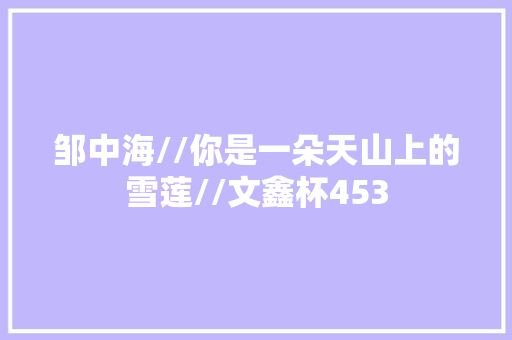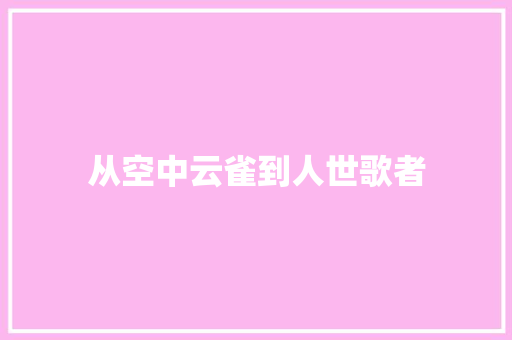天下很远,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的道路漫长,
天下上的地方很多,我却都认得,

我在所有的高塔上,见过了所有的城市,
见过了来来往往的人。
太阳和冰雪之间,很远,
铁路和街道之间,山和海之间,很远。
天下的嘴巴很远,
所有的声音都传到了我的耳边,
乃至在晚上都在唱着多样的歌。
我一口气干了五杯酒,
四处乱窜的风吹干了我湿漉漉的头发。
旅行结束了,
而我和诸事还未了却,
每个地方都拿走了我的一部分爱,
每一束光都灼烧了我的一只眼睛,
我的长袍在每一片阴影中撕裂。
旅行结束了。
而我还跟每一处远方牢牢相联,
但没有鸟救我飞越边界,
没有奔流入海的水,
托住我往下看的脸,
驱赶走我不想远行的睡意……
我知道天下近了,静止了。
诗歌便是生活,欢迎来到由封面新闻、成都广播电视台与《草堂》诗刊联合推出的“草堂读诗”,我是读墨客涓子。刚刚大家听到的是英格褒·巴赫曼的诗歌《天下很远》的节选。英格褒·巴赫曼是奥地利女墨客、小说家。紧张作品有诗集《延迟支付的韶光》《大熊星座的召唤》,小说《玛琳娜》等。
巴赫曼生平中的大部分韶光险些都在“远方”度过。她曾在罗马、那不勒斯和柏林等地旅居。在西西里度假期间,她与俄国墨客阿赫玛托娃相识;而在维也纳,她重逢了交往生平的精神伴侣保罗·策兰。
巴赫曼的父亲曾是纳粹军官,巴赫曼从童年起,就对纳粹历史深怀厌恶和恐怖,并对犹太人有着原罪般的“负罪感”。而保罗·策兰则出生于一个讲德语的犹太家庭,父母去世于纳粹集中营,策兰本人也由于犹太人的身份历尽磨难。两个看似水火难容的灵魂,却相爱了。他们在写作上相互启示,相互汲取灵感。巴赫曼后来受策兰的影响,走上了诗歌创作之路。
但当时维也纳对策兰而言,只是一个流亡中转站,作为来自罗马尼亚的犹太难民,他不能留在奥地利,只能去法国,而巴赫曼当时在维也纳大学攻读哲学博士学位,她只能承受分离的痛楚,与恋人作别。分别后的两个人就像隔着银河相望的牛郎和织女,聚少离多。书信成了互换的紧张办法。在一起时,统统都那么美好而甜蜜。分开后,许多无法沟通和相互不理解的部分便显现出来。巴赫曼与策兰的爱情终极走向分裂。一年后,策兰在巴黎与他人成婚,有了自己的家庭。此后,巴赫曼希望“借助诗歌同策兰连续对话”,两人保持精神上的友情,连续通信,记录彼此的生活、心灵状态,进行文学对话。两人的书信承载了一段相爱相伤的岁月,也见证了彼此薄弱与辉煌的时候。
遗憾的是,美好的岁月稍纵即逝,两人先后陷入了生命中的低谷。他们经历着各自的困难与外界的非难。巴赫曼从1962年开始涌现严重的精神问题,入院接管治疗。同期间,策兰也被送进精神医院进行治疗。在此期间,他多次企图自尽,直到1970年4月的一天夜里,策兰跳入塞纳河自尽,这一年他刚过50岁。两人在治疗期间就已停滞通信。巴赫曼得知策兰去世讯后,随即在自己的小说手稿中添加笔墨道:“我的生命已到了尽头,由于他已在强制运送的途中淹去世。他曾是我的生命。我爱他赛过爱我自己的生命。”1973年的一个秋日的夜晚,巴赫曼因意外去世,年仅47岁。
巴赫曼与策兰的爱情故事可谓是历史阴影下注定会发生的悲剧,但两个伟大灵魂的交汇,开出了短暂而残酷的花。
诗歌便是生活,“草堂读诗”,有温度、有质感。英格褒·巴赫曼的诗歌《天下很远》以及墨客的故事本日就跟大家这里,感谢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欢迎向我们报料,一经采纳有用度酬谢。报料微信关注:ihxdsb,报料QQ:33864057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