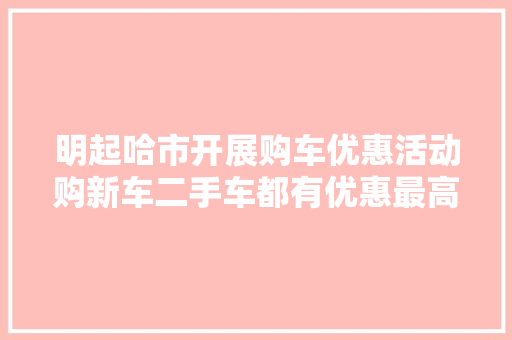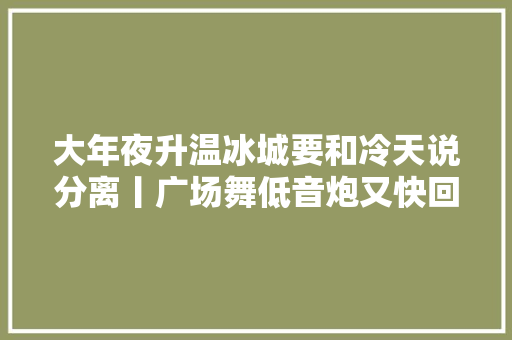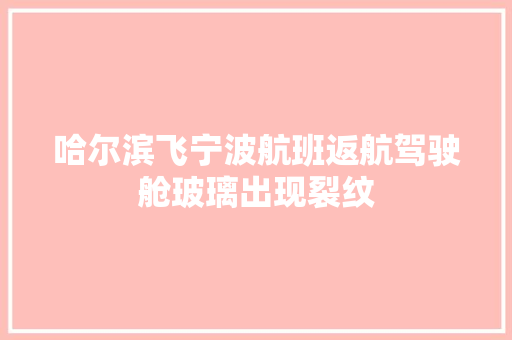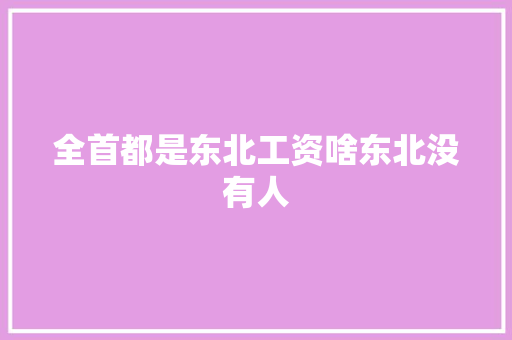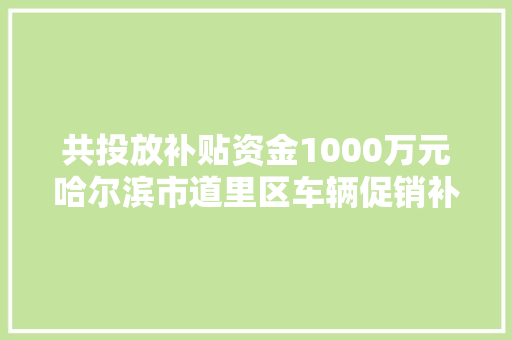人都会有审美疲倦,在美好的事物,短缺了变革就会引起厌烦,而这种厌烦终极还会让人产生崩溃。旅游便是调处这种感情的最佳办法,旅游,便是从自己呆腻烦了的地方去别人呆厌烦了的地方,偶尔换个环境,就换了副心情。
旅游在那个年代只是一个迢遥的词汇,那时随便去往另一个城市,只能叫流窜。很多人喜好生活在城市里,由于城市与“山也还是那座山,梁也还是那道梁”的屯子比较,是不断变革的,商店、饭店的兴衰更替,街道的扩大改变,每天碰着不同的人,总在给人们带来新鲜的觉得。这种新鲜感能给人带来希望,希望就能给人带来活下去的动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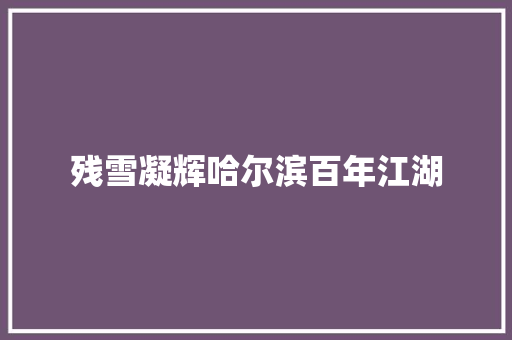
袁克夫在想尽统统办法探求新鲜感,有时就靠回顾往事,确保自己不能在这狭小的空间崩溃。他的视觉之内便是七监铁门和监内几十个号犯人,没办法看到天空时,只能用嗅觉去感想熏染空气的味道,他感到空气中有了青草的气息。春天,是多么美好。七十年代初的哈尔滨,还是鸟语花香,郁郁葱葱,绿树成荫的城市,绝少看到像后来那样在风沙中旋转起舞的垃圾。而自己少年时期的老家山东,此时该当是风和日丽,漫山遍野盛开着那艳丽的桃花了。
那真是一个桃花盛开的地方。1945年7月17日,袁克夫出生于山东掖县西由镇袁家庄。他出生二十天后,8月6日,美国在日本广岛扔下第一颗原子弹。8月15日,日本天皇哇啦哇啦,磕磕巴巴宣读屈膝降服佩服诏书的声音,在全天下各个角落响起。有着深厚敌后游击队根本的山东掖县成为革命老区,为东北贡献大批革命干部和战士。袁克夫的爷爷生有五个儿子,当时在村落里号称袁家五虎。同时有五个壮劳力的袁家本来可以在里庄有着好的生活,可那时的山东,人多地少,苛捐杂税,磨难频发让人口繁盛反而成了包袱。无奈之下,老大袁翰林和许多掖县的人们一样,闯关东,希望在沃野千里荒无人烟的地皮上开拓一片新天地。一进关东,被招募到了俄国雇佣的民工队,替俄国士兵挖战壕,就即是变相参加了第一次天下大战。返国后,参加抗联军队,并随部队入驻最早解放的哈尔滨。老二袁美林便是袁可夫的父亲,终生在村落里务农,赡养老人照顾兄弟。老三、老四饮酒耍钱受不得辛劳贫瘠的农耕生活,也闯关东定居宽城〈今长春〉。老五在潍县十五旅当连长,也曾风光一时,常常骑着高头大马带着卫兵,回袁家庄探望老父。老五在潍县妓院有个相好的妓女,不成想这个妓女同时又和老五团长的相好,团长想独擅其美,寻机暗害,老五在一次回袁家庄路上,被团长派人偷袭,打晕后活埋在的高粱地里。
1950年,袁克夫的父亲过度劳累一病不起,并于第二年去世。父亲去世后,使原来窘迫的生活更加雪上加霜,孤儿寡母又勉强支撑了几年,到了1955年,实在是支撑不下去的母亲托人写信,向远在哈尔滨的大伯陈说家里的窘境。1956年,袁克夫的大伯寄过来三十元路费,让无所依赖的袁克夫来哈尔滨与自己生活。就这样,1956年10月,十一岁的袁可夫告别家乡和亲人,来到了千里之外的北方名城哈尔滨。
1956年的哈尔滨,已经解放十年,由于是背靠苏联最近的大城市,建国之初又和苏联有着紧密友好的关系,有人曾发起,将共和国的宗子哈尔滨作为都城,这个发起未被采纳,从哈尔滨的地理位置上看,过于偏北,也确实不适宜作为都城。1954年,松江省和黑龙江省合并,哈尔滨取代齐齐哈尔成为黑龙江省省会。那时在哈尔滨郊区纷纭建立大型工厂,哈尔滨成为名副实在的重工业城市,朝气发达呈现一派欣欣向荣的气候。
1956年,哈尔滨完成了个体手工业者改造,私有工商业改造,完成公私合营。8月1日,市政府宣告,哈尔滨已进入社会主义社会。那时,哈尔滨的街头巷尾已经没有什么闲人,上学,就业,人们秩序井然。刚到哈尔滨,从未出过远门的袁克夫就被哈尔滨的阔大和洋气所震荡。穿着整洁川流不息的人群,叮叮当当的电车,高大的教堂,悠扬的钟声,盘旋而飞的鸽子,宽阔的街道,琳琅满目的商店,这统统都让初来乍到的袁克夫目眩心花,哈尔滨的繁华壮不雅观和袁家庄,和掖县,和潍县〈潍坊〉不可同日而语。
当年,哈尔滨也只有五十多年建城史,是在泥滩上拔地而起的新兴城市,这样一座标准的移民城市,也使袁克夫很快就融入进去。大伯家住南岗区国庆街8号,袁克夫被街道安排进了马家沟小学。他本来就比同龄孩子强壮高大,又降了一级,在同学间显得引人瞩目。逞强好胜的性情,让他屡次三番的替同学强行出头,有时乃至对抗老师,暴烈的脾气,也使他常常与人发生争斗。因此,袁克夫学习成绩虽然不错,但老师和校方总是视他为另类,是调皮捣蛋、思想风致掉队的学生。常把袁克夫的大伯叫到学校,当面批评训斥,回家后的袁克夫就会遭到一顿狂风暴雨的体罚。长此以往,少年袁克夫有了极强的逆反生理,加上繁重的家务劳动,贫瘠粗陋的物质生活都与表面的天下形成巨大反差。
袁克夫的住处属于比较繁华的地方,后面的文教街店铺林立,小吃浩瀚,一分钱一个的猪肉三鲜水饺,焦喷鼻香扑鼻的盘龙饼,悬挂在钢丝上外脆里嫩的烤鸭,整洁排列油汪汪喷鼻香气四溢的烧鸡,这些美食对他形成了巨大诱惑。大伯每个月给他的两元钱,去掉沐浴理发的,只能够看几次七分钱一场的电影。
刚到哈尔滨,袁克夫认识了在家对面楼上住的刘志伟。刘志伟的父母都是外交官,家境优胜,和袁克夫一见如故,两个人的友情一贯保持至今,外号“崽子”的刘志伟是哈尔滨“蓝道”〈赌钱〉中的顶尖人物。
袁克夫来哈尔滨第一场电影,便是和刘志伟一起看的,从此,光影交错变换的大银幕成了他终生最大的喜好。很多次,袁克夫在自家小院劈柴运煤忙乎家务时,对面楼上阳台,刘志伟的歌声“表面晴空万里,山里面的凤凰何时能够飞行……”就飘了过来,歌声便是约定出门的暗号。这首歌是两个小时十分钟黑白电影“凤凰之歌”中的插曲,影片很长却不令人乏味,片中张瑞芳主演的“凤凰”不屈服命运的寻衅精神,深深的传染了袁克夫,只是,叛逆倔强的他走上了一条相反的路。那阵,袁克夫除了好友刘志伟,还与雨阳街“母猴子”孙艳波,木介街的“黑小子”于百川等人交往,当时不但在街头无事生非斗殴打斗,还时常和他们窜到各处连偷带捡的弄些破铜烂铁换点零钱,知足一下对美食的渴望。
1957年夏,哈尔滨连降暴雨,平日和顺俏丽的松花江开始波涛彭湃水位暴涨,到8月28日,水位达到创记录的120.30。哈尔滨的一些老人儿影象起二十五年前那场洪灾,1932年7月,哈尔滨连续降雨27天,松花江开始肆虐发威,8月7日,松花江决堤,最高水位119.72。中心大街可以行船,当时哈尔滨人口38万,有23.8万人受灾,罹难者2万多人。1957年的水位已经超过了那一年,但哈尔滨没有重蹈覆辙,在市委,市人委紧急动员领导下,共有88.44万人上江堤责任劳动。加上黑龙江,吉林军区解放军的增援抢险,终于降服了这次特大大水。为此,哈尔滨市于1958年建筑了防洪胜利纪念塔,至今都是哈尔滨地标建筑。当时,袁克夫所在学校也停课救灾,他和同学肩挑手提土篮来到江堤。当时,市商业局大力支持,在江堤上摆满平时难得一见的红肠,小肚,肉丸子等,免费给责任救灾的人们食用,袁克夫第一次品尝到了哈尔滨驰名中外的特色美食。
由春入夏,由夏转秋。袁克夫在太平看守所历经寒冷,湿润,酷暑,他从回顾少年时期的往事,想到现在自己的处境,是什么缘故原由上这条路,走错了路,也要挺着走下去,没有后悔路,没有转头路。靠在墙角的袁克夫感想熏染到秋日的一阵凉风,很是惬意。七监的人进进出出,他成这里牢底坐穿的“老人儿”了。南岗的“三瞎子”在七监坐班,按袁克夫的规定,南岗、太平的人四个一排码坐,其他区一律六个一排。南岗的人得照顾,毕竟袁克夫属于南岗。“三瞎子”三十来岁是个“荷包”,身材瘦高马力挺足,在马家沟一带也挺出名。袁克夫每次看他,这小子都微闭双目彷佛再养神,由于脸瘦,显得他的颧骨特殊凸出。袁克夫摸了一下自己的脸,从打进太平看守所,自己也瘦了许多。刚一开春,太平保卫组连续提审了他几次,勤打锣鼓没好戏,预审员翻来覆去便是向他要案子。联翻审讯下,袁克夫仍是熟视无睹,坚不吐实。
预审恼羞成怒,说道,给你机会你不说,那好,你就呆着吧!
袁克夫的心态有所改变了。前阵监号进来个人,叫鄂世宽,原是动力红旗畜牧场的党委布告,隔离反省期间私自回家,被押进看守所。进来时,就在门口大喊大叫,骂声不绝,说这是国民党的监狱。保卫组见其骂不绝口,影响恶劣,当即给他一顿修理。鄂世宽遍体鳞伤,仍旧不服,当天开始在监号绝食。绝食第三天,在押犯上报,两名管教进监,强行给他喂食。鄂世宽激烈反抗,谢绝进食。马管教想了个办法,拿着玻璃瓶装着加盐的苞米茬子粥,由管教掐住他嘴巴,瓶子伸进嗓子往里灌。这样持续了十多天,造成他的嗓子发炎,接着高烧不退。一天,鄂世宽在监内来回走动,有个在屯子生活过的犯人向袁克夫报告,说鄂世宽的举头纹开了。在屯子有种说法,举头纹一开,预示这人离去世不远了。袁克夫让他赶紧向管教报告,正在表面打扑克的几名管教进来,鄂世宽已经晕厥倒地,送到医院后不治身亡。前后不到二十天,一条鲜活的生命就在面前消逝。袁克夫心想,这都是由于啥屁大点事,弄得一命归西,跟自己的事比起来,不值一提。
人与人就在互比较较中寻求慰籍。每想到这,袁克夫便不再抱怨了。
半年后,两个表情冰冷的年轻军人将袁克夫提了出去,个中一个军人让他靠墙站好,从各个角度照了三张像,然后就把他送了回去。
袁克夫整不明白他们究竟要干啥,提及这事,七监的人也如堕雾中,剖析不出以是然。思来想去,都认为是保卫组采纳的手段,索性还是横下一条心,以不变应万变,爱咋咋地了。
第二天,监门响起。“57号!
”杨管教进监门喊着袁克夫的编号,要提审。
审讯室内,端坐着初次审讯见过的两位老相识。
“怎么样?袁克夫,瘦了不少啊。”,戴眼镜军人面带笑荣率先发言。
“这暗无天日,能活下来就算捡着了。”,袁克夫回应着他的冷嘲热讽。
“纯属放屁!
你说这话,便是反革命!
什么叫暗无天日?”,黑脸军人一如既往的严厉,张嘴就上纲上线。
“跟反革命有啥关系,号里便是没有阳光,吃不饱,也没有水。”,袁克夫心知,人要整你,辩白毫无意义。
“国宴好吃,你配么。”,黑脸说。
“你家人给你拿的罐头,原封不动的给你了,我们对你仁至义尽了吧。”,眼镜军人看着袁克夫,打感情牌。“好好把你的事交代清楚,你通缉令也下来了,家里老太太也千里迢迢来看你,”,眼镜慢条斯理的喝了一口水接着说“你就不想见见面?”。
“通缉令?公安部发的?还是公安厅发的?”袁克夫心中暗笑,还整出个通缉令,切实其实便是胡说八道,军人的审讯手段倒底和专业的公安相差甚远,他直视眼镜军人,猜不透这副眼镜后面那双闪烁不定的眼神,他只能胡乱接下这个话头。罐头肯定是徐波打听到自己折进了太平,想办法送进来的。他在表面肯定千方百计打探自己的,太平看守所出出进进这么多人,徐波要有什么好对策早就通过渠道通报进来。这么久了,一点没有,解释徐波也没有节制太平保卫组到底要如何处理这样一个打掉了一把手牙的人。这个肖大组长肖大胡子到底要怎么样?
现在又把远在山东的老娘提了出来,这绝对是天方夜谭了。这个小脚老太太便是走出山东,也得先去长春的姐家。但也由此可见,太平保卫组也真对自己下了功夫,这个肖大胡子每照一回镜子,恐怕就会对自己增一分恨意。死活有命,目前只有咬定青山,绝不放松了。
审讯持续五六个小时,沉默,对峙,软硬兼施,末了,在呵斥和诅咒声中结束。没有完成预期任务的两名军人朝气不已,挥手让人带离袁克夫。
这次时隔六个月之久的审讯就这样结束了。袁克夫算了一下,押在太平看守所已近十个月,这种没有结果的等待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又从黑脸口中得知,太平保卫组又一次的谢绝“老店”追捕队来此提他。他不知道,这一系列的审讯手段,都出清闲部队学过生理战,太平军管组二把手方正的主张。冷处理,遥遥无期的等待能引起人的巨大惶恐、焦虑,就会引发崩溃。崩溃后,就能主动交待罪过,当然不止是打伤肖组长那一件罪过,案犯由此获取重刑。
在回七监的路上,袁克夫觉得像在走向深不可测的无底洞,近乎绝望的心情又让他感到沮丧,方正的生理战显出了效果。方正所不知道的便是,袁克夫有乐不雅观的天性和顽强生存下去的决心,历经磨难养成的耐力也让他和内心绝望的争斗中逐渐霸占了上风,屡次在崩溃的边缘挽救了自己。
进监号之前,袁克夫迅速调度了一下心态,他不想让监号里的人,看到自己满脸颓废的表情。迈入监门,他觉得气氛有些非常,铺上多了一人,头枕在双手上,四仰八叉的躺在那,两条毛茸茸的粗腿微微抖动着,脚踝处戴着一副大号脚镣。头大如斗,浓密头发下,一双苗条的三角眼半张半合,满脸的络腮胡子,粗壮的手臂上带了付捧子。袁克夫扫了那人一眼,脚步未停径直往里走,脑筋里电光火石的飞快运转,这人太熟了,猛然间想不起来是谁。走到里面坐下,也想起来了,这个人是王军,一起在福安农场改造,还和他发生过争执,是个极度难缠的人物。
袁克夫刚一坐下,坐班的“三瞎子”就凑过来低声说,不知道搁哪来了这么个玩意而,一进屋就找事,又喝水又干啥的,完后就打起来了,“土球子”和“杨疤楞”都受伤了。接着杨管教进来了,说不能伤着他,还得重点盯住他,不能让他失事,我看这小子他么的怎么这么狂。
袁克夫点点头说我认识他。
这时,手脚都戴着桎梏那人挺身而起,晃晃荡悠的向袁可夫走来,边走边说:咋,山东,不认识我了?你咋搁这呢。
王军眯着眼睛,监号里一举一动都看的清清楚楚,袁克夫刚进屋,他就认了出来,隔了一会就凑了过来,一扒了南岗的“大果子”,说,你去阁下那呆会,我俩唠会嗑。
“大果子”横目而视,他不知这人和袁克夫啥关系,不好产生发火。
“这是福安的老相识,叫王军,你先去吧,我俩说会话。”,袁克夫顺带着跟监号里的人先容了一下,那些人倒是没听过哪有这么号人物。
“啥事进来的?山东。”,王军拎起袁可夫的手,象征性的握了一下,顺势坐在了阁下。
“我这事不值一提,看你这架式,事不小啊,先说说你吧。”,袁克夫握了一下王军戴的手捧子。
王军腿往铺板上使劲一蹬,把后背牢牢靠在墙上,腿伸开伸展了一下。
袁克夫斜眼看了他一下,这个王军还是那么大了呼哧。
王军把手搭在了肚子上,紧锁眉头,说,我这把事整不好要大了,黄茂良,孙敏,梁世信,何大轮子,油葫芦罐子都进来了。也他妈怪了,这七个监,恰好一人一个屋。
王军提的这几个人,都是道外有名的人物,七监很多人都有听说过。袁克夫和这些人都认识,只不过道不同不相为谋。
王军这一团伙犯下了三天抢劫四起的特大案件。
王军,辽宁阜新人。几年前在福安农场良种分场〈一分厂〉带排时和袁克夫认识,他是辽宁省摔跤冠军董玉山的大弟子,同时又精通拳击,和拳击高手蓝宏生是哥们。1966年文革开始后,在沈阳和“臭炮”团伙呼风唤雨兴风作浪了好一阵,“臭炮”团伙覆灭后来到哈尔滨。
袁克夫在福安农场改造时,深知这个王军心狠手辣,狡猾多变。城府极深的王军没有一句实话,且听听他怎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