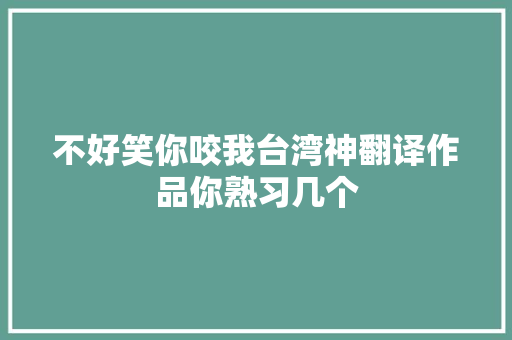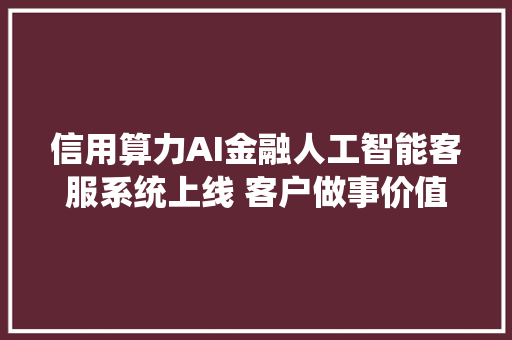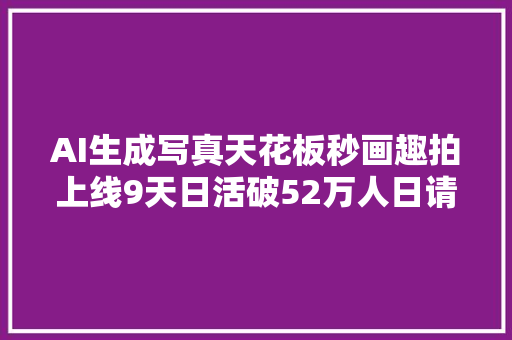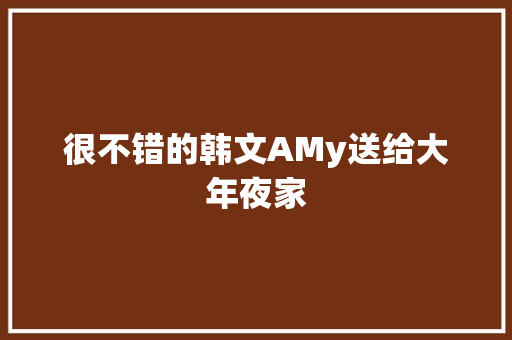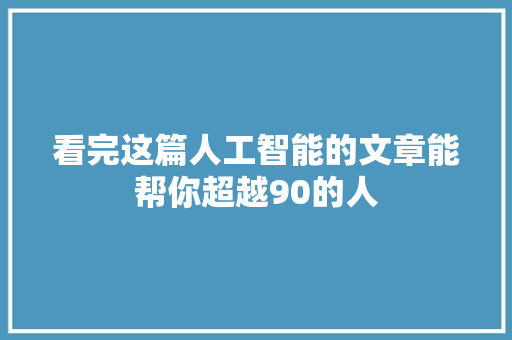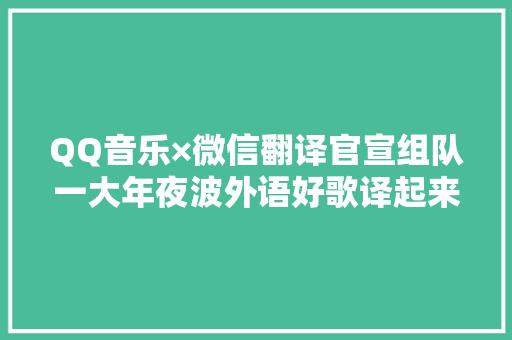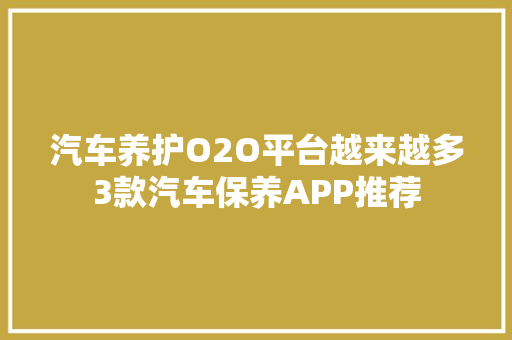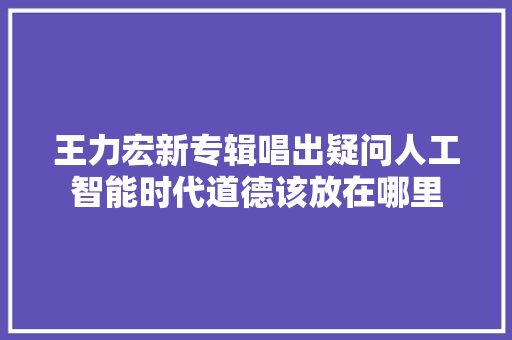米兰·昆德拉、村落上春树、JK·罗琳、伊恩·麦克尤恩和勒克莱齐奥,或许很难坐在一起聊聊他们各自的作品,但是,通过翻译将《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挪威的森林》、《哈利波特》等一系列精良外国文学作品带入海内大众视野,使其成为广大读者可共飨的译作者们或容许以。
前天,浙江大学中华译学馆特邀毕飞宇、林少华、马爱农等海内十余名著名作家与文学翻译家作客“文学翻译名家高峰论坛”。

译者最好和作者不要相见
与其相见不如暗恋
作家毕飞宇对付文学翻译给他的作品带来的影响,深有体会。他回顾道,2012年他在喷鼻香港领取英仕曼亚洲文学奖的时候,在场的一位CNN走上前来祝贺他,并夸赞他的获奖作品《玉米》措辞十分精妙。“所谓措辞非常好,我想一定不是指汉语版的《玉米》,而是英文版的。”他认为,《玉米》之以是能受到英语天下广大读者的喜好,跟好的翻译是离不开的。
同时,作为一名读者,他认为“翻译是母语的分外写作”,译者们在进行文学翻译时可以在忠于原作的根本上保有个人风格。“我17岁时读到傅雷翻译的《约翰·克里斯多夫》,当时我以为罗曼·罗兰的笔墨便是那样充满激情又具有空想主义色彩的,那种措辞风格深深地吸引了我。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我才从现在浙大译学馆馆长许均教授那里知道,那不是罗曼·罗兰原有的风格,而是傅雷的翻译授予她的。虽然大吃了一惊,但我创造我是接管的,我乐意通过傅雷独具一格的翻译来理解罗曼·罗兰的作品。”
“文学翻译中,为了保留一些东西势必是要舍去一些东西的。二者如何达到平衡,是翻译的艺术。”因翻译村落上春树《挪威的森林》而被广大读者熟习的林少华认为,文学翻译属于再创造的艺术,重视创造性的同时也不能忽略对原著的虔诚性。“以严复的‘信达雅’言之,信,即内容充足、语义虔诚;达,即行文虔诚、文体虔诚;雅,即艺术虔诚、审美虔诚。”他提到,就文学翻译中的形式层,风格层,审美层三个层面来说,审美层最为主要。纵然译作者自身的风格对原作来说有小小的“叛逆”,但审美层也是“不可叛逆”的文学翻译之重。
浙江大学翻译学研究所所长郭国良则提出了一套有趣的“暗恋理论”来论述译者和原著作者之间应有的关系:译者最好和作者不要相见,与其相见不如暗恋。“文学翻译从某种角度上来说,也是一种创作,必须诉诸于想象,包括对作者本人的各类想象。很多译者每每带着一肚子疑问想要去问作者,希望得到一个一锤定音的答案。”但是他表示,文学最大的魅力就来自它的暧昧性和丰富的解读性,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译者作为分外的读者,通过想象和翻译,传达的也是自己的一种解读与感想熏染。
人工智能为精良的文学作品翻译
可能不在其列
随着人工智能一起高歌年夜进,人工智能能否取代一些人类事情的话题愈演愈烈,个中翻译就被认为是首当其冲。拥有丰富英美文学作品翻译履历的《浙江日报》高等文敏提到,为了节省劳动本钱,现在的国内外翻译市场上,许多笔译员在做post-editing,即机器翻译的译后编辑。
“用机器来翻译大略句子效果或许不错,但是换做专业文本乃至是文学作品,翻译效果就不敢阿谀了。翻出来语法用词语义都乱七八糟,很多都须要推倒重做,编辑这样的文章还不如自己直接翻译来得快。”她认为,由于中英文在语法构造各方面差异甚大,目前机器翻译的水平能够达到的准确率还十分地低。
“人工智能翻译还只是个小baby,牙牙学语有几分可爱,以是大家对它也是称颂有加,但是据我们所能看到的未来,人工智能或许会摧毁底层很根本的一部分性翻译事情,但是并不能完备的取代人工翻译。”她也承认,人工智能的发展实在是太快了,说不定哪天它就会实现质的打破。
“鲍勃·迪伦曾和IBM公司的人工智能系统Watson进行过一场‘发言’。Watson对迪伦说:‘鲍勃·迪伦师长西席,您的歌曲中反响的是两种感情——流逝的光阴和枯萎的爱情。’随后,再通过无与伦比的推理判断能力,揭示海量歌词背后‘爱与痛’的含义,以及和主题之间的模式与关系。这让迪伦大受震荡,他以为人工智能机器竟然已经能够感知人类细腻繁芜的感情了。”实在,这是基于Watson的后台中有一个弘大的歌曲数据库和认知系统。Watson在研究了很多类似的村落庄音乐后,再去剖析鲍勃·迪伦歌曲中表达的感情。
文敏认为,人工智能不是在理解措辞,它只是在不断地编码与解码。它无法拥有像人类一样思考、创造、搞怪、愉快、恐怖、期盼等感情。它也无法像翻译者们在翻译伟大而精良的文学作品时,用眼睛、措辞、心灵同时追逐着作者的思想,在悲哀处与其一起悲哀,恐怖处一同害怕,思虑处随之自问自答。“对付人工智能翻译来说,一样平常的翻译可能不在话下,但是能够称之为精良的文学作品翻译可能不在其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