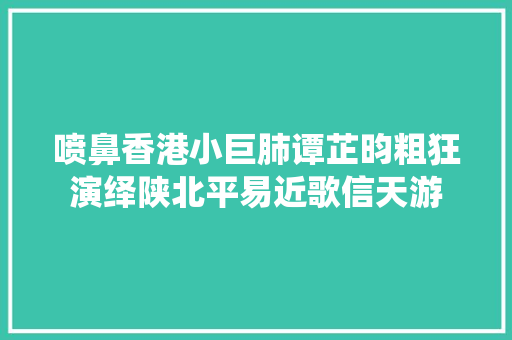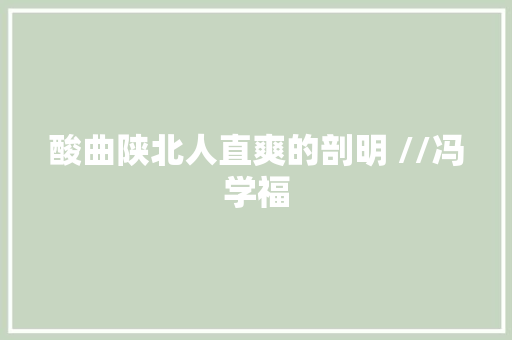“陕北歌王”王向荣,这句话包含了两层意思:其一是指他的籍贯;其二是指他在陕北民歌这一艺术领域里取得的造诣。事实上,从艺数十年的王向荣的影响及名声早已超越了陕北这一地域的局限,在不少威信媒体上他还被誉为“西部歌王”。2008年,王向荣被文化部公布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陕北民歌代表性传承人。
王向荣演唱的民歌都是老歌,有的乃至可以说是很古老的歌。这些歌经由王向荣的演唱依然能征服生活在当代的听众,究其缘故原由,首先在于这些民歌具有可以穿越时空、直击人性深层的力量;其次在于他天才的独具个性的表达。真正从事艺术的人对艺术创作的自由都有一种渴望,陕北民歌中的信天游实在便是蕴涵着想唱就唱,想怎么唱就怎么唱的一种自由创作的艺术精神。王向荣是一位在民间艺术的滋养下发展起来的歌手,他正是从陕北民歌所蕴涵的自由创作的艺术精神中得到启迪,在长期的艺术实践中,逐渐形成了自己既激情亲切旷达、高亢通亮,又悠扬圆润、深奥深厚雄浑的独具光鲜个性特色的演唱风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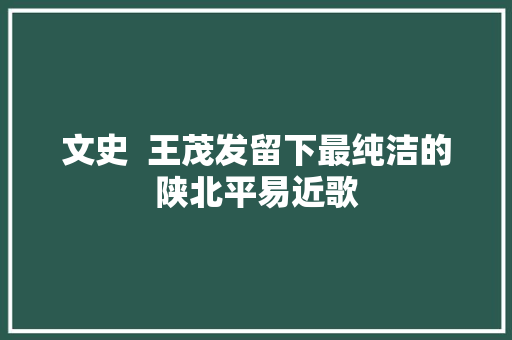
母亲是他最好的老师
1991年前后,电视记录片《望长城》的播出使得已经成为榆林民间艺术团专业歌手的王向荣有了更大的有名度。这部记录片共四集,个中“长城两边是故乡”这一集便是环绕王向荣的故事展开的。1952年,王向荣出生在榆林市府谷县一个叫马茹则圪垯的小村落庄。这里地处塞上,站在村落外的山头上向北望去,就能看见山脊上蜿蜒连绵的长城。王向荣母亲的外家就在长城的北边,属于“口外”;而他的父亲,一个要强、寡言的陕北男人为了养家糊口,一度常年去“口外”,到地广人稀的内蒙古打工、做生意。在王向荣十二三岁时,父亲由于过度劳累以及缺医少药而撒手人寰,抚养王向荣的重担就落在了母亲瘦弱的肩上。
在记录片《望长城》中,我们真实地捕捉到了王向荣母亲的动听形象。这是一个个子矮小、长着一双小脚、步履蹒跚的老人,也是一位爽朗、倔强、深具爱心的母亲。
王向荣
作家牧笛在一篇题为《王向荣的歌》的文章中对王向荣的母亲有一段生动动听的先容笔墨:“看过纪实电视片《望长城》的人都忘不了那个镜头:在荒凉光秃的黄土山上一孔古旧的土窑洞里,走出一位七八十岁的老婆婆。她站在土院里,那肤色那神态那衣着,让你立即觉得到她切实其实就像个黄土疙瘩。随着镜头的推移,当你看到她也会唱歌儿,并有腔有调的;她也会捏面人儿,还把几个面人儿交给采访职员,要他们捎给自己的儿子……这时,你会不由得眼睛湿润起来。她便是王向荣的母亲。王向荣便是在这样一个地方由这样一个可亲可爱的‘黄土疙瘩’里生养出来的。这个地方和陕北其他许多地方一样,自古以来人们就爱闹秧歌唱民歌。”
生平从未踏出过黄地皮的母亲,善良、勤恳、俭朴,却饱受贫寒生活的煎熬。这不仅影响到王向荣为人处世的品性,也使他从小就有了改变命运的强烈欲望。同时,爱唱歌的母亲还成为王向荣走上艺术之路的主要启蒙者。王向荣成名后,多次说到母亲的功劳。他说:“我妈便是我最好的老师。”
王向荣的哥哥王尚荣回顾说:“弟弟五六岁的时候,坐在母亲怀里就能随着母亲唱出持续串的民歌,有《打马茹茹》《十对花》《摇三摆》《种白菜》《妇女翻身》《禁洋烟》等。到了七八岁时,弟弟随着父亲去放羊,上山后就歌不离口,像《五哥放羊》《走西口》《梁山伯与祝英台》等都会唱。”
一次,王向荣接管笔者采访时,习气性地盘腿坐在宾馆的床上,一边吸烟,一边讲述有关母亲的故事。后来,他像是累了,斜靠在床头上,开始轻声哼唱母亲曾教给他的童谣:
雁,雁,摆溜溜,
红衫衫,紫扣扣;
我在你家房檐上捡豆豆,
捡了一碗两袖袖。
哦哦,睡睡,
猫儿打盹盹
狗儿烧火火,
鸡儿捏窝窝,
捏的两疙瘩糖窝窝,
气得我老命不吃,
撇在那锅盖上……
王向荣从心底流出的歌,舒缓、柔柔,具有一种沁人心脾的力量。他在影象深处捕捉到的是什么?这不止是歌,而是一种温暖,更是一种留恋。我感到这仿佛不是他在唱,而是他又依偎在母亲温暖的怀里,听母亲吟唱。他停顿了一下子,说:“我妈会唱的童谣特殊多,我记得的几首只是常常唱的。”
向民间学习
父亲病故后,又逢“文化大革命”中“武斗”开始,王向荣无法连续完成学业,只好告别在府谷中学的求学生活,回到家里。1969年至1975年,他担当民办西席,其间辗转于五六个村落庄学校之间,每年有60块钱的收入。
当西席虽然收入不高,但在事情实践中却提高了王向荣的文化素养,还能使他分开繁重的体力劳动,有比较充裕的韶光学习民歌。
王向荣来自民间,乐于靠近民间艺术以及那些安分守己、苦中作乐的民间艺人。他在民间艺人身上看到了艺术的神奇和力量——一个平时或许满脸苦焦的男人,在演出时喜形于色的神色便是一种诱惑。在当地还有一种被称为“打坐腔”的演出。这是一种逢年过节时群众自娱自乐的文艺演出,险些村落村落都能见到。有了些名气的艺人,还可以走村落串乡演出,获取收益。王向荣很喜好这种土生土长的“打坐腔”演出。哪里有庙会,他就往哪里走,存心于对民间艺术和民间艺人的追寻。
在当时周遭几十里最为有名的民间艺人就数孙斌了。孙斌住在府谷县一个叫温庄则的村落庄里,间隔马茹则圪垯有20余里。1972年冬,20岁的王向荣决定拜师学艺。他提着烟酒去拜访孙斌。当时孙斌已有80岁高龄。他个子不高,容貌清瘦,留了一把白胡子,精神依然矍铄。他的老伴与他同龄,也很康健。
孙斌老人对王向荣的来访非常高兴,当即就爽快地答应了王向荣拜师学艺的哀求。孙斌和老伴住着一孔很大的土窑洞,炕也大。王向荣就住在老人的家里,与老人朝夕相处,潜心学艺。外边天寒地冻,窑里的炕却烧得很热,老人就在舞台般的大炕上传艺。有了师傅,就像又有了一个家。拜师往后,连着几年冬天,王向荣都要到孙斌老人家里住几天。经由一段韶光的学习,王向荣已经能和老人互助演出了。虽说演员都在炕上,但演出却十分负责,一丝不苟,而现场唯一的不雅观众便是师娘。
王向荣和师傅最乐于演唱的节目,是为当地群众喜闻乐见的秧歌剧《钉缸》。他们一人一句唱得有条有理:
一个鸡蛋两头光,
一母生下三个郎。
大哥他学了一个铁匠艺,
二哥他学了一个盖木房,
所生下三弟我年纪小,
自幼儿学会巧钉缸。
别的活儿我不讲,
担上个担儿走四方。
正行走来用目看,
不觉来到王家庄。
担儿放在溜平地,
高叫一声钉盘钉碗又钉缸……
在孙斌这里,王向荣学会了《打樱桃》《耍半子》《吃醋》《听房》《扇子记》《软糕面》《走西口》《珍珠倒卷帘》等几十首二人台和传统陕北民歌。王向荣一贯客气向民间艺人学习,但正式拜师这还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他由衷钦佩孙斌师傅的人品、艺品。时隔多年,他在回顾当年学艺的情景及师傅与师娘相濡以沫的情绪时,说:“他们老两口一辈子都没有盖过两床被子。我师傅记不起来的词她记住呢。她说,哎,那词不是这样。她还给我师傅递词呢。师傅去世的第三天,师娘也走了。埋的时候,两个人是一起埋的。”
走向成功
在丰硕的民间艺术环境里,王向荣厚积薄发,在1977年终于迎来了崭露锋芒的机会。这一年,他所在的新民乡举办了一次文艺汇演,他自我介绍,登台演出,一曲唱罢,高亢洪亮的歌声竟然通过高音喇叭传到10里之外的马茹则圪垯村落。戏台下的不雅观众更是为之沸腾。紧接着,他到府谷县城演出,同样一鸣惊人。
1978年冬天,为了参加榆林地区文艺汇演,王向荣和府谷县代表队的演员们每天都要紧锣密鼓地进行排练。王向荣的差错杨玉娥本是一位性情泼辣的女民兵队长,在她面前王向荣总是束手束脚。年轻姑娘为此不满,责怪说:“你这样扭摇摆捏,连手都不敢握,咋能练好呢?人家常演戏的,这种情形见得多了。你干脆不要参加排练,回家算了。”姑娘的快言快语如醍醐灌顶,让王向荣这位业余演员对舞台演出与生活的差异有了全新的认识。排练结束后,王向荣满怀信心地参加了榆林地区文艺汇演,他演唱的《五哥放羊》荣获一等奖。1980年,他代表陕西省到北京参加全国农人文艺调演,演唱《兄妹赶集》得到都城不雅观众和专家的高度赞誉。
王向荣在艺术舞台上一起辉煌,成为演唱陕北民歌最为精彩的代表人物之一。1984年,榆林民间艺术团成立时,王向荣得到时任榆林地区文化局局长尚爱仁这位“伯乐”的赏识,被破格招入艺术团成为一名专业歌手。据尚爱仁回顾说:“当时会上有辩论。张有万、李增恒、王向荣都超龄了,是否招收他们进入艺术团,年事成了一个挡在他们面前的门槛。我坚持说这三个人不进来,民间艺术团就不要成立了。如果没有这三个人,精华就没有了。”尚爱仁还写过一组赞颂陕北民间艺人的顺口溜。个中赞颂王向荣的顺口溜是:
拦羊后生王向荣,
生来一口好嗓音,
高亢圆润吐词真,
府谷唱到榆林城,
西安唱红进北京,
拍罢电视上电影,
羊倌变成了大名人。
成为专业演员后,王向荣演唱陕北民歌在艺术上更臻完美,演出活动也更加频繁。全国许多主要的演出都有他的歌声。他还把陕北民歌带到天下上很多国家,让外国朋友领略了陕北民歌的艺术魅力。2006年,中国唱片总公司推出《“陕北歌王”王向荣》演唱专辑。这个专辑的录制是50多年来该公司在制作理念上的一大打破,也可以说是书写了中国唱片史上的一条新记录。民间音乐专家乔建中在这张专辑的出版手记中指出:“本专辑收入的30多首陕北民歌,没有一首不是王向荣几十年来从前辈那儿学来的,但又没有一首是原封不动地模拟。一词一调,一抑一扬,都倾注了他创新精神的血汗。”
王向荣歌声的魅力所在,或许对付每一个听众都会有不同的理解和感想熏染。但是对付王向荣来说,他认为自己的歌声之以是能够打动万千不雅观众的心灵,最主要的是“要用情”。他常说:“我唱歌便是要用情唱,唱出老百姓的喜怒哀乐,唱出老百姓的酸甜苦辣。”
留下最纯洁的陕北民歌
在谈到传承问题时,王向荣说:“一定要留下最纯洁的陕北民歌。”为此,他把培养年轻歌手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任务。他提出的收徒条件是:一要发自内心热爱陕北民歌;二要有好的天赋;三要人品好。这三条看似并不苛刻的哀求,或许正是王向荣从艺数十年来最为实质的体会。
为此他苦苦探求了几十年,他常说:我不能把我学了一辈子的歌都烂到肚子里,但现在天分好,又乐意踏实学歌的好苗苗太少了。2008年11月,他首次招收冯晓红、李春如为徒弟,不久又收下周金平、张辽军。经由几年的考察,2015年6月24日,他再次招收王建宁、高琳、丁慧成、苏文、刘美玉、延锦园六名歌手为徒弟,并在西安举行了收徒仪式。
在收徒仪式上,他激动地说:“我热爱陕北民歌就像热爱自己的生命。我理解每一位徒弟的品行和特长。做我的徒弟首先要人品好,其次才是才艺。”他在台上颁布的师训是:做年夜大好人,把人做好;唱好歌,把歌唱好。
随后,山西歌手崇高鹏也行拜师礼,成为王老师的爱徒。
现在,王老师已过耳顺之年,只要表面没有演出,便在祖传授徒弟唱歌。他说:“我现在不求名,不求利。在我的有生之年,把最纯洁的民歌传给他们,是我的最大义务。我希望能与徒弟们结为一个团队,共同挖掘、整理、弘扬陕北民歌。作为这个非遗项目的国家级传承人,我不能眼看着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断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上。”
来源:各界杂志2021年第4期
作者:霍文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