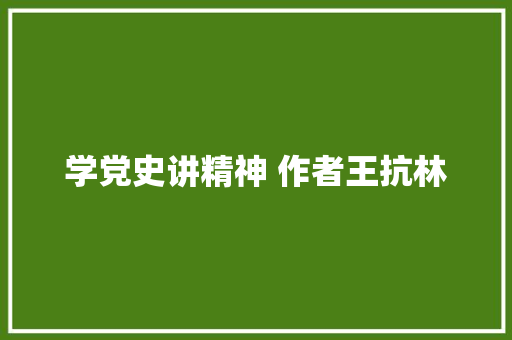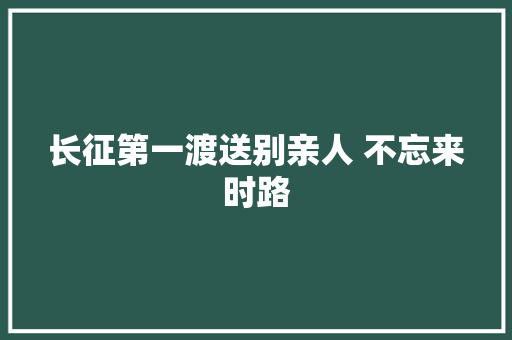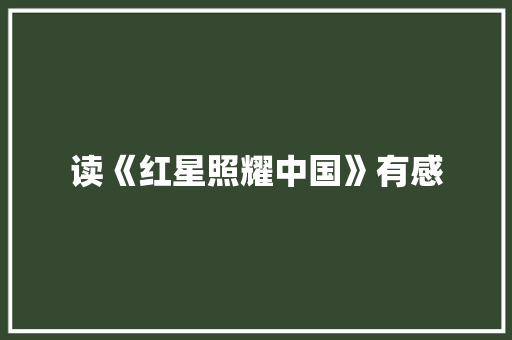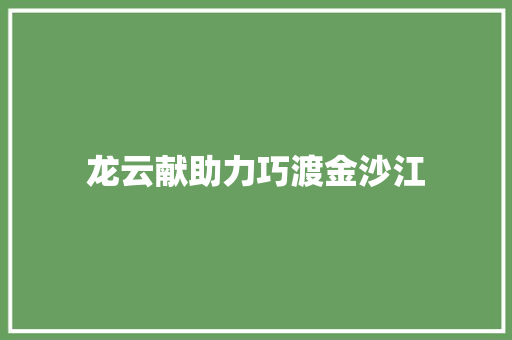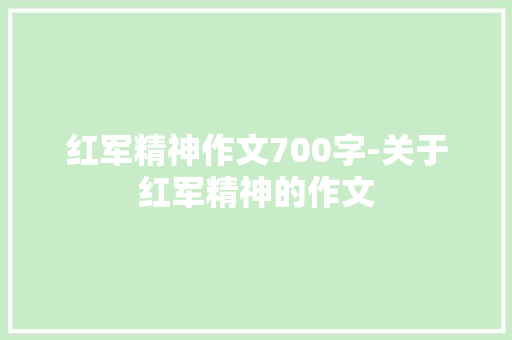谭冠三将军与夫人李光明
李光明(1921-2011),四川通江人。1933年5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四方面军。1934年入团,1937年入党。她是首批一千多名进藏女兵中,唯一经历过艰巨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和解放西藏“第二次长征”的女红军。她的范例业绩,是十八军乃至全军女军人中的典范!
她两次长征的壮举,称为“巾帼英雄”应是当之无愧的。她在共产党毛主席的领导下,为创建新中国、解放西藏和培植新西藏,舍弃母子亲情和家庭幸福,一不怕苦,二不怕去世,长期建藏,边陲为家,为解放西藏百万农奴和中国公民的壮丽奇迹奋斗贡献了生平。她是首批授衔为数不多的女校官中的一员,荣获了多枚勋章、奖章和纪念章。她永久是我心中的英雄母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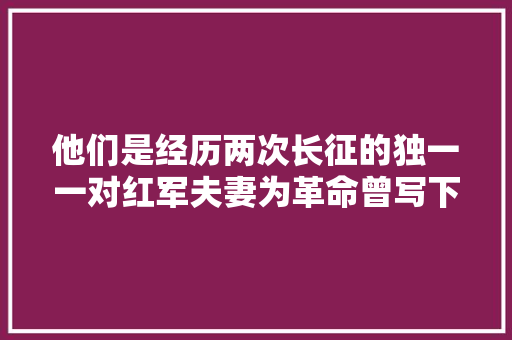
——谭戎生追思亲爱的妈妈
口述:李光明 整理:谭戎生
为纪念西藏和平解放50周年,我这个参加过两次长征的女兵心情万分激动。我因“文革”蒙难,患脑溢血瘫痪至今已30余载,加之年已八十,实感力不从心。但是,忆及两次“长征”(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和进军西藏)的伟大壮举,亲历那艰巨卓绝的奋斗征程,感想熏染那惊天地泣鬼神的壮烈捐躯精神,我这个革命已近70年的老兵仍禁不住心潮澎湃,难以沉着。“忘却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在全党、全国公民沿着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当代化道路开拓提高的本日,我感到有任务和责任将自己所经历的“两次长征”的一些情形先容给大家。一方面不断勉励自己,永葆革命青春。同时,也希望对青年一代有所启迪,为他们增长一份振兴中华的精神力量。
永恒影象1955年2月,中华公民共和国全国公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作出《关于规定勋章、奖章付与中国公民革命战役期间有功职员的决议》,我作为一名红军战士,被付与八一勋章和解放奖章。1988年,中华公民共和国中心军事委员会又付与我二级红星功绩名誉章。当我接管金光闪闪的勋章、奖章时,我的心情久久不能沉着。想到在长征路上爬雪山、过草地和在战斗中捐躯的战友们,想到那些因作战负伤和患病不能随部队一起提高而留在敌战区和老百姓家里的战友们,不知还有多少生存下来的;想到西路军两万多战士们大胆奋战,壮烈捐躯,特殊是那些为数浩瀚的被马匪蹂躏、残害的红军姐妹们刚毅不屈、惨烈捐躯的情景,我不由自主地流下热泪。我想,这些勋章和奖章该当付与他们!
他们是为国赴难、舍生忘去世的英雄!
他们永久活在我们心中!
1988年,李光明被付与二级红星功绩名誉章。
作为一个长征的亲自经历者,本日回顾长征的历史,亲切、激动、愉快的心情不禁油然而生。两万五千里长征已过去65年了,但是在长征中所经历的千难万险,红军战士所表现出来的大无畏英雄气概和不怕捐躯、打消万难、争取胜利的伟大革命精神,以及他们对党的武断信念,是永久值得怀念和弘扬的。我为能参加这一伟大壮举而感到无比的光荣和自满。历史已经证明,红军长征精神作为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已打破了时期和国度的界线,成为天下历史上一个壮举。在公民心目中树立了一座辉煌的永恒丰碑。
苦难童年1921年3月26日,我出生在四川省通江县华家坪一个贫雇田舍庭。母亲非常疼爱我,给我取了个好听的名字:华金喷鼻香。华家坪地处深山老林,交通不便,老百姓生活非常穷苦。在我出生时已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我只记得母亲带着我们过着十分清贫的生活。我从没见过父亲是什么样子,稍懂事时,母亲见告我,父亲外出谋生一贯没有音信,死活不明。后来有一天,哥哥上山砍柴也一去不返,不知是掉下山崖摔去世了,还是被野狼叼走了。家中的男人都没有了,母亲只好带着姐姐和我再醮到瓦室铺肖口镇一个姓李的农人家里。继父叫李炳福,靠给地主扛活为生。这时的母亲靠给人做鞋、绣花、缝补衣服困难度日。不久,母亲又生下一个小弟弟,生活更加困难。无奈之下,在我四五岁时,继父就把我送到跳上村落一个叫杨三生的家里做童养媳。在旧社会,童养媳实在便是家奴。在杨家,我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险些每天挨打受骂,干得是最脏、最累、最苦的活。杨家人一点人性都没有,我年纪小,不懂活计怎么做,只要干得不当,就挨一顿拳打脚踢。吃的是猪狗饭,受的是牛马累,睡的是草垛堆。冬天冻得浑身冰冷,夏天被蚊虫叮咬得体无完肤。在我6岁的时候,母亲患重病,卧床不起,家里只有姐姐和弟弟俩人。我听到后想回家看看,杨家便是不准,还是姐姐跑来向杨家再三央求才答应回去。待我与姐姐一起回到家中,母亲已经咽气了。姐姐扑到母亲自上痛哭起来,当时我和弟弟还小,都不知道哭,弟弟还闹着要吃妈妈的奶。母亲去世了,家里穷得连一文钱都没有,没有办法,姐姐只好背着弟弟,拉着我,到街上挨家挨户去乞讨,一些善良的人家看我们实在可怜,多少给一点钱。姐姐拿这些钱买了一口棺材,草草把母亲掩埋了。我送走了人间间唯一疼爱我的母亲后,又回到杨家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
在那暗无天日的旧社会,我每天盼着天亮,每天盼着天上的神仙、不雅观音菩萨下凡救我出苦海。可是,神仙在哪里?不雅观音菩萨又在哪里呢?
参加红军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主力离开鄂豫皖转战川陕边地区,开辟川陕革命根据地。我们通江和瓦室铺也来了很多红军军队。在我们住的跳上村落上街有一个红军后勤的被服总厂,个中有不少的红军女战士,我上山打猪草常常途经那里。开始的时候,听说红军来了,村落里的人都跑到山上躲了起来。杨家人威吓我说:红军都是强盗,红头发,青面鬼,捉住小孩会杀了吃人肉。起初,我心里也很害怕,不敢靠近红军。后来看到别的孩子都敢去,我就去问他们,红军是红头发,青面鬼吗?这些孩子都笑了,说红军可好啦,说话和气,还给我们饭吃哪!
这样,我才敢逐步靠近红军。和他们讲得一样,红军战士对我们穷苦人家的孩子非常和气,问寒问暖,宣扬红军是自己的军队,打土豪、分田地、求解放,还给我们白米饭和白馒头吃。由于常常打仗,我逐渐萌发了一定要参加红军的想法。后来,我常去红军那里的事被杨家人知道了,又遭到毒打和训斥。杨三生威胁我说,不许再去找红军,如果你要逃跑,就打断你的腿。当时,我咬着牙,忍着痛,一声不响,一滴眼泪不掉。但是,我心中更加痛恨他们,想参加红军的决心更加武断了。有一次我患病不省人事,杨家人起初根本不闻不问,后来听说红军按每户的人口分配地皮和地主财产,他们才急忙找来郎中给我开了几副汤药吃,我才逐步醒来逐渐好转。如果不是红军的这个政策救了我,我早就不在人间了。
1933年初夏的一天,驻瓦室铺的红军军队要转移到其他地方。杨家人知道了这个,怕我跑去找红军,一大早他们就把门锁了起来,不准我出去。我知道情形不妙,心中十分发急,可是又没办法出去,真是急去世人!
红军从我们住的大门口整整过了一天。直到快薄暮的时候,杨家人看到没有军队了,才放我出去打猪草。我急忙背上背篓,拿上镰刀,冲出大门,朝着红军行军的方向急奔而去。追了三五里路,仍旧没有红军的踪影。这时我心里真是凉了半截,以为希望变成了泡影,顿时瘫坐在山崖边,抱头痛哭起来。
不知过了多久,在我险些绝望的时候,模糊约约感到有人在说话,还有人轻轻拍我的肩膀。我猛然抬开始来一看,原来是四个红军女战士站在我的面前。我以为是在做梦,用力揉了揉眼睛,定睛一看,确实是四个女红军站在我的面前,她们都满脸笑颜地看着我。一个年纪稍大一点的女红军问我:“妹娃子,天都这么晚了,怎么坐在这里还不回家呀?”我鼓足了勇气大声说:“我没有家,我是人家的童养媳,我要参加红军!
”女红军对我说:“你年纪这么小,怎么能参加红军呢?红军要打仗、行军,要吃好多好多的苦!
”我说:“吃苦我不怕!
你们红军是大年夜大好人,我一定要参加红军!
”她们问了我的出生后,都很同情我。对我说:“好妹妹,你要参加红军也要给雇主打个呼唤啊!
”我说:“便是雇主不准我去找红军,如果去打呼唤,我就走不成了。”她们又商量了一下,说:“好妹子,你可不要后悔呀!
如果真的下了决心,就跟我们一起赶部队吧!
”我一听赞许我跟她们去追赶红军军队,顿时高兴地跳了起来,把背篓一丢,把镰刀高高地抛向天空,彷佛解脱了绑在身上多年沉重的枷锁。我一边跑,一边跳,仰面望着蔚蓝色的天空,年夜声大叫:“我参加红军了!
我终于参加红军了!
”四个女红军和我一样高兴,我们唱着、跳着、笑着,欢畅地向红军大部队行进的方向奔去。
我同四个女红军走了两天两夜,过了通江河的茅芋镇,第三天赶到通江的南岭才追遇上大部队。在这期间,曾碰着许多熟习我的乡亲、邻里,他们都劝我不要离开杨家去参加红军。但我参加红军的决心已定,根本不去理会他们。在红军大部队里,我惊奇地创造,有许多像我这样的苦孩子,我们女孩子都被分配到总被服厂(后改为工兵营)。我被组织分配在工兵营里做交通情报员事情,由于通江是我成长的地方,道路很熟习,过仇敌的防区和封锁线时,仇敌来盘查,我一口的通江话,仇敌根本不防,如有主要情报,我就过大山走小路,一天要走几十里的来回。在工兵营中,我虽然很小但很精明,也很努力,在营里也有点小名气。营长林月琴(罗荣桓元帅的夫人,她是从鄂豫皖转战来川陕根据地的老红军)非常关心我们这些新到红军军队里的女娃娃兵,大家都很尊重她,叫她“林大姐”。林月琴同道把稳到我事情很专心用力,也理解到我出身贫寒和做童养媳的痛楚经历,对我特殊关心、爱护,把我调到她身边做勤务事情。从她那里我知道了好多关于红军的故事,懂得了不少的革命道理。林大姐还教我识字,学习文化,并给我起了一个名字:李光明。从此我就改叫李光明了。自从参加红军,我感到心里特殊充足,特殊高兴,我是真正盼到光明了!
红军在川北地区常常同当地的军阀作战,每逢战事,我们工兵营和其它后勤单位都要向安全的地域转移。我们工兵营常常向山里的寨子转移,有时行军中常常与通江河对岸的仇敌不期而遇,乃至隔江交动怒来。有一次转移作战时,我受了伤,还是林大姐亲自派人把我送到二分医院(沙溪嘴)治疗。病愈后,我又回到林月琴同道身边事情,后来林大姐为了培养我,把我送到总卫生部总医院剧社做宣扬员,同时学习照顾护士知识。也是在这时,我离开了林大姐,直到长征到达延安后我们才见面。1934年底,我在二分医院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当时才13岁。
红四方面军在川陕开辟根据地,同国民党军队和当地军阀势力作战,取得了粉碎敌军六路进攻的重大胜利。同时,积极发动群众,建立苏维埃政权,扩大军队,红军扩大至八万余人。最初战事取得了节节胜利,嘉陵之降服利之后,接着横扫了嘉陵江和涪江之间的剑隔、昭化、梓潼、彰明(今江油)等十余座城镇,经茂县、理县到达懋功地区。
红一方面军在1935年1月占领遵义城后,召开了中心政治局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缺点在党中心的领导,初步确立了毛泽东同道在红军和党中心的领导地位。在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红一方面军四渡赤水、南渡乌江、进军云南、巧渡金沙江、勇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于6月到达懋功地区同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从而粉碎了蒋介石消灭红军的狂妄操持,壮大了红军的力量,鼓舞了胜利的信心,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两大主力会师后,中心政治局两河口会议确立了两军共同北上,在川陕甘创建根据地的计策方针。会后,毛主席率领红一方面军于6月下旬动身,翻越梦笔山、长板山、打鼓山等大雪山,到达松潘附近的毛尔盖。在毛尔盖勾留了1个月,毛主席一壁命令部队筹粮,准备过草地,一壁耐心等待张国焘北上。中心政治局在毛尔盖召开会议,决定兵分两路北上。右路军由党中心、毛主席率领,左路军由朱德总司令、张国焘率领。右路军穿过草地,向班佑、巴西、阿西一带提高。左路军由卓克基出发,经草地向阿坝、班佑一带提高。这是我第一次过草地。但是到了阿坝后,张国焘进一步暴露了他分裂党、分裂红军的野心,竟自主伪中心,向中心发电报,要右路军全部南下。中心虽曾八次去电,指出只有北上才是出路,纠正其南下的缺点。但张国焘不顾中心指示,擅自率领左路军及右路军中原属四方面军的两个军,回过分南下,再过草地翻雪山,经毛尔盖、懋功、宝兴等地向川康边疆的天全、芦山一带退却。在桌木碉,张国焘公然宣乐成立伪中心,自己担当主席。四方面军在天全、芦山一带勾留了3个月。这时,敌中心军周浑元部入川,与刘湘合营向我进攻。两军对峙,仗越打越大,部队花费很大,张国焘被迫撤向道孚、炉霍、瞻化、甘孜和大金寺一带,仍企图向青梅、西宁方向逃跑。这时,红二方面军长途转战,千辛万苦,来到甘孜。经朱德、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等同道的艰巨事情,加上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纷纭哀求北上,张国焘才被迫取消了伪中心连续北上。由甘孜出发再次爬雪山过草地(第三次过草地)经东谷、阿坝、色座于8月到达甘南,盘踞哈达铺、大草滩、临潭,于10月尾到达甘肃会宁地区与一方面军会合。三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结束了长征。张国焘的缺点,给红军和党带来严重丢失,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倍受艰辛,对此我感想熏染极深。
在红四方面军一年零七个月的长征和西渡黄河的前一段,我一贯是随红四方面军行动。在总卫生部、总医院和妇女独立团任剧社社员、宣扬员、卫生员和战士,从事文艺宣扬事情、救护伤员事情及行军作战任务。我们宣扬员的任务是十分繁重的,不但要和其他战士一样背背包、扛枪行军,还要在部队安歇时,放下背包,敲罗打鼓、唱歌、说快板、喊口号、鼓舞部队士气,而且在行军途中,我们还是一样沿途为同道们唱歌、喊口号,以减轻疲倦,加快行军速率。
在长征途中,由于战斗频繁,救护伤病员的任务十分繁重。像我这样的女红军战士,年纪小、体力差,要8个人分组轮流抬一副担架和伤病员一起行军。我们的脚磨出血泡,肩膀也磨得红肿流血,但大家仍旧咬牙,忍着疼痛坚持。我们翻越的几座大雪山有的海拔竟达六千多米,十分寒冷,行军前虽然作了些准备,但仍抵不住寒冷。在藏区,上级哀求每人完成二两羊毛的纺线任务,没有纺织机,大家就向藏民学习用手捻毛线。同道们加班加点起早贪黑赶任务,坐累了就站起来活动一下,困了就用冷水洗把脸复苏一下连续干。毛线捻好了,又没有织毛衣的机器,大家就互教互学自己来织毛衣,终极还是完成了任务。我们女战士的任务更重,除了自己穿的,还要为部队织毛衣。许多女同道都是在那个时候学会了织毛衣。便是这样,部队的御寒能力还是很低的。战士们把棕树上的棕毛撕下来,絮在单衣里御寒。用未经熟制的牛羊皮做背心穿。
部队冒着风雪寒冷和高山缺氧,顽强地向雪山挺进。在山脚下还是晴空万里,到了半山腰,天空会溘然乌云翻滚,狂风大作,大雨倾泻而下。到了山顶,大雪夹杂着鸡蛋大的冰雹,来源盖脸砸下来,砸得人浑身疼痛难忍,许多战士受了伤。当时我随身背着一个脸盆,碰着下雨、雪雹就把脸盆扣到头上,这样头就安全多了。这个脸盆随我走完了长征路,既用来洗脸、洗脚,又用来烧水做饭,是立了大功的!
我们许多指战员因受伤受冻,经不住恶劣景象的煎熬而倒在雪地里,再也没有能够站起来。记得我们在翻越夹金山时,上到山顶天色已黑,又摸黑走了一段路,由于雪山大、路又滑,非常危险,部队只有就地宿营。不料天亮我们出发时,与我一同宿营的3位女战士再也没醒来,她们被风雪吞没了。想到昨天还活蹦乱跳的战友,过了一晚就捐躯了,心情极为悲痛,她们只有19岁,连姓名都没有留下。第二天下山的途中,我们又看到许多战友的尸首被埋在了雪地里,我们心里真是难过极了!
下山比上山还难以节制办法,身子总往下滑,一欠妥心就摔筋斗。后来大家就干脆坐到雪地上往山下滑。大家把这种方法叫“坐滑梯”。我们便是这样降服了梦笔山、夹金山、大雪山和党岭山等一座座大雪山的。
红军长征爬雪山(油画)
过草地更加困难,更加危险。红军北上必须经由数百公里的松藩草地。这一地区人迹罕至。举目四望,一片荒凉,没有人烟,没有树木,没有活气,那糜烂了的永久浸泡在污水中的野草,无边无涯。草丛下水沟交错,泥泞不堪,腐草覆盖的地表面十分松软,人走在上面“噗哧、噗哧”作响,就像走在摆动的浮桥上一样,挪动一步就扭捏几下,俗称“海绵地”。一欠妥心,脚跟就会陷进一堆抖动的草丛里,泥巴不仅滑,而且像胶一样沾,一旦陷进去,就会越陷越深,越向上挣扎,就会下陷得越深。碰着这种情形,便是近在咫尺的战友,也不能冒失地去伸手接济,否则会一起沉入潭底,造成更大的捐躯。我们眼睁睁地看到许多经由枪林弹雨磨练的战友,没有倒在仇敌的枪口下,而被这无情凶险的草原妖怪所吞没。
红军过草地场景图
茫茫草地景象变革无常。忽而迷雾重重,忽而风雨交加,忽而骄阳似火,忽而又漫天算夜雪。午前,毒热的太阳晒得人抬不开始来,全体草地像扣在一个巨大的蒸笼里,蒸得人们汗如雨下,连气都喘不过来。可是到了午后,会溘然阴云密布,刮起砭骨的寒风,乌云遮天,大雪裹着冰雹从天而降。我们连躲的地方都没有,浑身淋得透湿,冻得冰冷,全体草原变成了白茫茫的银色天下。由于恶劣的自然条件和环境,使许多体弱的红军指战员捐躯在茫茫的草地里。
沼泽地里溪流坑水各处,但水质恶臭,不能饮用。可是行军路上又饥又渴,实在难忍,许多同道因喝了这样的水,引起剧烈腹痛和急性痢疾,乃至中毒身亡。过草地最困难的问题是没有充足的粮食吃,只有挖野菜、挖草根,乃至把身上的皮带拿来煮着吃。前面部队许多人患了恐怖的腹泻和痢疾,吃进去的米粒和麦粒通过肠道渗出出来时还带着血污,后续职员就像麻雀一样,把这些谷粒挑捡出来洗净煮沸后,又狼吞虎咽地吃到肚子里去;乃至从马粪中淘洗出一点未消化的米粒来吃,这算是很幸运的!
而这种机会实在是太少了。吃了这些东西,到肚子里根本无法消化,肚子发胀,解不出大便,使人痛楚至极!
部队宿营,都是睡在连泥带水的草地上,草原和沼泽地里各处是蚊虫、毒蛇,咬得人浑身痛痒,起脓包,有的同道不慎被毒蛇咬了中毒捐躯。女同道生理上的痛楚就更没办法办理了,只有随它去,可以说,百分之百的女战士都患有妇科疾病。有许多同道没能够度过这些难关,头一天宿营时还活着,第二天清晨出发时,就站不起来了,也不能说话了。好不容易大家把他扶起来,可是又瘫倒在沼泽地里,再没有站起来。他们就这样默默地长眠在这茫茫无际的草原沼泽地里。
过草地我碰着最危险的一次是过一条湍急的河流。由于水流很急,大家就手拉手一字队形前后排开,涉水过河,我由于个子小,身体软弱,走到水流急的地方根本站不住,几次被冲进急流中,幸亏都被战友及时救出了水面。有一位骑马的首长看到这种情景,就骑着马朝我这里走来,他叫其他同道把我扶上他的马,坐在他的身后,把我驮过河去。后来才知道,他是我们红军医院的医官,解放后任解放军总医院的院长,叫蒲荣钦。
在爬雪山、过草地,转战川康边区数月艰巨斗争中,我们都是在人烟稀少的藏区行动。由于红军初到藏族地区,措辞不通,加之过去藏族同胞受国民党政府的欺凌,对红军也心存疑惧,乃至敌对感情很大。经由我们耐心的宣扬和实际行动的影响,害怕担忧才逐步得到缓解。我们从贫苦的藏族同胞那里征集到有限的粮食和畜生,办理了很大困难。我们第三次过草地时,有一对藏族夫妇主动为我们带路,直到把我们带出草地他们才返回家乡。
当我们走出草地的时候,同道们都欢腾起来,大家跳啊、唱啊,高兴极了!
可是相互打量对方时,谁也认不出对面的同道便是自己朝夕相处的战友了,由于永劫光的饥饿,已经使人变形了。你看我两眼深陷,面黄肌瘦,皮包骨头,破衣烂衫,我看你也是一个样子。大家相互拥抱在一起,流出了激动的热泪。大家感到,是党中心、毛主席把我们从张国焘的缺点路线里拯救出来了!
同道们深深地感到,是红军的阶级友爱、官兵同等和钢铁般的意志,降服了千难万险;是对共产主义的武断信念和对党的无限相信,使我们从弯曲中迎来了胜利的曙光。我们从心底高呼:红军万岁!
共产党万岁!
走出草地往后,我们就来到一片空旷的大草原上,一眼望不到边,只有东面有一脉山岭。这时,我们有为数不多的骑兵侦察部队在前面巡逻开道,大部队都排开散兵队形向前推进。我骑兵侦察部队同马匪帮小股军队打响了,我们就顺势向山岭方向靠拢。走在山脊的波折巷子上,脚下面便是绝壁山溪,十分险要。碰着紧急情形时,就赶紧滑滚到山底躲避仇敌,趟着溪水连续提高。有时还要牵着牲口一起行动,躲过仇敌的追击和敌机的轰炸后,又向大草原方向行进。走出大草原,就到了岷县县城附近,部队集中全力去攻打岷县县城,我们就又投入到救护伤病员的战斗中。
攫取岷县县城往后,我们又连续北上到了甘肃的会宁,同一方面军会师,随后二方面军也到达会宁。1935年10月,一、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旋即在山城堡打了一个胜仗,消灭了胡宗南部一个师。红军胜利结束长征。
参加红四方面军长征到达陕北时的李光明
为了实现党中心确定的“西渡黄河,攫取宁夏,从北面打通同苏联联系”的计策操持,红四方面军在会宁进行了休整和部队整编。周子昆同道支持成立了第三个妇女独立团,又叫妇女先锋团,近两千余人。团长是红军中著名的巾帼英雄张琴秋同道,参谋长是彭真(女)。整编时我也被编入了妇女独立团这支分外的部队投军士。我们每天进行严格的军事演习,紧接着便是连续的行军和作战。10月尾,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第五、第九、第三十军团组成红军西路军,遵照中心指示相继西渡黄河,我们妇女独立团也成功地渡过黄河,我由于年纪小,加上身体有病,逐渐掉了队,我们一起的有十来个男女战士,大家仍旧相互帮助、相互鼓励,咬牙忍痛,追赶大部队。待我们赶到离黄河还有不到十五里路的地方,我们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清晨,我们从老乡那里借到一口锅,大家把身上仅有的一点钱凑起来买了一只羊,准备煮熟饱吃一顿,增加体力,以便追赶部队。正当把羊肉煮好要吃的时候,溘然创造有一些老百姓,个中还有一些红军战士从黄河的方向朝我们这个方向退下来。我们急忙跑上前去打听。他们说,西渡黄河的部队已经同马步芳、马鸿逵的白狗子打起来了,渡口已被胡宗南部队盘踞了,船只也被国民党抢走,有的被烧掉了,已经没有办法再过河了。听了这个,我们几个同道很焦急,一起商量了一下,以为黄河既然过不去了,我们还是连续北上去找中心红军,去找毛主席。我们抱着对党中心武断不移的信念,又开始了急行军。我们拖着病体,忍饥受饿走了两天两夜没有安歇,终于在第三皇帝夜遇上了一支红军军队。正准备停下安歇一下子,大部队又吹凑集号向前行进了。我们又怕同部队失落去联系,只好强打精神跟在军队后面追赶。又走了两天,才追到了红一方面军设立的兵站,我们才找到了有吃的、有安歇的地方。就这样,我们一站一站地走出山,到了陕西的云崖镇。我们这些没有能渡过黄河的女战士,被集中送到云崖妇女学校进行整训和学习。每天“三操”(早操、军训、晚点名)、“两讲”(讲政治课、学文化)。清晨凑集出操,跑步、瞄准、拼刺刀;早饭后,学习文化和上政治课。学校共有四个连队,我被编在持续。我记得和我一起学习的川北老乡还有伍兰英、赵惠兰、李玉兰、罗平等一大批女同道。在这里,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我们这批红军从妇女学校学习卒业后,是何长工同道率领我们奔赴延安。到了延安,我们被分配到各个部队事情,我被分配到延安留守兵团后方政治部剧社当社员,从事宣扬事情。
结识冠三我们党精确处理“西安事变”后,全国形成了国共互助,共同抗日的局势。这时的延安已成为全国有志青年和爱国人士心目中的革命圣地,他们纷纭从全国各地来到这里,接管革命的洗礼。
党中心和毛主席特殊重视宣扬党的共同抗日纲领,以联络更多的人参加到这个军队里。因此,我们政治部和剧社的任务就非常繁重。险些每天都有演出和联欢任务。经刘忠、伍兰英夫妇和后方部队李兆炳同道的先容,我与当时任抗大俱乐部主任的谭冠三同道相识了。
冠三同道是湖南人,出生在一个农人家庭。早期从事农人运动,1925年独身只身奔赴当时的革命圣地广州寻求革命真理,投考黄埔军校,未果,即返回家乡从事农人运动和武装斗争。1926年加入青年团并于同年转党,是参加过湖南秋收叛逆、湘南暴动、三湾改编、井冈山斗争和开辟中心苏区根据地斗争的老革命。毛主席早在井冈山会师时就已经对谭冠三同道很熟习了。当时冠三同道率领耒阳南二区农人赤卫队参加湘南叛逆,随朱德同道上了井冈山。这时山上的军队扩大了,吃粮便是个大问题,毛主席找到谭冠三同道说:“听朱德、陈毅、毛泽覃先容,你还是个教书师长西席哪!
你我是同行嘛!
你是带着军队上井冈山的,要按‘绿林’的规矩来说,你还是入了股的呀!
当然,在我们红军军队里就不讲这些了。为了担保井冈山红军战士们每个人有饭吃,我要找个有些文化的同道来当这粮草官。冠三同道。你能不能干啊?”冠三同道说:“我的文化不高,如果主席以为我能干,我就去试试吧!
”就这样,一个区农人赤卫队的党代表、苏维埃政府秘书长兼党团布告,愉快地服从毛主席的分配,到红四军军需处当了一个管粮草的“布告官”。
1938年,参加井冈山斗争的部分同道在延安合影。前排左二为谭冠三。
冠三同道性情刚强,处事果断,作战年夜胆,又长于做思想政治事情,能上能下,深得广大官兵的爱戴。他先后任红十二军政治部宣扬科长、团政治委员、红一军团军事裁判所布告、陕甘支队政治部主任等职,随红一方面军参加了长征。在红军中,他算是比较有文化的人。他不但写得一手好字,而且很有文艺天赋,会吹箫、吹笛子、拉胡琴、弹月琴、琵琶,会唱山歌和红军歌曲,也会唱一些京戏、湖南花鼓调。李兆炳同道对我讲过,还是毛主席点将要谭冠三当抗大俱乐部主任的。在长征过草地时,一股国民党骑兵在我军的前面,毛主席对谭冠三同道讲:“冠三同道赶紧带领军队去消灭这股仇敌”。在这场战斗中,冠三同道负了几处伤,毛主席亲自将他的拐杖送给冠三同道,并对冠三同道讲,一定要走出草地,完发展征,留下革命的火种(至今主席送给冠三同道的拐杖我还保存着)。四渡赤水战役时,有一次部队打了胜仗,在行军途中安歇时,冠三同道抽出笛子给大家吹出欢畅的乐曲,以鼓舞士气。正巧毛泽东同道和王稼祥同道从这里途经,听到这充满喜悦之情的笛声,就朝笛声的方向走去,走近一看是谭冠三同道在给大家演出,非常高兴。毛泽东同道高兴地说,冠三同道,你的笛子吹得很好听啊!
把同道们打胜仗的喜悦心情都吹出来了!
好哇!
冠三同道,你还是个多才多艺的多面手嘛!
冠三同道听到毛主席的表扬也很高兴。他发起大家一起唱一首红军歌曲,大家热烈相应,共同唱了一首《当兵就要当红军》的歌曲,声音宏亮,响彻云霄,毛主席和王稼祥同道也和同道们一起唱了起来。这歌声极大地鼓舞了红军的士气。
红一方面军胜利长征往后,冠三同道参加了直罗镇战役和东征、西征战役。西征战役尚未结束即被送到红军大学一科学习,毕业后留校。他先同刘亚楼同道在演习处搞演习事情,不久即调到抗大俱乐部当主任,后来又调到秘书科当科长。与毛泽东同道打仗的机会就更多了。毛泽东同道在抗大教务事情会议上,对谭冠三同道领导的俱乐部事情给予了表扬。
参加红一方面军长征到达延安时的谭冠三
由于我同冠三同道的个人经历有许多相似之处,又都经历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艰巨磨练,有许多共同措辞,我们于1937年8月在延安结婚。我们先后生养了6个孩子,由于战役环境的恶劣和残酷,有两个孩子不幸短命。
1947年7月9月,时任晋察冀军区第三纵队政治部主任的冠三同道,去西柏坡参加中共中心事情委员会召开的全国土地会议。会后,他向中心北方局提出到长江以南敌占区开辟事情的要求。得到批准后,立即动身南下,我当时也带着3个孩子随他一起南下。走到邯郸,我因身怀六甲行动不便,冠三同道就安排我和孩子们返回冀中深县王村落,在他抗战期间的老警卫班长赵金标的家里安顿下来。1949年3月2日,公民解放军胜利进驻北平。为了欢迎新中国的建立和革命胜利后的培植任务,我急迫希望进一步学习文化知识,提高文化本色。这样,在庆祝胜利的鞭炮声中我把两个小的孩子(女儿齐峪1岁,小儿子戎丰生下来刚7天)分别寄养在当地的两个农人家里,把两个大一点的孩子(老大戎生仅8岁,老二延丰刚刚4岁)送到北平华北军区荣臻学校(后改为北京军区八一学校)上学,我即到石家庄河北省委党校学习,直到成都战役结束。
【1950年,接管进军西藏任务后,李光明把宗子谭戎生(左三)、次子谭延丰(左一)送到荣臻小学住读;1947年,三女儿谭齐峪(左四)被送到河北高阳县一个庄家家寄养;1948年,四子谭戎丰被送给河北深县一家庄家抚养,并立下《送子左券》。】
谭冠三和李光明写下的《送子左券》
随同十八军进藏1949年12月尾成都战役后,我接到总政治部的电报,要我即刻到北京集中,前往重庆二野报到。当时我正在石家庄河北省委党校学习。接到关照后,我即赶赴北京,把两个在华北军区荣臻学校的孩子接到招待所。八九个月不见,孩子们都有了一些变革。作为母亲,我非常理解孩子们须要母爱的心,但党的召唤便是命令,革命的利益高于统统,我必须摆脱孩子们的“纠缠”,按时动身。于是,我趁孩子们睡熟之际,强忍心伤的泪水,离开了他们。
我同十几位同道一起从北京乘火车南下到武汉,改乘轮船逆水而上到达重庆。在招待所正巧遇上了十八军后勤部部长扶廷修到二野开会。他说可以同他一起乘汽车前往乐山十八军军部。通过扶廷修先容,我才知道冠三同道任十八军政治委员,现已接管党中心的命令,准备进军西藏。到乐山已经很晩了,扶廷修把我送到驻地就告辞了。很晚冠三同道才回来,看到我他很高兴,快两年不见了,他还是那么瘦削,眼睛里带着血丝,看得出他的事情很紧张,也显得很疲倦,但是仍旧乐不雅观、武断,信心十足。他问起这两年我的情形及孩子们的安排,我都逐一贯他作了申报请示,他点头表示满意。他也同我讲了他的情形:参加西柏坡中心召开的地皮会议后,他哀求南下到江南敌后开辟新区的报告得到批准,到达豫皖苏区。当时刘邓大军胜利挺进大别山,中原局哀求迅速创建新的根据地,抽调大批军队干部做地方事情,发动群众,建立政权。这样他未能渡江,而被派到汝南工委任布告。成立豫皖苏八地委,时任地委布告兼八分区政委,参加并增援淮海战役。1949年2月,成立十八军,调任军政治委员,率部参加渡江战役,一起南下作战,历时10个月,路子8个省,作战数百次。成都战役后,决定十八军经营川南,军长张国华兼任川南行署主任,谭冠三兼任自贡市委布告。未几,党中心、毛主席指示,由西南局承担解放西藏、经营西藏的任务。刘邓首长经由权衡决定,由张国华、冠三同道率十八军担此重任。目前正进行思想动员和各种准备。
1950年1月,李光明与谭冠三在四川乐山会合时的留影。
在我见到冠三同道时,对部队情形和全局情形不甚理解,曾很冒昧地向他提出:我们现在已经在一起了,可是四个孩子年纪都还小,可不可以先接来四川安顿?他沉思了一下子,没有立时回答我。我接着又追问道:难道这个问题很难、很大吗?在我的追问下,他不得不通盘托出他的想法。他对我说:“光明呀!
我们结婚12年了,由于处处在战役年代,我们真正在一起的韶光并不多,但是彼此信赖,相互支持,最艰巨最残酷的磨练我们都熬过来了。现在新中国建立了,是该当过和蔼团圆的日子了。但是,我和全军指战员已经接管了党中心、毛主席和刘、邓首长下达的进军西藏、解放西藏的光荣任务。刘伯承司令员乃至强调,进军西藏的任务极其艰巨和意义重大,可以称作是‘第二次长征’。把这个光荣的历史重任交给十八军,是党中心、毛主席和刘、邓首长对我们的最大信赖。但是,现在看来,我们的一些同道,特殊是在少数领导干部中,有过安稳太平日子的思想,有个别的乃至抵触感情很大。我作为政治委员,该当旗帜光鲜地表明自己的态度和态度,我和你不在川南安家,也不能把孩子接到川南安顿。为了西藏公民的解放,我们只有舍弃小家,只有舍弃儿女情长的顾虑,以我们的实际行动去传染和教诲全军将士,率领他们去完成历史授予的光荣义务,把五星红旗胜利地插到喜马拉雅山上。这才是我们红军战士的本色呀!
你说对吗?光明同道,我想你一定会支持我的!
我们一起进行第二次长征吧!
”他的这番话是发自肺腑的,也是他真实情绪的表露。十几年了,我对冠三同道的性情理解得太深了,同时,也非常理解他的处境。作为军政治委员、紧张领导者之一,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会对全军几万官兵产生重大影响!
我对他说:二万五千里长征我们走过来了,抗日战役那么艰巨、残酷的年代我们也熬过来了,蒋介石也被打挎了,新中国也成立了。现在的西藏还是农奴制度,百万西藏公民还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我从小给人家当童养媳,实际上便是当奴隶,做牛做马,知道当奴隶是什么滋味!
为了西藏公民的解放,进军西藏我义不容辞。我也是一名红军战士,受党教诲多年,为能同你一起参加“第二次长征”而感到自满。孩子们我已作了安排,比在战役年代稳妥、安全多了,这些你都放心吧。他听了我的一番话,非常高兴,牢牢握着我的手激动地说:“我知道你一定会支持的!
”
不久,我被分配到十八军妇女干校任第三中队中队长,同大家一起学习有关政策,学习藏语文,做进军西藏的各种准备。一次,军政治部主任刘振国来看我,一开口就对我说:光明同道,你带了个好头哇!
我一听楞住了,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就问他:刘主任,我刚来了不久,还没有做什么事啊!
他风趣地说:“就你表示要同谭政委一起进军西藏这件事影响就不小啊!
在全军带了个好头啊!
军党委扩大会上,国华同道连声夸奖‘好!
好!
好!
这个头带得好!
’。老政委还表示:这次进军如果捐躯了,也要把他的骨灰送到西藏,埋在西藏的地皮上。‘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就义沙场还。’老政委果武断态度,后盾还在你光明同道这里嘛!
”我急忙说:刘主任,这话可就过奖了!
冠三同道你是最理解的,纵然是我做不到,他也会武断做到的。何况,我是他的战友和妻子呢,这也是一个红军老战士的职责嘛!
刘振国听了很高兴,还很关心地讯问我身体怎么样?孩子们的安排情形,有什么困难须要组织办理?我说:统统都安排妥当了,就等一声令下,整装出征了。就这样,我同冠三同道一起接管了进军西藏的光荣任务。
1950年3月4日,天空晴朗,红日高照,十八军在乐山举行了庄严隆重、叱咤风云的进军西藏誓师大会。军长张国华、政委谭冠三率领全军将士庄严宣皙:为了完成祖国统一大业,驱逐帝国主义出西藏,解放苦难中的藏族公民,我们一定要发扬红军光荣传统,吃大苦、耐大劳,不怕困难困苦,不怕流血捐躯,武断完成进军西藏任务,誓把五星红旗插到喜马拉雅山上,让幸福花朵开遍全西藏。
十八军进军西藏誓师大会
誓师大会结束后,一场向“天下屋脊”的大进军开始了,全体部队以无比的激情亲切积极进行出征前的各项准备。当时,在体检时创造我已身怀有孕了,组织上动员我暂缓进藏留在后方。我表示:既然冠三同道已经向全军将士表示了我们共同进藏的决心,那便是说没有后路可走,更不能说了不做,失落信于众,便是碰着再大的困难和危险,也要实践自己的诺言。我的武断态度使他们很冲动,并关心地叮嘱我一定要把稳身体,保重安全。
就这样,我被派到军司令部通信科作报务事情,随军直机关重新津动身。出征部队经雅安、天全、泸定、康定向道孚、甘孜进军。其间,翻过了二郎山、折多山进入高原。部队到达甘孜后作了一段休整(大约半年),同时等待中心公民政府同西藏地方政府的和谈。1951年5月23日,中心公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签定了和平解放西藏的17条协议,这是党的民族政策的伟大胜利。
1951年7月1日,进藏部队在张国华和谭冠三率领下连续向昌都挺进。西藏地方政府首席和谈代表阿沛·阿旺晋美夫妇同军直机关一起行动。
部队翻越了海拔5300米的雀儿山和5000-6000米的达马拉山、甲皮拉山,于7月17日到达昌都。从昌都到拉萨还有2300多里路。沿途横亘着十几座嵬峨的雪山,有的终年积雪,空气稀薄,干部战士都要背六七十斤重的武器装备和粮食;有时爬雪山还设法带上干柴以备野炊用,在积雪没膝的险路上与凛冽的风雪搏斗。晚上就在雪地上宿营,帐篷就扎在雪地里,人一呵气,帐篷里就结成了冰花,不少人头痛胸闷,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我们通信科的同道每天都要超负荷运转。白天和部队一样行军,晚上部队宿营,我们却要立时设机架线,发动马达开始收发报事情。
在部队行进到昌都西北的丁青宗时,猜想之中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军指挥机关在丁青宗驻扎,我们通信科距军指还有一段路程,那天是我值班,当我走在路上时,我感到肚子有些模糊作痛,但是我想:在事情岗位上事情第一,个人有再大困难也要战胜。于是,我坚持走到事情室。当我用力摇动马达时,因用力过猛而导致大出血流产,人顿时晕厥过去。事后得知,在我处于手术抢救的紧急时候,冠三同道正在基层部队检讨事情。手术后,当军政治部卖力同道打电话向他报告,请他早点回来探视时,他只对政治部的同道说:“请转告光明同道,分开危险就好,一定要她把稳安歇,手上的事情可以暂时交给其他同道,我事情完了就回去看她。在我脱险之后,许多同道都关心地疏导我返回内地休养,由于前面的道路更艰险,自然条件更恶劣。冠三同道回来往后,也极为关怀地向医务职员理解我的情形。当他理解到由于药品东西短缺,确实存在不少困难时,也搜聚我的见地:“是否可以先返回四川休养,治疗好了再进藏。”我对他说:战役年代我们生养了六个孩子,去世了两个,那是战役的残酷所致,二万五千里长征捐躯了那么多大胆的战士,那是红军的物质条件极度困难,自然环境非常恶劣,加之仇敌强大军事力量的围追堵截所造成的不可避免的捐躯。这次我们接管进军西藏、解放西藏的任务,受到党中心、毛主席以及全国公民的大力支持,条件比二万五千里长征,比抗日战役、解放战役要好得多了。那个时候我都没有去见马克思,难道碰着这么一点困难就退缩不前吗?那还能称得上是红军战士吗?还配作谭冠三同道的战友和妻子吗?他听了我发自肺腑的话,也高兴地笑了起来,说道:“光明啊!
我知道你的性情是刚强的,困难面前是不会动摇的。你一定要好好安歇,我们一起把第二次长征走到底,解放西藏,完成统一祖国大陆末了一片地皮的神圣任务。”
部队在丁青宗休整了一周旁边的韶光又踏上了西征的路程。我虽然身体还很虚弱,但在首长和同道们的关怀照料下,仍旧顽强地随同部队提高,同雪山冰河搏击,勇往直前。不几天,部队来到怒江边。怒江两岸峭壁绝壁,江水是冰山雪水,翻滚咆哮,狂怒奔流,一泻千里。军首长亲自带人实地稽核,选取比较安全的地带,采取牛皮筏子载人渡江,骡马进行泅渡。坐上牛皮筏,在江水激流中冲荡,很随意马虎使人头昏眼眩。我们只能闭上双眼,屏住呼吸,全身放松,顺其自然,逐步漂向对岸。渡江时,职员没有伤亡,骡马却丢失了20多匹。横渡怒江天险后,我们在大草原上走了10多天,来到进军途中末了一座大雪山——冷拉山。冷拉山海拔6300米,山顶冰雪沉积,空气稀薄根本没有路。部队刚走到山脚下,就有不少同道涌现高山反应。大家一步三喘气,走几步停下来缓缓劲再使劲往上爬,从山脚下一贯攀登到山顶。爬到山顶纵目了望,一片银色天下,景致极其壮丽。但是严重缺氧,使人头昏眼花,头重脚轻,有再好的自然美景,也没兴致去欣赏它了。下山时更为险要,从山顶向下俯视,是一眼望不到底的万丈深渊,可谓人迹罕至,鸟兽绝无。在冠三同道的指挥下,大家坐在地上,双腿伸直,双手抱紧枪支,两眼盯住一个方向。一声令下,同道们按照先后顺序排列往下滑,这种办法虽然有危险性,但是在当时情形下,谁还能想出更好的办法来呢?部队整整用了两天韶光才胜利超越冷拉山。据统计,翻越冷拉山时,干部战士口鼻出血的占2/3,因高寒缺氧,心脏病产生发火而捐躯的有5人,还有许多骡马倒毙。和我一起行军的一位同道就捐躯在冷拉山顶。
红军长征爬雪山(油画)
经由千辛万苦,两千多公里的漫漫征途上,十八军将士发扬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凭着对党、对公民的无限忠实,以顽强的革命意志,用坚实的双脚,历时一年零八个月的长途跋涉,翻越了十几座嵬峨的雪山,渡过几十条湍急的河流,穿越了广袤的茫茫草原和原始森林,踏过了高原流沙和冰川地带,降服了高原雪山的奇寒缺氧,抗过了狂风骤雨的打击,战胜了物资极度缺少的困难,终于在1951年10月24日,进抵西藏首府拉萨。10月26日,在拉萨各界万名僧俗、群众的欢迎下,十八军将士举行了庄严隆重的入城仪式,走在军队最前面的是军长张国华、政治委员谭冠三。在这支具有光荣历史和屡建战功的英雄部队行列中,有数百名英姿飒爽、引人瞩目的女军人。她们同那些男子汉们一样,带者胜利的喜悦,雄赳赳、气昂昂地踏进了高原古老的阳光城——拉萨,胜利地完成了把鲜艳的五星红旗插到喜马拉雅山的神圣任务。当晚,冠三同道带着难以仰制的激动心情,挥笔写下了豪迈诗篇:
……大军西进一挥间,二次长征不畏难;数月艰辛卧冰凌,天下屋脊红旗展。男儿壮志当报国,藏汉联络重如山;高原有幸埋忠骨,何须就义沙场还。
1951年10月26日,西藏地方政府为公民解放军举行了隆重的入城式。
1985年12月6日,冠三同道去世后,经中心批准,他的骨灰安顿在拉萨西郊——他当年率部创建的八一农场苹果园,实现了他“长期建藏,边陲为家,去世在西藏,埋在西藏”的夙愿。中国的神圣地皮一寸也不能丢!
他永久守卫在西藏,这对驻藏广大官兵永久是一种教诲和勉励。进军西藏的岁月让人永生难忘,西藏是我魂牵梦萦的地方。
建国后,女红军林月琴大校(前右)、吳朝祥上校(前左)、王新兰上校(后左)、李光明少校(后右)合影。
本文系作者授权《祖国》杂志社祖国网揭橥,转载请注明来源和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