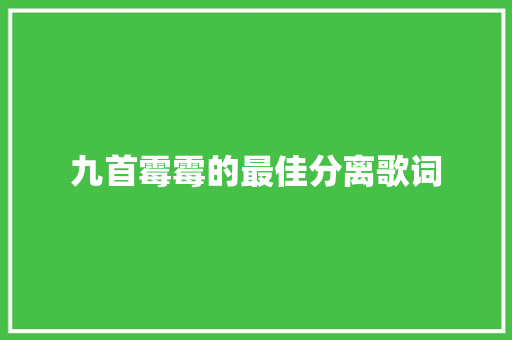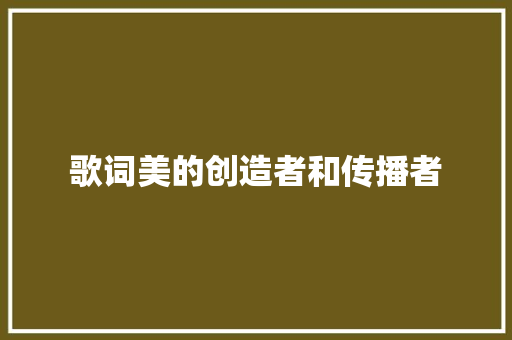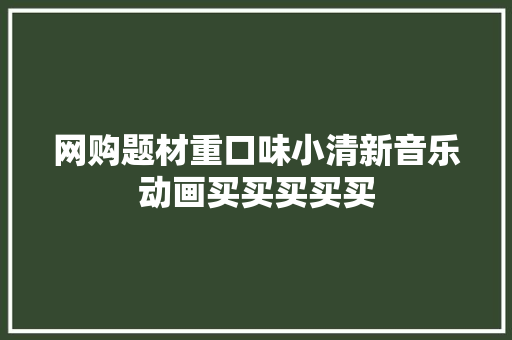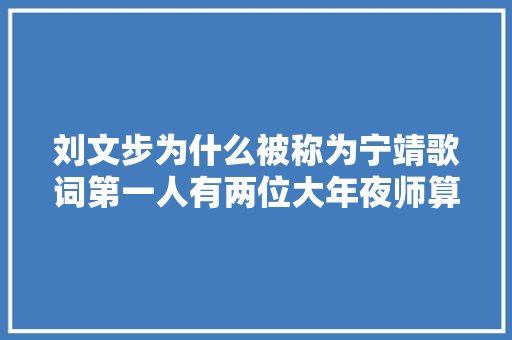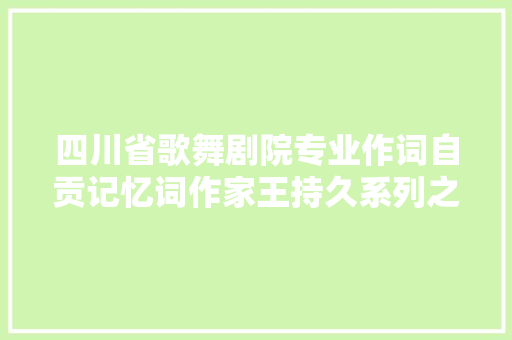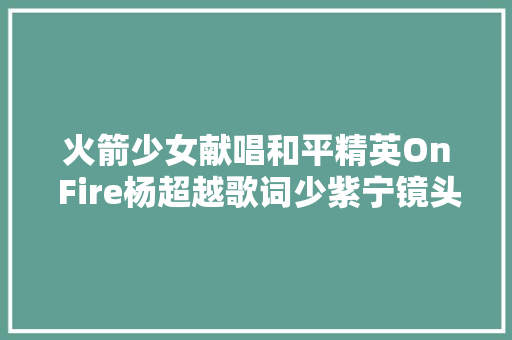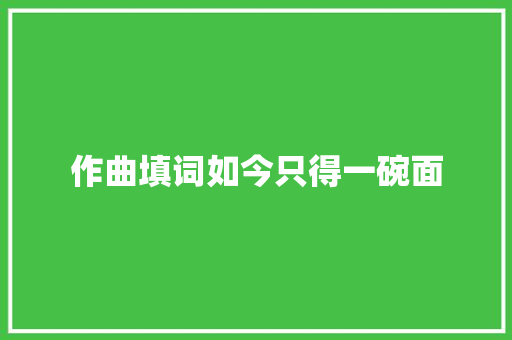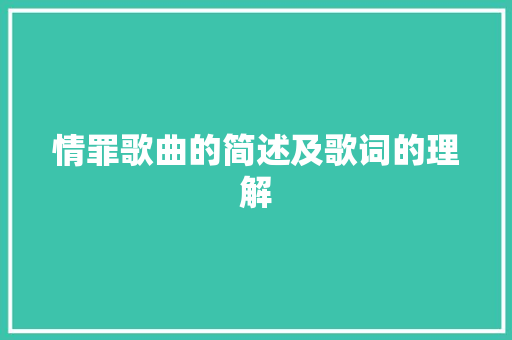曾几何时,不管是京津两地的小相声园子,还是各级电视台的舞台上,太平歌词都早已淡出了曲艺爱好者的视线。借用马三爷在《扒马褂》中的一句话:“俗,太俗了,这都臭遍街的玩意。”虽说只是句台词,但也不丢脸出在过去很长一段韶光老艺人们都不愿意再唱它。直到郭德纲和德云社的异军突起,才让太平歌词这一传统演唱形式重新回归相声舞台。
如果现在有人说“太平歌词是由于郭德纲才重新火起来的”这话该当不会有太多回嘴的声音。对付听龄较短的新不雅观众而言,他们从郭德纲口中理解到太平歌词原来是相声演员的本门唱;理解到《单刀会》《白蛇传》《太公卖面》这些传统唱段;乃至更多的理解到演员唱太平歌词时用的玉子板的来历。客不雅观来说,郭德纲对付太平歌词的推广是值得肯定和褒奖的。不过对付“老听户”们来说,郭德纲在演唱时暴露出的硬伤又是难以接管,更难以容忍的是他将个人缺点的理念认知贯注灌注给了不雅观众和徒弟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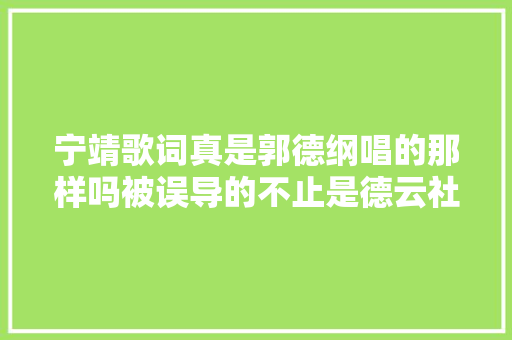
郭德纲在各种演出中曾不止一次先容到:“太平歌词便是一上句一下句,节奏大略,也没有太多演唱技巧。演员只要根据个人嗓音条件,加上自己的装饰音,每个人唱出来的风格都不一样。 ”实在,这一说法本身便是种误导。首先, 太平歌词在节奏上有花点、有赶板;其次,在演唱时讲究鼻腔共鸣和脑后音的转换利用。这便是老粘子们常说的,听的是甩腔的 “嗖儿”。太平歌词的确便是一个上句接一个下句,但要让不雅观众听出唱的好,且韵味并不大略,演唱时同样要有迟急抑扬。而所谓的“装饰音”在传统太平歌词里更是不存在的。
举个例子,《白蛇传》是郭德纲频繁使的唱段。郭版唱法为“杭州美景盖世无双,西湖岸奇花异草四了季的暗香。”在原词中多加了两个字,看似平添了“翘口”,实际上却是多此一举。太平歌词演唱的最基本哀求是不能唱“倒音”,即必须遵照唱词中的原字原音。按郭版唱腔转化成文本后变成了“西湖岸奇花异草去世了挤的晴祥”。这样唱出来的词句很难让曲艺爱好者听出美感。
历代相声老艺人中唱太平歌词拿手的大有人在,例如德字辈的吉坪三,寿字辈的王兆麟,宝字辈中有杨少奎、马志明、王本林,笔墨辈中有刘文贞、刘文步、佟守本。这些先生长西席在演唱时不仅没有刻意而为的高门大嗓,而且行腔韵味十足,讲究“腔圆”的同时,更看重“字正”。
除了《白蛇传》中暴露出的问题,郭德纲演唱的《秦琼不雅观阵》也差强人意。这个传统唱段是太平歌词中比较吃功夫的,由于个中有大段类似“贯口”的唱词,演出时极为磨练演员对气息的调节和节奏的把控。郭德纲唱这段“贯口”时,有两处明显硬伤。其一,没有气口,完备是一口气唱完,不会换气的唱法不仅演员唱着累,不雅观众听的更累,缺少应有的节奏律动。其二,也正是由于没有气口,导致一大段唱下来很随意马虎涌现“滚口”。类似的问题在郭德纲背趟子时也常常涌现。
太平歌词作为相声演员必备的基本功,理应被保留和继续。但被保留和继续的条件是正统的唱法。将个人偏颇的缺点理念贯注灌注给不雅观众,传授给徒弟,如此畸形的传播反到成了对太平歌词的扭曲,也不利于这种演唱形式的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