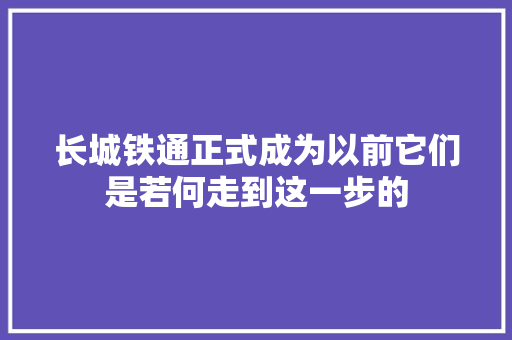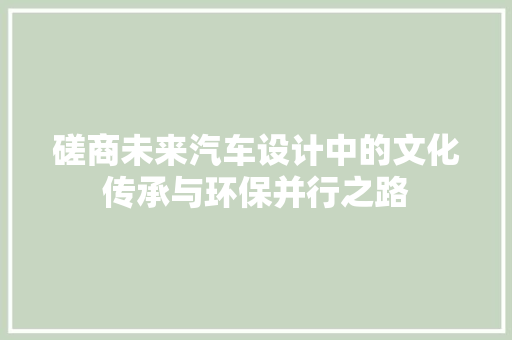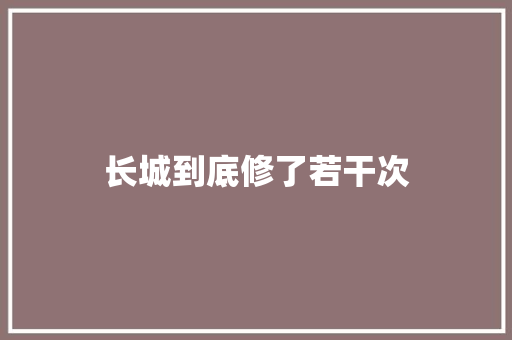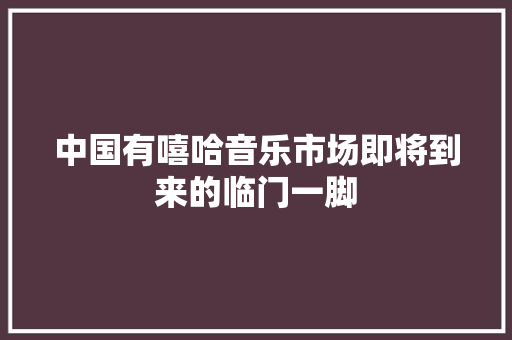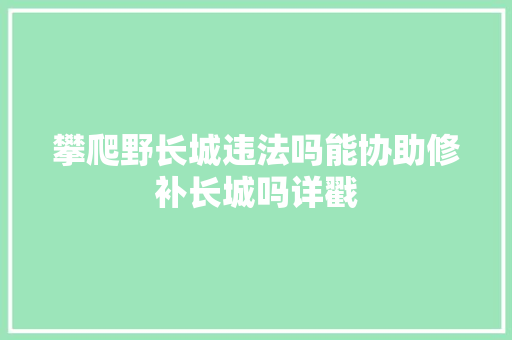《长城史话》是我国著名古建筑学家、“万里长城第一人”罗哲文师长西席最主要的作品之一,他“严谨务实的风格冲动了所有打仗过的人”。正若有论理学者许嘉璐所言,罗老的事情激情亲切让人望尘莫及,他的足迹踏遍了全国所有长城遗迹。在《长城史话》中,罗哲文结合文献记载和实地稽核,全面先容了长城从先秦到明清的历史,长城的用场和布局,长城是若何建筑的,以及长城的几处遗址。这对宣扬和理解长城文化,精确认识长城的地位、历史浸染及促进长城的保护与研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参考代价。
著名历史学家田余庆在《论轮台诏》中说:“在西汉势力向西推进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在绝域中列置亭障具有关键意义。”作为人类社会现存最为宏伟的文化遗产之一,“长城在军事上并不但是具备防御功能。当中原王朝转入计策进攻态势时,烽燧亭障随着前锋兵马的挺进而向前延伸,在稳扎稳打不断巩固前沿阵地的同时,又供应交通供给之便,为新的拓展奠定坚实的基地”。罗哲文认为,长城的历史地位除了“安定与和平的保障”这一功能之外,它所携带的历史信息非常丰富,是其他任何一件宝贵的文物所不及的。长城历经岁月的洗礼和历史的熬炼,既蕴含着众志成城、坚韧不屈的民族精神,亦造就了独特的历史景不雅观,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象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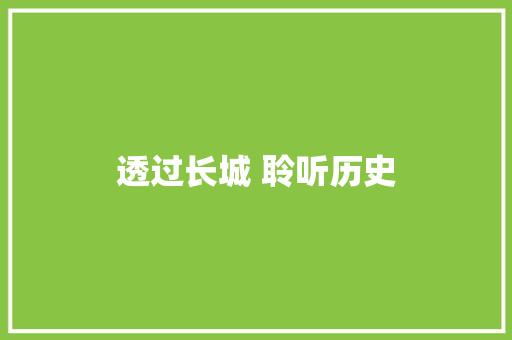
考古学家马尔克·奥莱尔·斯坦因在1933年出版的《斯坦因西域考古记》中感叹道:“我不能不惊叹古代中国工程师的技巧”“那些军事工程专家碰着恐怖的天然险阻所表现的坚忍精神及组织力量,又得到显著的证明”“诚笃说,这可以视为精神赛过物质的一种胜利”。纵不雅观古代中国西北部边陲发展的历史,中原文明(或谓之“黄河文明”)的扩展大多与以长城为核心的边防培植密切干系。构筑、护卫长城防线,包括修建交通网道,开设马市贸易,刺激了边地经济发展。西汉时,新秦已“公民炽盛,牛马布野”,呈现出“致马千匹,牛倍之,羊万头,粟以万钟计”。“缘边城守之地,堪垦食者皆营屯田”,屯田实边、辟置郡县基本上以长城为轴心或以之为后盾向外辐射扩展。秦汉军屯、民屯分布范围遍及北部诸多计策要地。“九边生齿日繁,守备日固,野外日辟,商贾日通,边民始知有生之乐”,即真实地再现了长城边防与屯田实边、交通网道、通商贸易之间环环相扣、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
长城既是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历史影象,还是中国版图一体相连而不可分割的历史见证,而且是连接丝绸之路东西两端和黄河高下五千年历史的文化桥梁和纽带。一方面,长城在中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产生的积极效应构成中华民族生理认同的客不雅观依据,而这种秘闻、内涵又与长城雄伟博大的景不雅观所引发的豪情壮志完美和谐地融为一体,终极积淀、熔铸成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另一方面,长城绝非阻断与其他民族、国家交往的障碍,相反,长城连接中亚、西域,中经黄河腹地,直到辽海和鸭绿江两岸的“丝路”中脊地带,这种“旷哉绝域,每每亭障”的格局,确保了丝绸之路的畅通和东西方政治、经济、文化的频繁互换,使公元1世纪以来中国的西北边陲成为印度文化、希腊文化、波斯文化等多元文化与中华文明交汇的前沿。与天下上许多伟大的人类历史遗址一样,在其军事实用功能逐渐消退与其文化精神代价不断增强的双向历史演进中,长城吸引着天下,乃至可以说“天下在一定程度上也是通过长城开始真正地理解中国”。
长城形式上是军事的,本色上却是文化的,其斑驳的墙体、残缺的烽燧,无一不是文化的象征。古老的长城完成了它的历史义务,历史授予它以全新的意义:它是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标志性建筑,有着聪慧、坚忍,肯奋斗、敢捐躯,坚不可摧、勠力同心的精神内涵,是涉及军事、交通、建筑、地质、气候、农业、艺术等领域的宝贵遗存。罗哲文认为,长城最“突出普遍代价”是“直接或明显地与具有突出普遍主要意义的事宜、生活传统、崇奉、文学艺术作品干系”。他在《长城史话》中认为:当长城完备成为历史的陈迹之后,解析它的现实代价以及进一步挖掘和整理长城的历史文化远比它的军事功能更为主要。首先,绵亘万里的长城沿线,遗留着极其丰富的宝贵文物,它不仅是理解中国古代军事科学、建筑艺术的主要实物,也是探索中国北方农业、牧业、气候、水文、地震等的主要依据。其次,长城所“创造中国文化并加以孕育的一种保护力量”“已经一步步地筑起了一道无形的内在防线……使它结晶成为比长城花岗岩更坚牢的形式。纵使迢遥的未来,任何外来的侵略,都再也无法使它崩溃”。(刘英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