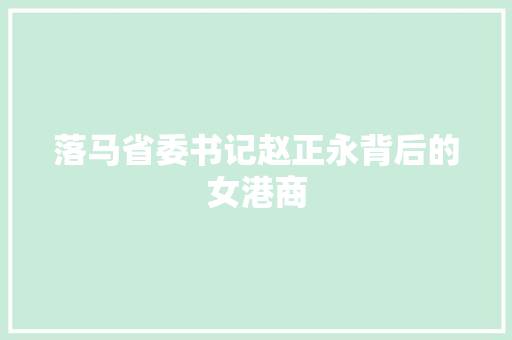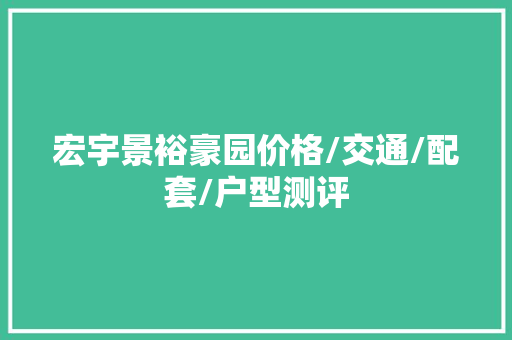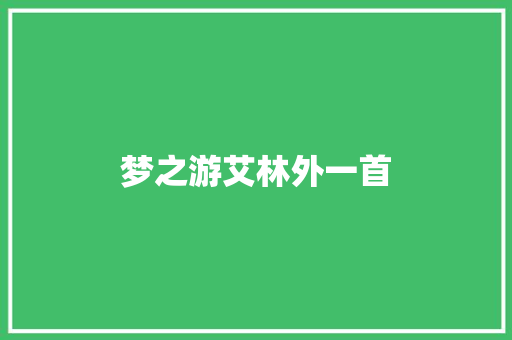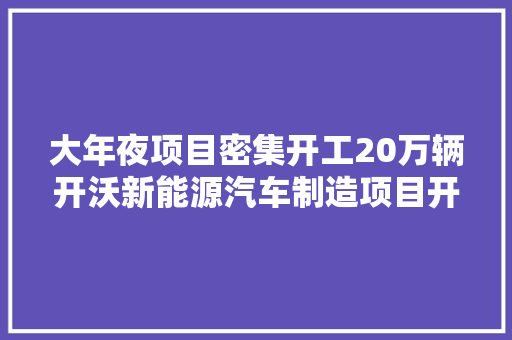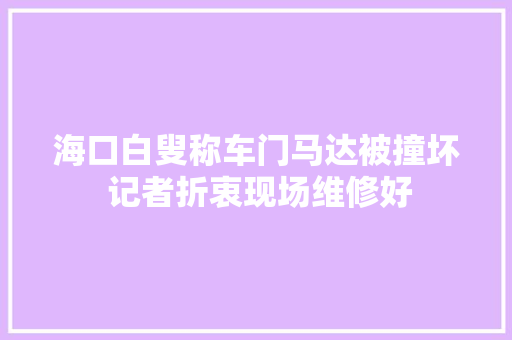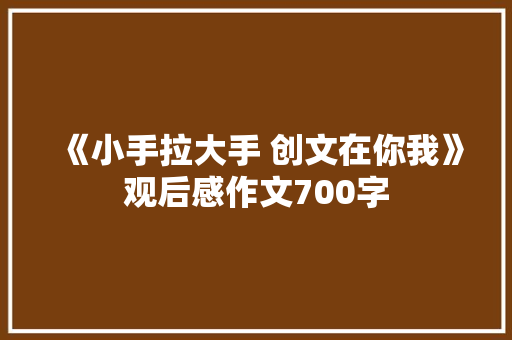来源:南方都邑报/南都广州
寻访手记 南海神诞日怎变了波罗诞? 我一贯感到奇怪,农历仲春十一至十三日明明是南海神的诞日,为什么到了民间,就蜕变为不知何解的波罗诞呢? 今年赶在波罗正诞那天,去了一趟南海神庙,车行路上,天色变得墨黑,接着下了一场多年广州难得一见的冰雹,本以为此行就此泡汤,岂料到站天放晴了。才瞥见棚架下卖东西的商贩又重新张罗支配。 转眼间期待进庙的人已排起长队,很多人一口四会、东莞等珠三角地区屯子口音,可见只管庙会上兜售的商品不过尔尔,但波罗诞在珠三角地区公民心目中的地位确实不同一样平常,值得临近地区老人家跑老远的路,就为了进庙烧一炷喷鼻香,拜祭掌管海上商路的财神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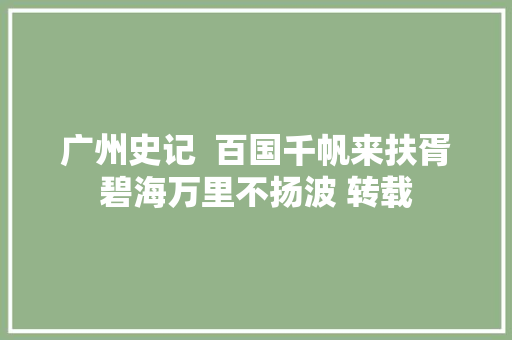
本日,珠三角地区的人们每年都不忘来拜祭这位掌管海上商路的财神爷。
我随人流入了庙,爬上山岗上的浴日亭,站在一旁听老人家的闲聊,提及四五十年前浴日亭上还能望得见海。还提及扶胥浴日的有名,提及苏东坡的诗。但在场的人对扶胥港曾在中国海上贸易史上所作的辉煌贡献,彷佛一无所知。
扶胥港的繁荣,确实是太久之前的事情了,当景象不再,建筑留下,不过是沉默的证人,影象亦会随人物、事宜的离散,而深深奥深厚入史册,于是再来览胜的后人,对关于过往论述的真伪,就无从判断。 由此推测波罗诞称谓的形成,彷佛豁然开朗了,在庙会茂盛的明清两朝,扶胥港已经步入衰落,在南海神庙举行,为商贸做事的祭海行为亦因此缺少真实场景的注释,反而是俚俗而离奇的传说在民间流传,民间总是难免嗜好传奇,认同普通易记的称谓。南海神的诞日变成了波罗诞,其缘故原由亦大概如此。 □ 李小翠
历史再现 海上丝绸之路从这里出发 历代帝王“偏爱”南海神 1400年前(公元594年),当隋文帝下诏,在黄埔镇扶胥港,为南海神建祠时,南海神所享用的,还只是“侯祭”的规格。 到天宝十年(公元751年),唐玄宗册封南海神为“广利王”,南海神庙规格即改为宫殿建制,岭南节度使孔戣领命三次拜祭南海神,按的已是“王祭”的标准。 宋太祖一统南北,更把南海神加封为“广利洪圣王”。 而到明朝朱元璋开国,亦丝毫未曾怠慢南海神,然而他认为自己功高盖世,不愿把自己的册封跟在前朝封号之后,于是洪武三年,立碑取消前代封号,直接封为“南海神”,即以官方口径,确立南海神至高无上的海神地位。 只管自明朝起,黄木湾口日渐淤塞,港口地位渐被黄埔港取代,清代天子依然不断重修南海神庙,并且每年致祭。 那么究竟是什么缘故原由,令一座阔别政治中央的海神庙,受历代帝王的刮目相看,并几次再三对它进行册封? 南海神何以独尊? 中国水神甚多,海上渔民信妈祖,江河渔民拜北帝,这些水神的寺院,多由民间兴建;而帝王拜祭天、地、山,以求社稷安稳,风调雨顺。《外洋南经》有“六合之间,四海之内”之说,这个四海与天下同义,因而帝王祭四海,亦即祭天下。“西海”和“北海”没有定论,而东海和南海中,又以南海为大,南海神地位超然,就如五岳中帝王唯泰山独尊一样。南海神庙卖力人黄应丰说,如今南海神庙是海内最大的木构造宫殿。而原址位于山东莱州城西北的东海神庙在“文革”中已成废墟。 因而不同种类的水神庙中,南海神庙是官庙,是天子祭海的据点。南海神掌管海上商船航行,商船离港前,必先入庙拜祭,方扬帆出海。 黄应丰说,没有资料显示曾有帝王亲自到神庙祭海,他们一样平常是委托地方官代祭,或在都城向四方遥祭,史料所记载受朝廷所托,到南海神庙来拜祭,官职最高的是唐朝宰相张九龄。 祭南海神需具猪牛羊三牲、酒和五谷,主祭官员宣读祭文,击鼓乐神,鸣炮升旗,然后刻碑纪事。 财富入口扶胥港,海神原是大财神 韩愈在《南海神广利王庙碑》中描述南海神庙前乃“扶胥之口”、“黄木之港”,在还未有神庙前的魏晋南朝,扶胥港已是“舟舶继路,商使交属”。 晋代裴渊在《广州记》中称:“广州东百里有村落,号曰古斗,自此出海,溟渺无际。”黄应丰说,这古斗村落即神庙附近庙头村落的前身,庙头村落布局不似受农耕文化主宰的村落那般小街小巷、屋院紧密,村落中一条宽阔大街,是古时墟场的遗迹。因古时出海、自远方来或途经的商船进庙拜祭,祈求航路安然、买卖兴隆,商旅云集古斗村落,令这儿庙会频繁,民间交易茂盛。这条大街,便是海洋文化留下的烙印,见证当年的商贸发达。 唐时称南海神庙前、珠江出海口外水域为“大海”,伸向要地本地的珠江为“小海”,因外来船舶不能进入小海,扶胥港成为全国最大的对外贸易港。 唐代的“广州通海夷道”已长达14000公里,是当时天下上最长的航道。商船军队从广州出发,经南亚各国,越印度洋,抵西亚及波斯湾,最西可到非洲东海岸。 那时位于珠江出海口的古庙前烟波浩淼,商船来往如云,“海旗幢出,连天不雅观阁开。货通狮子国,乐奏越王台。”(见韩愈《南海神广利王庙碑》) 宋代自扶胥港出发的商船可达“西南诸蕃三十余国”,“夷舶往来,百货丰硕”。据《元丰九域志》记载,扶胥镇为广州八大卫星城之首,商业比猎德、石门、瑞石、平石、大水、白田、大通繁盛。 历代帝王重视南海神庙的秘密到此得到揭晓,唐宋扶胥港的繁荣步入壮盛,自扶胥港的外贸收入,成为充足国库的主要财源。 据陈大震入元后所著《南海志》记载,元代到广州贸易的国家有147个之多,扶胥镇一年税收达4467贯,新会为4082贯,清远为3623贯,东莞为2282贯,解释扶胥镇到元代仍未衰落。 扶胥港为皇朝带来丰硕的财政收入,守护商船的南海神因而被最高统治者欣然册封为“广利王”(意即广收天下之利)和“洪圣王”(寓意财雄势大)。
古人拜祭南海神,是为了求它保佑海上贸易的顺利,难怪历代帝王都那么重视这个地处偏僻村落庄的“财神爷”。
民间传说 官府的拜祭,演化成了民间的娱乐 民间把南海神庙称为波罗庙,把南海神诞日称为波罗诞,并举行为期三日的庙会,在庙会上卖波罗鸡。波罗庙和波罗诞,在民间语文里,固然更为琅琅上口,但此二者,与南海神庙原来的庄严形象,无疑是相去甚远了。然而,关于“波罗”的传说,却是远比南海神要丰富。 波罗庙 萧梁时称今南印度为波罗国,波罗国即婆罗门。据南宋方信孺《南海百咏》,唐朝波罗国青鸟使到京城朝贡,返程时顺道登庙拜偈南海神,贡使种下从海内带来两粒波罗树种子,却因流连于庙中景致,误了归船。其人望江悲泣,并举左手于额前作望海状,希望海船回来载他,后来立化海边。当地人以为此人乃神仙所化,加以厚葬之余,还为其漆像加衣冠,受封“司空”,“祀于左廊,一手上加眉际作远瞩状”,封为达奚司空。因其来自波罗国,村落民俗称此塑像为“番鬼望波罗”(粤鄙谚中,外国人被称为番鬼),神庙因此被称为“波罗庙”。 宋仁宗庆历年间阮遵的记载,却说达奚是天竺高僧达摩的季弟,于萧梁普通年间跟从兄长经海上丝绸之路来中国。在扶胥登岸,见到南海神庙雄伟非常,遂进庙拜会。祝融见其身具神通,极力挽留他在庙中帮忙管理风云。他效忠职守,每天在海边巡察海上船只,后立化于海边。 “波罗”在梵语里指“彼岸”,“蜜”指到达,“波罗蜜”即“到达彼岸”之意。因而也有说商船靠岸时波罗国船员齐声欢呼“波罗蜜”,流传开来,人们便以为这是外国人对庙名的称呼,故为方便友邦人士的理解,亦称神庙做“波罗庙”,扶胥江为“波罗江”。 如今“番鬼望波罗”的塑像,仪门东侧有一尊,大殿内有另一尊,被封为南海神六位护法神之一。 波罗鸡 波罗诞上,人们习气买波罗鸡,祈求康健和好运气。波罗鸡并非真鸡,而是用硬纸糊上泥,做成鸡的形状,再粘上染成彩色的鸡毛。 这买鸡的习俗,源于一个传说。从前波罗庙附近村落里有位张姓老妇,无儿无女,与一只大公鸡相依为命。村落外有个财大气粗的员外,酷爱斗鸡,逼老妇把公鸡卖给他,受到谢绝,员外恼羞成怒,趁老妇下田之机,派仆人将雄鸡偷走。岂料鸡到员外家中,从此不再啼叫,员外一怒之下,把鸡宰了。伤心不已的老妇将鸡毛捡回家,洗净晒干,粘到黄泥做成的鸡身上去。做好的雄鸡维妙维肖,第二天清晨,老妇竟听到雄鸡的啼叫。她高兴至极,又做了不少这样的鸡,拿到波罗诞上售卖。波罗鸡的神奇与波罗诞上买鸡的习俗,就这样逐渐流传开来。
波罗鸡象征着南海神的赐福。
听说,每年出售的波罗鸡里,有一只是会啼的,谁买到它,便是得到了南海神的赐福。 南海神庙俗称波罗庙,位于黄埔区庙头村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出发码头扶胥港就在此处。神庙西侧章丘上浴日亭上不雅观狮子江日出的“扶胥浴日”,曾是宋元两代“羊城八景”之首。
“扶胥浴日”在宋元两代曾是羊城八景之首。
昔日羊城第一景,今以波罗鸡扬名
变迁之路 宋朝扶胥港作为贸易港口达到顶峰状态,贸易的繁荣聚拢了人流,带动南海神庙成为旅游胜地,“扶胥浴日”在当时羊城八景中名列首位;黄应丰说,也是此时,史上第一次涌现描写波罗诞的诗词,可见波罗诞的抽芽期间,不可能早于宋朝。 明代之后,南海神庙一带无论是环境,还是功能,都涌现重大变迁:一是扶胥港商贸的衰退;二是民间的敬拜和民俗活动反而越演越烈,波罗庙会到清代步入兴盛。 扶胥港衰退 明清期间,统治者畏惧外敌通过海路侵略江山,如明初朱元璋刚即位时、清初康熙未收复台湾时,都屡次实施海禁,海上贸易遭受重大打击。 同时黄木湾出海口为上流沙土淤泥冲积,近岸的水域形成沙洲,鱼游鹤立,却逐渐失落去船舶停靠的浸染。 明朝时,“扶胥浴日”的景象已大不如前,已不在羊城八景之列。明人陈献章和东坡韵的诗碑有云:残月无光水拍天,渔舟数点落前湾。赤腾空洞昨霄日,翠展苍茫何处山。顾影未须悲鹤发,负暄可以献龙颜。谁好手抱阳和去,散入千岩万壑间。其苍茫寥落,远不是苏东坡当年所见的壮阔与惊艳。 到了清代,船进黄木湾,滩宽水浅,潮退时,船上人上岸,都需趟水,稍自恃矜贵的人则请疍家佬背上岸。崔弼载文道:“今则游积已久,咸卤继至……潮当长就岸易,水消长则平沙十里,挽舟行陆,进退两难。” 后来更因海水退缩,沧海变桑田,解放后,原为船舶靠岸处,终日为海水拍打的“河清海晏”牌坊,离河滩足有300米远,牌坊前为一片蕉田,蕉田后是新中国成立后新兴黄埔电厂和船厂。 明清后与海洋接洽的港口转移到海宽水深的琵琶洲与黄埔洲,随着扶胥港的衰落,只管统治者仍旧重视在南海神庙举行的祭海仪式,但其功能更多地蜕变为旅游胜地,尤其每年的波罗庙会,吸引来自周边地区的善男信女、凑热闹的老老少少、小商小贩,以及民间艺人。 波罗庙会崛起 波罗庙会在南宋已经热闹非凡,刘克庄有庄《即事》描写波罗庙会:“喷鼻香火万家市,烟花仲春时。居人空巷出,去赛海神祠。东庙小儿队,熏风大贾舟。不知今广市,何似古扬州。” 当年年举行的民间喜庆渐成传统,变成民众的自娱自乐,也就逐渐分开了对港口经济状况的依赖。 于是波罗庙会的声名越传越远,在港口日益衰落的明代,反而越演越烈,到清期,民间对庙会的参与激情亲切空前飞腾。黄应丰说,清代的波罗庙会要办15天,除了周边居民,番禺、东莞、佛山、南海亦有许多人参加,有人坐船、有人骑马、有人坐轿、有人步辇儿。波罗庙会是一场文化娱乐活动,亦是一场商业活动,卖唱的、做大戏的、杂耍的、赌钱的、卖小玩意儿的,什么都有。 嘉庆年间人崔弼撰《波罗外纪》,十分生动地描述当时庙会的热闹情景:“波罗庙每岁仲春初旬,远近环集如市,楼船花艇,小舟大舸,连泊十余里,有不得就岸者,架长篙接木板作桥,越数十重船以渡,其船尾必竖进喷鼻香灯笼,入夜明烛万艘与红波照映,管弦呕哑,喧华竟十余夕。连声炮竹,动怒通宵,登舻而望,真天宫海市不是过矣。至十三日,海神诞期,谒神者……络绎庙门填塞不能入庙……凡省会、佛山之所有日用器物玩好,闺阁之饰,儿童之乐,万货聚萃,陈设炫集,照耀人日……糊纸作鸡涂以金翠或为表鸾彩凤,大小不一,谓之波罗鸡,凡谒神者游剧者必买符及鸡以归,赠送邻里,谓鸡比符为灵。” 波罗庙会延续至今 可喜的是,赶庙会的习俗一贯延续下来,本日,波罗庙会热闹依旧,人气兴旺,这里自然成了广州民俗旅游的热点去处。赶庙会的人也仍旧喜好买几只波罗鸡赠送亲友,图个吉利。 至于波罗诞买波罗鸡的习俗来源,黄应丰说,民间虽有多种讲法,但较可信之说为,因南方属火,动物以火鸟为代表,这火鸟的详细形象,即赤色鸟雀,也是南海神庙庙徽。估计赤色的波罗鸡形象,源于庙徽的演化。
遗址眼见 大海撤退导致神庙衰落 康熙御笔的“河清海晏”四字依然古朴,四柱三间的石牌坊前,此处当年曾“前鉴大海,茫然无际”,是“抛锚系船”之地,如今是一块平坦的空地,海却是在300米外的船厂那边了。 入内是五进院落式布局,最近一次修葺在1986年,由广州市政府出资200万,1991年2月8日落成,重新对外开放。据黄应丰先容,重修后的神庙,主体建筑基本保持明代建筑风格。但头门保存了周朝皇府建制的规格,门后有台,左为“书”,右为“塾”,是古代设计给人读书之地;而仪门则保存春秋战国期间建筑建制,利用复廊,即走廊以柱分隔为两部分。 庙内古木森森,广州编号1号和2号的木棉古木,都在神庙内。故意思的是,站在头门正中往里望,会创造大殿南海神塑像并没有处在同一中轴线上,只看到他的半边脸。黄应丰阐明说,这大概是古代建筑风水学在神庙设计上的表示,由于古代建筑布局讲究引人入胜,不能一览无遗,固需在门前制造一些阻隔,然而南海神必须遥望海洋,不可能利用屏风,故刻意令其轴线偏离,算是一个折衷的方法。 扶胥浴日景不雅观的长消与扶胥港、南海神庙的兴衰险些同步。若是宋朝时于拂晓时分登临神庙西侧的章丘小岗,则看到狮子洋上烟波浩淼,彤霞升起,万顷碧波被染上一层金光,一轮红日从海中跃起,一半仍浸于汪洋之中。 如今登上“浴日亭”,周边景象一片凌乱,只是修葺过的碑刻上苏东坡《南海浴日亭》一诗尚清晰可辨:“剑气峥嵘夜插天,瑞光明来到黄湾。坐看旸谷浮金晕,遥想钱塘雪拥山。已觉沧凉苏病骨,更烦沆瀣洗衰颜。忽惊鸟动行人起,飞上千峰紫翠间。” 历代天子派官员到庙中举行祭典,留下了不少宝贵的碑刻。最著名的是由韩愈所撰“南海神庙碑”、北宋开宝六年的“新修南海庙碑”、明“洪武碑”、清康熙“万里波澄碑”四块,立于院内,建有碑亭,由神兽背负。 庙内石碑共45块,分布于仪门复廊,不少石碑上刻有关于海上“丝绸之路”及广州历史的宝贵资料,以是神庙又有“南方碑林”之称。
庙内现存石碑45块,故神庙有“南方碑林”之称。
专家解惑 采访工具:黄应丰 南海神庙卖力人,广州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广州旅游文化研究会副会长,黄埔区文化局前副局长 记:南海神庙选址有何讲究? 黄:事实上,自秦统一中国以来,珠三角地区就开始了发展的步伐。这一带地皮肥沃,物产富饶,百姓生活安定,不像中原战乱频繁。自汉朝起,海上航路就有所发展,到魏晋南北朝海上贸易已是比较发达,因而隋文帝敕令祭四海,表明此时海上贸易的主要性,已达到不可忽略的地步。 当时南海神庙的选址必须符合三个条件,一必须是军港,可起防御外敌浸染;二是必须有一定常住人口,能常有人到庙中膜拜、供奉和管理;三是附近须有丰富物质资源,以便给过往商船足够补给。 记:神庙的建筑为何选用周朝或春秋时建制? 黄:神庙采取古时皇府建筑建制,正解释它作为官府身份的分歧凡响。 记:运载到扶胥港的商品如何转售到内地? 黄:货色在扶胥港重新装卸后,往东走,经由孔戣指挥开凿的古扶胥运河,进入东江,运到粤东、福建、江西等地;往西从西江到桂江,过灵渠,经湘江,沿长江而下,到扬州;再沿京杭大运河把货色往北运送。 记:达奚司空原来是一个流落异域的外国朝贡使,他与南海神庙本没紧要,却被供奉成神,为什么? 黄:达奚司空是广州过去受海洋文化主导的历史产物,作为一个在中国土地上的“番鬼”神,他是中外进行文化互换的见证;而南海神庙乃古代帝王祭海之地,扶胥港是古代丝绸之路的出发点,二者在文化秘闻上,还是有着某种层次上的联系与共通。
本版撰文: 李小翠 演习生 赖珍琳
本版拍照:本报 黄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