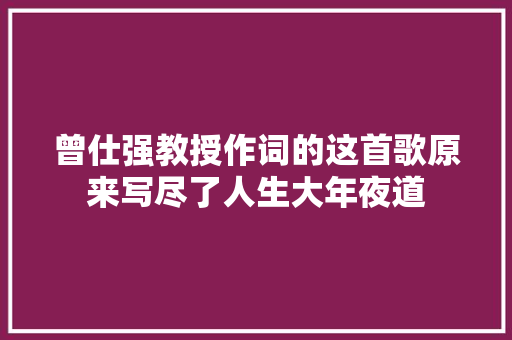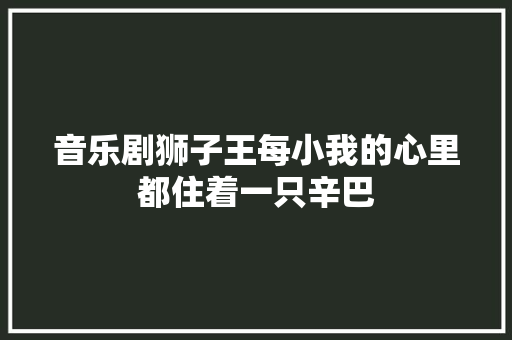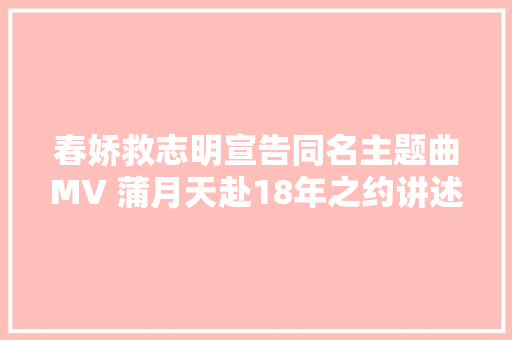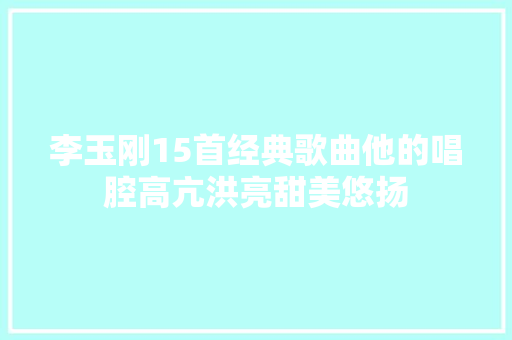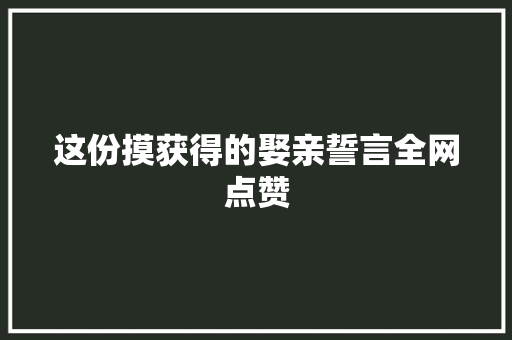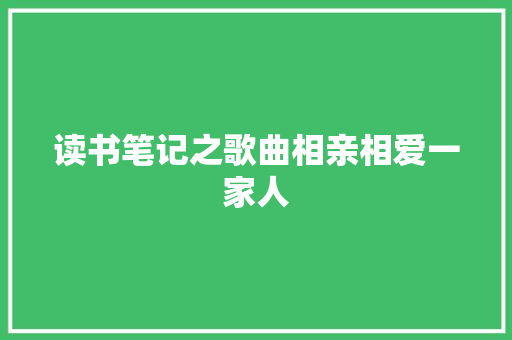我问她好,并诧异她怎么来得这么早,她举头望望我,似嗯似唉应了一声,脸上亦没有平常的笑颜,低下头默默地拉她的犁。
我心里纳闷,跑了一阵,这才记起昨日听母亲说,麦霞嫂的女儿本日出嫁。。

撰文 | 三书
出嫁:之子于归,远送于野
元 佚名《缂丝崔白杏林春燕轴》(局部)
《诗经·邶风·燕燕》
燕燕于飞,差池其羽。之子于归,远送于野。展望弗及,泣涕如雨。
燕燕于飞,颉之颃之。之子于归,远于将之。展望弗及,伫立以泣。
燕燕于飞,下上其音。之子于归,远送于南。展望弗及,实劳我心。
仲氏任只,其心塞渊。终温且惠,淑慎其身。先君之思,以勖寡人。
终年夜真是一件悲哀的事。不得不终年夜,更其悲哀。生,老,病,去世,身体通过这套既定程序,实现它自己,繁衍它自己,末了消灭它自己。怎能不问一句:谁设定的程序?
人间之事,没有一样不是悲喜交集。比如婚礼,自古便称大喜事,但究竟是谁的喜事?早在西周期间,婚礼已形成一套完备的制度,《礼记》中如是论述婚礼的性子:昏礼者,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故男子重之。昏礼者,礼之本也。
也便是说,婚礼是最根本的礼,其最大的意义,大概是唯一的意义,即在于繁衍后代,对付男子乃最主要的事。《礼记·王制》所列六礼:冠、昏、丧、祭、乡、相见,全都针对男子而言,女子附属于男子,并非社会生活的主角。这套婚礼制度延续了两千多年,直至今日,民间仍遗留其部分形式,而婚姻的性子及其强大的社会影响力,在很多地区仍一如往昔。
对付女子,婚姻意味着什么?古代文籍中没有提及,更不被谈论,缘故原由很大略,女子生来便是要配给男子,为他的家族延续喷鼻香火,她在亲生父母家里反倒是客,以是出嫁叫“于归”。此是理,却不是情,合理未必合情。
当今的新式婚礼父母可以出席,传统婚礼父母不能去送,女儿出门便如泼出去的水,不可复返,成了别家的人,花轿唢呐吹奏乐打,欢天喜地的是男方一家。我儿时见过年谁家娶媳妇,门上贴很大的红对联,阁下墙上和堂上贴着大红“囍”字,新媳妇黎明就被接了来,大家便都去围不雅观,抢主家抛洒的洋糖,看新媳妇被婆子搀扶着下车,看嫁妆一样一样郑重地递下车、抬进去,一整天那主家门庭内外来宾熙攘,酒菜喷鼻香味在路上都闻得到,晨昏、窗门、树木乃至家禽,无不洋溢着喜气。
我想众人瞥见的也大都是喜的一壁,彷佛婚礼真的开了人生新天地,却忘了去关心那女子的父母是何心情。表姐结婚时,我上初中,听母亲说表姐被花车接走,我姨和姨父关起门便在家里大哭,还不敢放声,怕邻家听见了笑话。这应是通于天下父母的常情,女儿给人家做了媳妇,不再是自家的人了,在人家里过得什么日子,婆婆好不好伺候,半子体不谅解,纵然过得不好,做父母的也爱莫能助,只能睁只眼闭只眼归结为“命”。我记得那天中午去吃筵,我们外家这边的姊妹亲戚都坐在一个房间里,表姐从表面敬完酒进来,我见她眼睛红红的,平日伶牙俐齿,这时却不怎么说话,像是怕一开口就忍不住要哭。我第一次知道,原来喜事竟也有眼泪,竟也藏着这么多悲哀。
南宋 牧溪《莲燕图》
《燕燕》这首诗,《毛诗序》认为咏的是卫庄姜送归妾,庄姜无子,以庄公妾陈女戴妫之子完为己子,庄公去世,完登基,为州吁所杀,戴妫归陈,庄姜送之而作此诗。这种说法既不合情亦不合理,然而作为“威信解读”被信奉了几千年,和国风中绝大多数诗一样,原来至情至性的歌唱,不幸被曲解为对妇人的道德说教。
另有说法认为此诗写卫国国君送其二妹远嫁,这倒更近人情,亦合乎诗中的“展望弗及,伫立以泣”。诗之兴,譬如画工,写送嫁的人,即诗的叙事者在路上瞥见“燕燕于飞,差池其羽”,飞得那样蹁跹,那样呢喃,不似人间有这许多伤心别离。“之子于归,远送于野”,妹妹出嫁,哥哥远送至郊野,依依难舍,但送得再远终有一别,只好目送她从视线里消逝,直到车马扬起的尘埃也从画面上消逝,他仍在那个断裂的位置,伫立以泣。伯仲之情,亦可以至深若此。
接下来两章,虽是重章复唱,觉得却愈来愈深奥深厚。“燕燕于飞,颉之颃之”,燕子忽高忽低地飞,震颤着贰心中的不安,“燕燕于飞,下上其音”,燕子又忽下忽上地叫,那叫声听得贰心惊。前三章的兴,是诗的措辞,不是伤感,也不是表达思想感情,而是传达出送嫁者的情绪状态,那是没法大略说出来的心情,若非要说出来,必得以这样的兴体。
末了一章,之子已远,送者逐渐规复了理智,亦是自宽之辞。她已经嫁出去了,为兄的也就只能往好的方面想,想着她“其心塞渊,终温且惠”,然不免有些隐忧,故希望她能“淑慎其身”,使先君和他都能放心。
兄看着妹出嫁尚且这么伤怀,做父母的更何消说,或许不去送嫁倒是好过一点。想起麦霞嫂嫁女那天凌晨,门子人都欢欢畅喜吃筵席去了,她独自一人在园里犁地,犁地是重活,本不是女人做的,何况天刚蒙蒙亮,她彷佛没地方可以躲藏,伤心不知如何安顿,彷佛能守在她身边的只有庄稼。
闹洞房:今夕何夕,见此外子
清 费丹旭《探梅仕女图》(局部)
《诗经·绸缪》
绸缪束薪,三星在天。今夕何夕,见此外子?子兮子兮,如此外子何?
绸缪束刍,三星在隅。今夕何夕,见此重逢?子兮子兮,如此重逢何?
绸缪束楚,三星在户。今夕何夕,见此粲者?子兮子兮,如此粲者何?
这是一首闹洞房时唱的歌,歌词活泼戏谑,正是民间本色。
三星,指的是二十八星宿的参宿,三星在一条直线上,即猎户座腰带三星。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在《日知录》中写道:“三代以上,大家皆知天文。‘七月流火’,农夫之辞也;‘三星在天’,妇人之语也;‘月离于毕’,戍卒之作也;‘龙尾伏辰’,儿童之谣也。后世文人学士,有问之而茫然不知者矣。”
惭愧惭愧,我等即后世茫然无知的文人学士,亦因在城市看不到星空之故。为了无止境追求物质生活,我们既阔别了大地,也失落去了星空。可否这样说:我们流放了自身的神性?
上古人看星星,可以知时辰,可以辨方位,可以预测景象。三星在天,在隅,在户,由此可知韶光推移,夜越来越深,从薄暮渐至夜半。
何以见得是新婚诗,而非约会诗?第一句“绸缪束薪”。《诗经》中言及男女婚事多以薪为喻,例如“翘翘错薪,言刈其楚;之子于归,言秣其马。”(《周南·汉广》),又如“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齐风·南山》)。“绸缪束薪”,喻夫妇缠绵,二人命运牢牢地捆在一起。
“今夕何夕,见此外子?”故作反问,恍兮惚兮,亦幻亦真,既惊且喜。前四句可由一人唱,亦可分两人唱,“子兮子兮,如此外子何?”可由众人齐声唱,气氛非常欢快。下二章叠唱也同样,亦可互换领唱。闹洞房多是打趣新娘,外子即新郎,歌者对新娘所唱,唱到心田上。亦有谐谑新郎,“见此粲者”,粲者多数是指新娘,新娘在新居,簇新的衣装,又正当妙龄,人面桃花,红烛高烧,照映得她愈发明眸皓齿,光彩照人。
“见此重逢”,这句很故意思,亲迎之前已经有过五礼,即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但这里却说“重逢”,歌者实在是墨客,由于虽有过那么多隆重的步骤,但男女双方并未谋面,直到此时二人方才初见,可不是重逢是什么。
清 邹其左《仕女图》
这样唱歌谐谑闹洞房,可谓文雅,歌词也极美。闹洞房的习俗延续了几千年,后来文雅渐失落,渐于粗野。小时候,过年村落里谁家娶了新媳妇,也必要闹洞房的,连闹三五天,我们小孩子常去看,主家的门洞开着,谁都可以进去看。新媳妇的房门上挂着新红的门帘,还没到跟前就听见里面繁盛热闹繁荣,悄悄掀帘进去,迎面都是烟气酒气,新郎的叔伯兄弟、朋友,村落里的闲汉、二流子,挤了满满一炕。
新居里什么都新,耀人眼目,炕上铺着红锻被,红的绣花枕巾,漆得光亮的新柜子,新脸盆,盆架上搁着喷鼻香皂毛巾,全都是新的,新娘一身或大红或桃红的新衣,像墙上贴的画中人。只见她端正贞静,坐在炕角,闹洞房的男人们各类刁难,要新娘给他们点烟,若何点火不对若何才对,且要新娘先吸一口,还逼新娘新郎亲嘴,很多人随着起哄,那新娘窘得满脸通红,却只能勉力陪笑。我那时总可怜新娘,恨不能想个办法把她补救出来,要不就把那群男人赶出去。
闹洞房本为图个气氛,不然新婚夜生僻清的,新娘新郎又是生人初见,难免会觉得不清闲,然而这种婚俗愈演愈烈,闹洞房耍泼皮甚至与主家斗殴,乃至闹出人命的也不是没有过。到了二十一世纪,作为一项“陋习”,闹洞房终告衰落。
撰文/三书
编辑/张进
校正/柳宝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