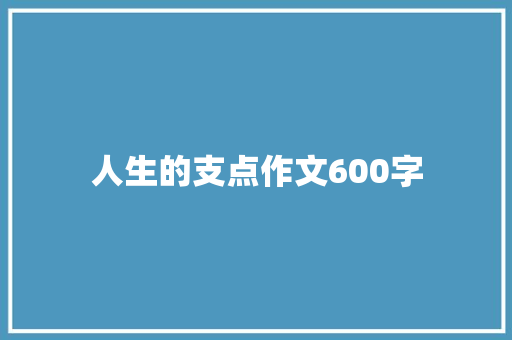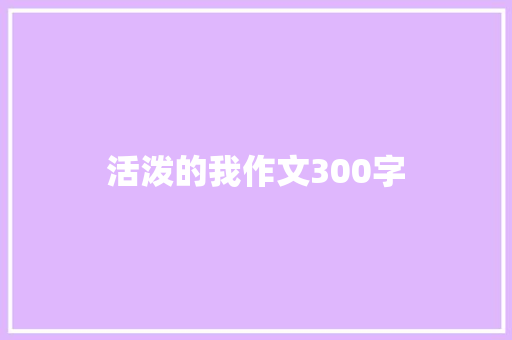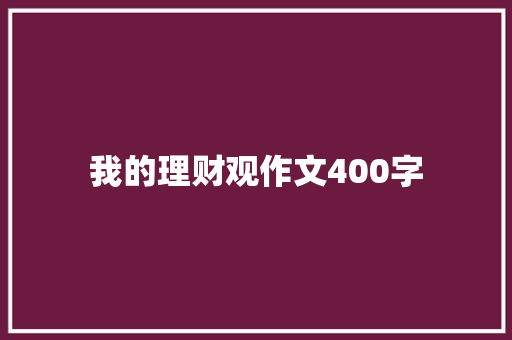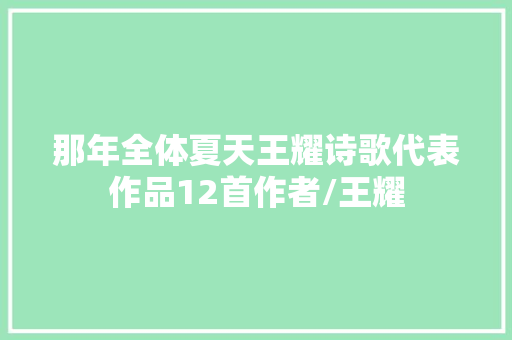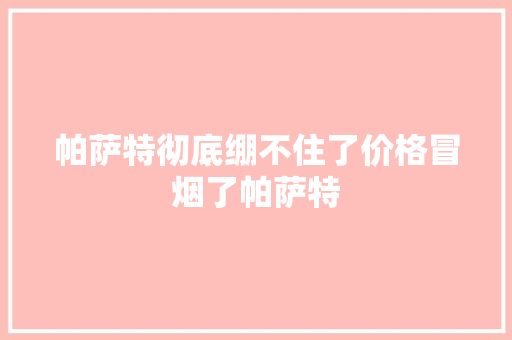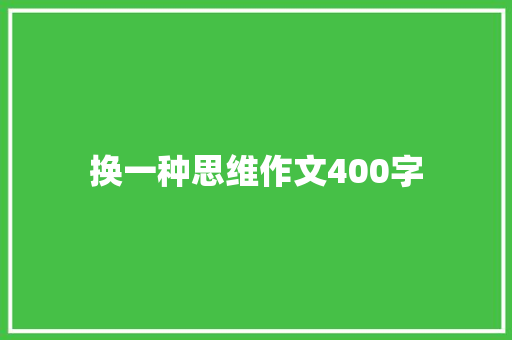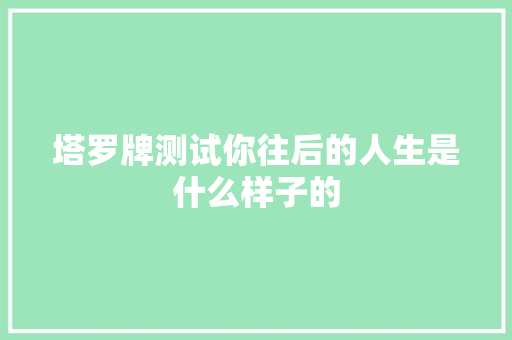这首先是一部走遍雪域高原的亲历实录,是作者用双脚“写”出来的关于西藏变迁的深度调查报告,就像摄影机和录音机一样,页面间连续不断地闪射绽放着千姿万样的声音、色彩、天空、湖水、积雪、绝壁、泪水和血肉。李柯勇是新华社海内部“新华视点”栏目的一位资深调查,多次赴藏,又援藏两年,担当新华社西藏分社副主编,只要有韶光,他都要离开拉萨的住地,深入基层藏区采访调研。这十二三万字的背后,是他面对面独家采访的千百位人物。他在雪域高原来来回回走过的路途,加起来也有几千公里了。他多次赶在历史的亲历者故去之前,登门拜访,记录下他们末了的心声和影象。他自己也因此而多次冒死。如本书中《西藏之路》一章记述的,那确是我见过的、描写得最为触目惊心的西藏死活之旅,由于有他的亲自经历,比如他自己就由于汽车故障而在寒冷的高原与去世神擦肩而过,读来更是太息不已。这部书中既有别人的讲述转述,也有作者的眼见亲历。在李柯勇的笔下,雪域高原的神奇尽现于前,如从天空坠落的千万只纠集在一起的田鸡,骇然泥石流冲出的巨型的无眼鱼群,汶川地震前夕珠峰下村落中群狗的彻夜哀嚎,自然界的奥秘已是如此了,而人文社会的波澜壮阔和繁复缠绕更让人辗转难眠,如那神授一样平常的格萨尔王说书艺人,这已是没有办法用平凡自然科学去阐明的一个谜题。但最打动人的,还是那些对平凡的藏族人的日常生活以及漫长历史中的重重恩怨的朴实记叙,让我看到,在这片地皮上,一个世纪以来,个人的命运是如何被他自己不可控的力量彻底旋转改变,一个民族,一群人,一个人,在浩荡的历史年夜水面前,是多么的无以把握自身。有的人去世了,有的人活下来。但看看他们是怎么去世的、怎么活的啊!
李柯勇写出了多少个“我的前半生”和“我的后半生”,无不触目惊心。难能名贵的是,作者并没有按照某种先入为主的定念去书写这统统。他虔诚于他的眼睛和心灵。
许多隐蔽起来的往事,在李柯勇的笔下,又活灵巧现地复活了。如他用一章的篇幅状写陈渠珍的《艽野尘梦》,以书写书,堪称奇特,不厌其烦把百年前的传奇重述,才让那个尘封的撼人故事重见天日。记得几年前,李柯勇从西藏回京,愉快地要把这本书赠我。我读后大为唏嘘。陈渠珍的自传,讲的是二十世纪初,英军入侵西藏,十三世达赖喇嘛进京求援,清政府派兵入藏,陈以管带身份帮忙西藏地方政府“剿匪”,并与藏族少女西原演绎了一段凄美爱情。后辛亥革命爆发,进藏部队哗变,最高指挥官被杀。陈又带领一百一十五人取道青海逃回内地,途中艰险万状,七个月后只有七人生还。李柯勇对《艽野尘梦》评价甚高,称其笔墨和内容,足以使作者列于当代中国任何一个文学大师之列,而它同时竟也是一本洞察西藏近代剧变的不二精品。难能名贵的是,这本不见经传的薄书是李柯勇在一个有时机会里从拉萨书店淘到的。他读后大为惊异,越日急返书店,把货架上剩余的十本《艽野尘梦》悉数购下。我想说的是,李柯勇是我所见过的搜集各种西藏文献资料的少数“疯子”之一。我曾随他在拉萨淘书,见他不仅买下了店面柜台上的一众书本,还要执意到人家库房里大肆包罗。李柯勇的西藏知识丰度惊人,他并因此而对西藏问题有着独到见地。他读过许多书,从《红史》到《清代驻藏大臣传略》,从宗喀巴的经典到活佛的传记,从格萨尔王到中共进军西藏文献,无不让人叹服。我以为,仅仅有过西藏的行走,而短缺了对西藏的阅读,那么我们眼中所见的怎么也只不过是雪山、青草和喇嘛庙的外表,是没有办法去深入理解伟大的藏民族的。西藏本身是一部大书。随手翻翻,与负责研读,独立思考,是两回事。《点亮一盏酥油灯》是一部关于西藏的书之书,也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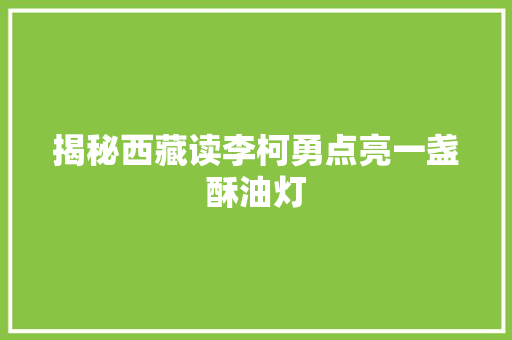
正是缘此,李柯勇由文籍、文献、传说和掌故,由雪山、农舍、寺庙和“牧牛修的路”,一起深入了有关西藏最纠结的那个部分——它那藏在云雾中的历史。仅用十三章节,以小见大,画龙点晶,便勾勒出了一部活生生的西藏简史,更探入了诸多的幽微之处,表露了非此无二的前沿一手资料。李柯勇以凡人弗成思议的坚韧、激情亲切、毅力和聪慧,采访了一大批西藏历史确当事人和见证人,不少已是八九十岁高龄,如进藏解放军将军、西藏叛军司令、老农奴、当年的民兵连长、进藏女兵、土司的后代等等,李柯勇从他们的影象深处,硬是一点一滴挖掘出了众说纷纭的原形。他还搜集并分辨了诸多的史料,像那起许多后来人都没有听说过的甘孜事变,他把汉人、藏人的三种不同说法,“罗生门”一样平常平行列举出来,再根据自己采访到的材料,加以深入阐发。李柯勇力求做到不人云亦云,而坚持自己对历史的主见意见。他的视野具有超越性,同时他的触角尤为细微,这使他笔下的历史,由一个个详细的活人组成,通篇是大量的细节,是友情书,是爱情记,是纷争传,是恩仇录,读交往往以为匪夷所思,拍案称奇。李柯勇自己说:“历史学家们记录历史的过程,每每是抹杀最生动历史的过程。他们知足于盖棺定论,而对那些表示人的最本真状态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的细节,出于各种缘故原由而删除,只留下几句冷冰冰、硬梆梆的结论。”我以为,后人若要深研西藏的历史和现状,李柯勇的这部书是绕不过去的。它更主要的代价,是让人掩卷后再去斟酌藏民族的未来。我以为书中彷佛含有这样一个结论:藏民族的未来,不是由别人授予的,或强加的,或制造的,而是由这片地皮和这个民族的内在逻辑决定的。
因此这终极是一部关于人的书。很多汉人写西藏,只是写写风光,写写习俗,写写游历。还有很多汉人写西藏,只是写写观点,写写术语,写写口号。这是关于西藏的两种最范例、最常见的描述,或许能增长外人对付西藏的“兴趣”或“信心”,却太难让我们真正深入这个民族,有时乃至还会产生误读和误导。而李柯勇这部书的每一章都以人为主角,呈现出一个个活生生的藏族人,当然还有在过去一个世纪里与他们的命运轨迹纷繁交织的汉族人,显现出一个不可回避的事实:是各个民族共同创造了新的西藏史。李柯勇写到的,有喇嘛、贵族、头人、牧民、说唱艺人、学者、军人、司机等等,作为记录,其详细程度常常让人惊叹,包括不少只有西藏人才能讲得出的、才能懂得起的对话,形成了原汁原味的直接引语。作者更试图逼近了他的发言工具的心灵,揭示出人的行为里面具有极大的繁芜性。雪域高原上的平生易近,既有人类的共性,更有族裔的个性,都不能忽略。他还特殊地写到了许多女人,如这部书写到《孤独陈渠珍》,这样开头:“许多年之后,被剥夺了军权和地盘,陈渠珍将军将会回忆起十六岁的藏族女孩西原纵马飞驰而来的那个迢遥的春天。”这是催人泪下的一个跨民族爱情故事。而在《爱情与战役》,藏族女土司德钦汪姆与班禅行辕卫队长益西多吉死心塌地的爱情掀起了高潮;随后又铺陈了更多的进藏女性的动人篇章,到末了扫尾,则是作者本人在高原的死活旅途上结识了自己终生伴侣。为什么?大约是女性是生养万物的主体吧。在西藏,珠穆朗玛峰便是一位女神。雪域高原上的生存是困难的,能够生养后代的女性因此有着特殊的代价,由此也引伸出了这块地皮上独特的死活不雅观。而在讲述奋力求生的传奇的同时,全书又以去世亡的故事串连,这使它尤为令人窒息。每一章都浓墨重彩写到了去世,藏族人、汉族人各种各样的去世,以及人们对待去世的态度。还有比死活之事更大的吗?在世界屋脊这种地方,还有比了却死活更要紧的吗?这恐怕是我们这些养尊处优生活在平原上的大城市里的汉人常常想象不到的。藏族人究竟为了什么,会不惜一去世呢?或许知道了这个,就知道统统的答案了。但我们久久不睬解,因此纠结、疑惑、烦恼、暴怒,失落去了平常心。
由于这些,《点亮一盏酥油灯》留下了许多让读者寻思的问题,读它的时候就像紧贴在喜玛拉雅山的胸膛上谛听它沉重的呼吸。西藏是我们这个时期的一个不可回避的核心命题,是涉及全体人类出路的命题。环球化的背景下,它的繁芜性,它的难以抵达,它的政治化,它的剧变中的不变,还有那永久难以被它之外的人理解的一壁,都无法用大略的言语来说清。那么,探寻一个真实的西藏,既须要勇气、聪慧和知识,更须要做一个脾气中的人,做一个真实而大略的人,这在这个时期是困难的,而李柯勇正走在这条路上。我想,他写作这部书,也大约是要和读者们一起去探寻那些或能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西藏的态度或态度,而这常常是我们的误区所在:
亲近。藏族,是一个格外友善的民族,你对他们好一分,他们便以百倍的好来回报你。而他们又嫉恶如仇,如你刻意搪突,他们定会与你势不两立,战斗至去世。没有情绪的投入,是无法与他们交心的。这种亲比来不得虚假,不能有高高在上西方殖民心态或大汉族主义。历史的环链既可以被阐明得十分的繁芜博识,有时却也是非常大略直接的。
平等。相处既然已这天常间的现实,那么,就要学会以平等的态度去认识其他的民族,从对方的角度和态度出发,去看待其文明,理解他们的文化和宗教,进而尊重他们的心情和行事。不可以以己度人,或越俎代庖。有的误会或将制造出难以弥合的裂隙。藏族实在是很困难的一个民族,他们正经历着其几千年来最大的变故。看看天下上,彷佛很少有哪个社会,像他们这样翻天覆地,乃至从头再来的。全体天下都还须要花费更多的韶光去理解他们。这方面我们要向李柯勇学习。
通达。我一贯以为,这个宇宙中仅有极少几个地方,能使一个人超脱种族而以全人类的视角,意识到我们是共存在诺亚方舟似的同一颗星球上,乃至以超出人类的视角,感悟到我们是与宇宙同一体的存在。这几个地方便是太空站、南极和西藏。李柯勇最打动我的笔触,或许是对珠峰之上那片令人敬畏的群星的描写吧,这一瞬间我们彷佛超越了历史和政治。只有当置身于群星的辉耀之下,重新转头来看这片地皮上缓慢活动着的微小人群,那些牦牛,那些叩长头的朝圣者,那些终生的修行者,那些路边的骸骨以及城堡的废墟,便会滋长出一种大彻大悟感。这也正是李柯勇在珠峰下捡到的条记本上,那不有名的人写下的那首诗,其带来的强大冲击,让人一下空了。或许正因如此,也可以从一个别的角度,去感悟作者说的,“无论是那些出于职业习气而冷漠麻木的人,还是那些囿于政治恩怨而目光狭隘的人,抑或那些陷于一己之私而恶意中伤的人,都该当得到感谢”。的确,无论有多少的恩怨,我们仍将活在一起,直达宇宙的终极。还有什么不可以放下的呢?
像这本书一样,西藏的存在,固然是世间的一壁镜子,能照出了很多的东西,让每个人看到他或她的前生来世,从而让我们满怀感激,但同时,西藏也的确不是任何人可以用来打扮他或她容妆的镜子,它便是它自身的那个灵台。
文/著名科幻作家韩松
本文系转载,已得到作者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