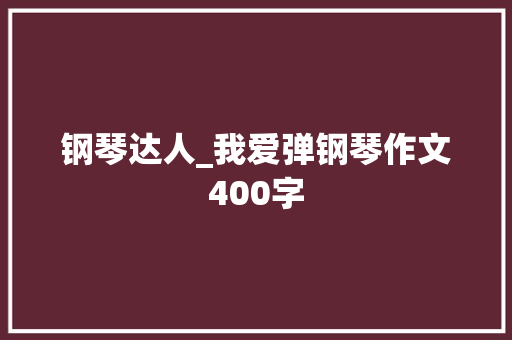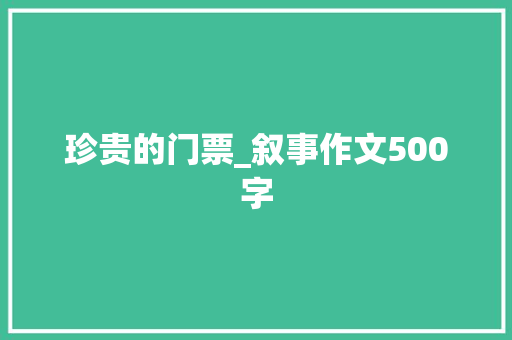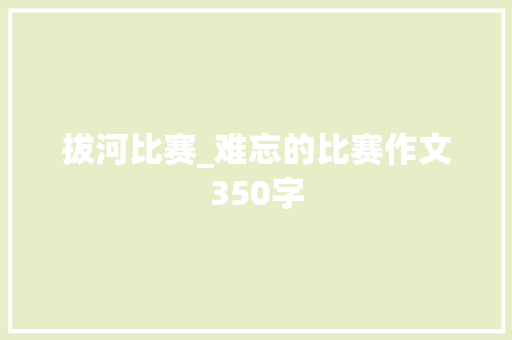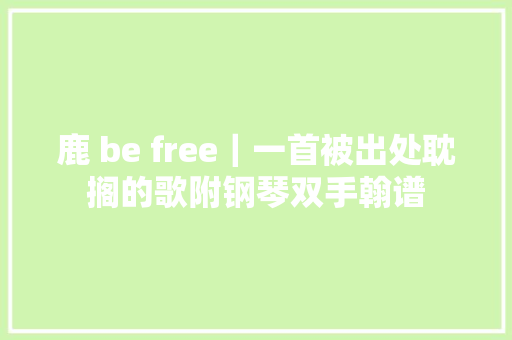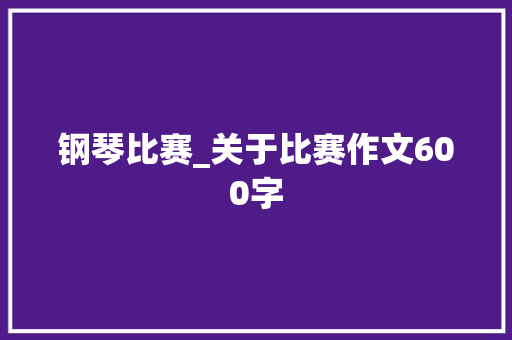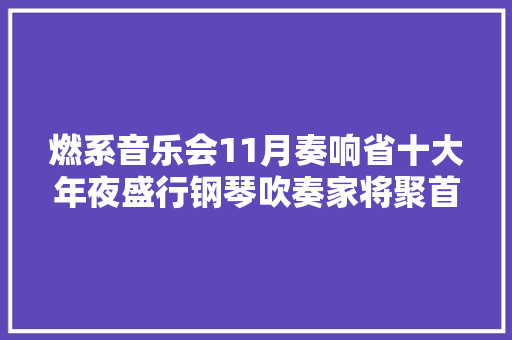快到13岁的那年夏天,一个也在学钢琴的小朋友来找我玩,高兴地说她已经通过中心音乐学院附中(那时叫“少年班”)专业课考试。我一听就急了,我也想考,可是根本不知道招生啊!
于是立即哀求她带我一起去考试的地方。
虽然报名韶光已过,专业考试也已结束,第二天我们两个小姑娘还是一起坐着有轨电车来到考点。两位卖力专业考试的主考老师竟答应越日一早为我安排考试。就在考试结束后确当天下午,我的家长接到电话关照:我考上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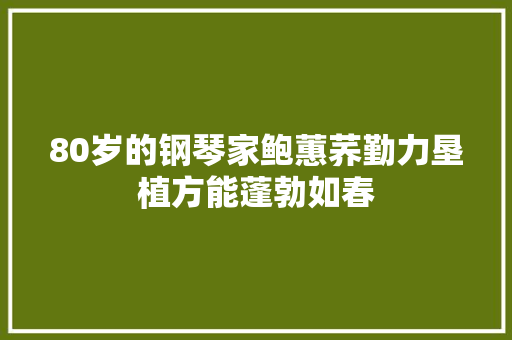
后来我常常想,我怎么会在那么有时的情形下,“一步”就迈进音乐的大门?从知道招生到被录取一共48小时,没有交一分钱报名费、没有填一张报名表、没有考前准备……统统都那么不可思议!
大概是上天看到我对音乐的热爱,于是年夜方地为我打开这幸运之门吧!
1961年,正在中心音乐学院钢琴系读本科四年级的我,被当时的文化部选派参加在罗马尼亚举行的乔治·埃涅斯库国际钢琴比赛。那时摆在我面前的困难很多。我起步晚,9岁才开始学钢琴,短缺踏实童子功;这个比赛共有三轮,必弹曲目中的大部分我没有弹过,间隔比赛只有半年多韶光。准备国际比赛的重担落在两位中国钢琴教授,中心音乐学院朱工一和上海音乐学院范继森的肩上。
彼时正值自然磨难期间,在国家提出的“独立重生、奋发图强”精神鼓舞下,我们师生拼尽全力准备比赛。我们原来一星期上两节钢琴课,朱师长西席改为每隔一天就在傍晚骑车到学校给我上课,风雨无阻而且没有报酬。我自己也在吃不饱饭的分外期间每天练琴8到10个小时。
末了,我和同去参赛的上海音乐学院大四学生洪腾双双得奖。虽然这个比赛不是顶级大赛,我们也没有得到冠军,但是首创了两个先例:中国教授自己培养的学生首次赢得国际奖项,中国选手首次在同一个国际比赛中得奖,在那个困难年代里为祖国赢得了名誉。
今年我80岁了,在这条漫长的音乐道路上,已经走了67年。回望来时路,真的体会到“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高下而求索”!
这是一座永久攀不到顶的高山,也是一场没有终点的马拉松比赛。在近70年韶光里,我一次次经历困境。正值大好年华久久不能上台的压抑苦闷,先后患甲亢、肾盂肾炎、肝炎、癌症的痛楚,右手手腕尺骨、桡骨骨折的绝望……由于心中对音乐的爱,由于有奇迹这个精神支柱,每一次,我都从低谷里走了出来;每一次走出低谷,都感到自己又成熟了一点,倔强了一点。
前几年,几经思考我决定趁自己还能弹琴,要在钢琴上留下一些属于自己的声音。录什么呢?300年来的外国经典作品已经有许多演奏版本,作为一个中国钢琴家,何不专门录一批中国作曲家创作的钢琴曲专辑呢?做出决定后,就开始选曲和练习。没想到的是,想录制的曲目越来越多,突发状况也接连不断。胯骨骨折、颈椎问题导致左手连一张纸都捏不住……一边治疗,一边抓紧选曲、练琴和录制,终于在我79岁这一年完成第一张《中原琴韵·鲍蕙荞中国钢琴曲独奏专辑》。我深知,自己的身体和技能状态都不能与年轻时同日而语,但是我的心依然炙热,这项事情我将连续进行下去,尽自己之力为中国钢琴艺术宝库留下一批中国作曲家的心血之作,也留下我对这些作品的诠释。
现在,弹琴仍旧是我生活的重心,每天均匀练琴不少于3小时,有演出或录音时每天练习五六个小时。很光彩,自己每年还能开全场钢琴独奏会,让更多人听到我的音乐。
我的学生们也在不断发展,很多人在国际海内钢琴比赛中获奖,发展为青年钢琴演奏家。我在日常练琴、传授教化、演奏、担当国内外钢琴比赛评委之外,采写了一套书《鲍蕙荞谛听同行——中外钢琴家访谈录》。这是另一个“无心插柳”的故事:1999年,我完成对自己第一位钢琴专业老师的访谈,无意中成为我访谈钢琴家的序曲。20年过去,我陆续采访百余位中外钢琴家,结集成书后得到出版社“精良作品奖”。
回望走过的漫漫长路,彷佛许多事情都始于有时的“无心插柳”,但是仔细想来,如果没有对音乐始终如一的热爱、对奇迹几十年的执著坚守和持续的费力劳作,无心插下的柳枝又怎会成为片片绿荫呢?惟愿我能连续和音乐相伴相守,惟愿我们的音乐奇迹发达如春。
鲍蕙荞,生于1940年,钢琴家,中心音乐学院客席教授。多次在国内外钢琴比赛中获奖,历任国内外主要钢琴比赛评委或评委会主席。曾任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录制20余种音像制品并获“金唱片”奖,著有《鲍蕙荞谛听同行——中外钢琴家访谈录》,主编《新思路钢琴系列教程》。
(来源:公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