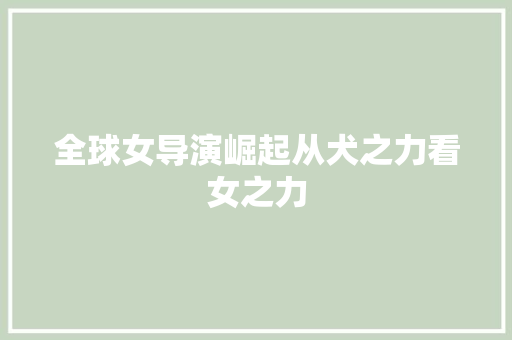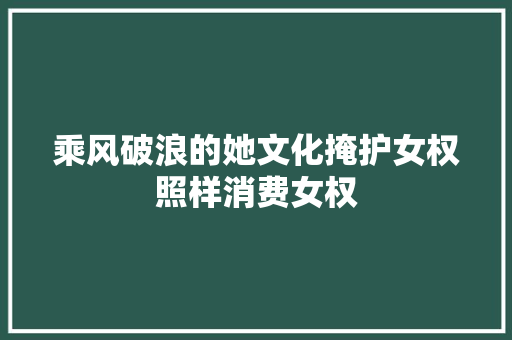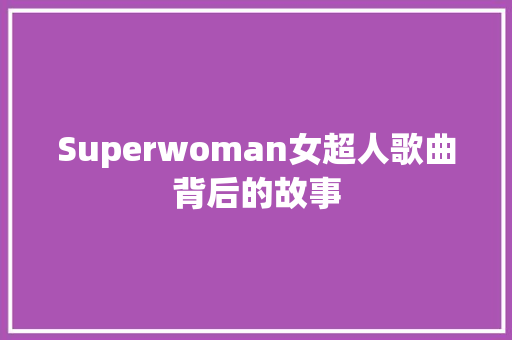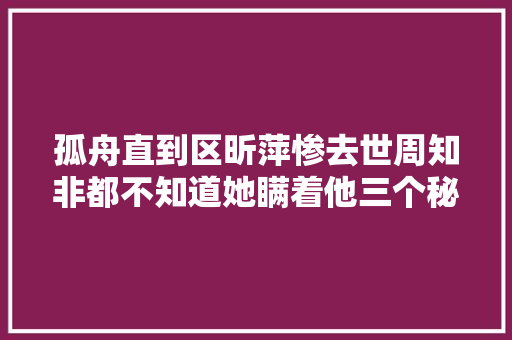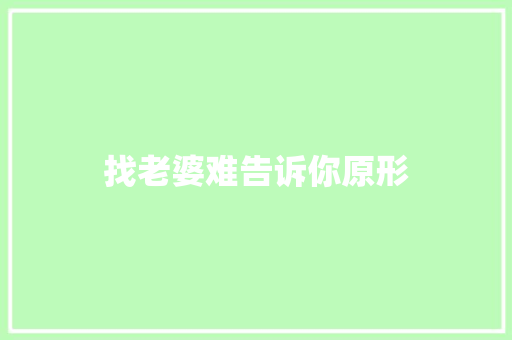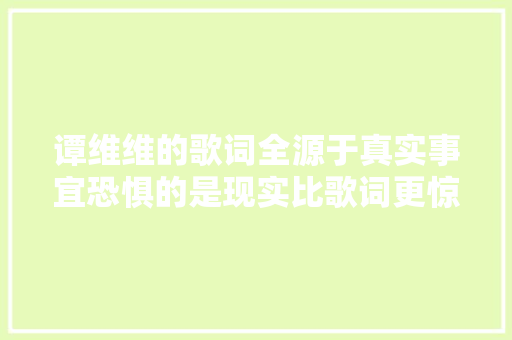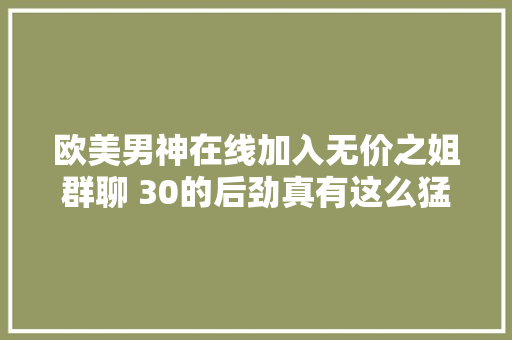宋代是经济、文化相称发达的朝代,受当局重文轻武的影响,文艺处于高度繁荣的状态,仕女画作为艺术之一种,表示了宋代美术的最高水平,人们通过对遗存的仕女画的不雅观赏和解读,对宋代仕女的观点及其在男性心目中的审美形象有了一定的理解。
宋代连续秉承唐朝尊儒传统,故而对女性的束缚很多,这可从宋代仕女画中一探究竟,女性被道德严重禁锢。但另一壁,男性对女性又有着自己的审美需求,我们借此可以认识到宋人对"德"与"色"关系的意见和主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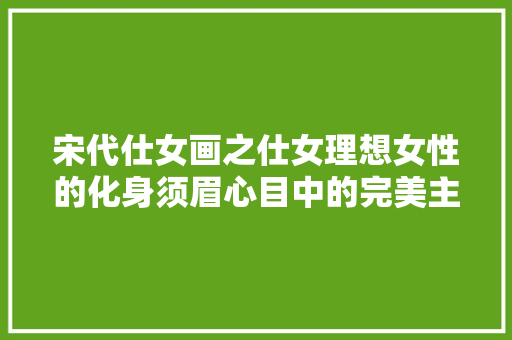
一、宋代仕女画概况
仕女画历史久远,这可以追溯至汉魏期间,只不过那时的画作多以列女为描摹工具。到了唐代,宫廷女性成了绘画重点,宋时,题材与表现手腕进一步丰富,女性形象具有多样性。
士女入画成"仕女"仕女脱胎于先秦时的"士女"。在《尚书·武成》中,有这样的记载,"肆予东征,绥厥士女。惟其士女,篚厥玄玄黄,昭我周王"。
不足为奇。诗歌总集《诗经》也有关于士女的记述,《诗经·郑风·溱洧(wei)》里写道,"维士与女,伊其相谑,赠之以芍药"。再如《荀子·非相》云,"处女莫不愿得以为士。"在王先谦看来,这是"古以士女未嫁娶之称",即未婚男女。
朱景玄在《唐朝名画录》中最先将士女记入画史,称周昉"又画士女,为古今冠绝",称陈闳"善写真及画人物、士女"。诸如此类,不胜列举。
纵不雅观秦汉至魏晋南北朝时的画作,其绘画工具多以风致高尚之列女为主,在皇室眼里,列女便是伦理、教养的代名词,故而受到大肆褒奖。
在唐人的画作中,除了一部分"列女画"外,"嫔嫱"、"美人"等为内容的人物画也不在少数,这些画知足了人们的审美享受。像《历代名画记》云,"罗瑱……画嫔嫱,当代第一"。在《贞不雅观公私画史》里,斐孝源写道,"美人诗意图一卷……孙尚子画"。
到了宋代,"士女"一词屡屡见之于画史。北宋中期更是在画史中将"士女"改成"仕女",如在《图画见闻志》中,郭若虚称周文矩:"工画人物车马,尤工仕女"。进入南宋,美人题材基本上覆盖"士女画"。
在宋代,就表现工具的身份而言,士人家的女性每每成为仕女画首选,这些女性大都出生于官员或较高等别的文人家庭,这与《辞源》对仕女的阐明"官僚家庭的妇女"相吻合。以遗存的宋代仕女画不雅观之,部分女性的装扮及其所处环境与出身官僚家庭无异。
宋代仕女画概貌
在宋代仕女画《调鹦图》、《盥手不雅观花图》、《浣月图》中,唐宋文人的诗词每每成了它们的母题。如唐人于良史在其《春山夜月》中写道,"春山多胜事,抚玩夜总归。掬水月在手,弄花喷鼻香满衣。兴来无远近,欲去异芳菲。南望鸣钟处,楼台深翠微"。该诗所描述的一女子靠近侍女所奉盆洗手不雅观花的情景正是《盥手不雅观花图》的母题。
宋代仕女画其仕女形象大多面部丰满,身材瘦削,这符合宋人的审美需求,亦可见唐、五代人物造型的影响之深。
以《浣月图》为例,画中鲜花饰满女性头部,这是范例的宋代样式。南宋墨客陆游在其《老学庵条记》中载,宋时女性多将"桃花、荷花、菊花、梅花"四季花作为头饰,这些花"谓之一年景"。
牟益是南宋画师,其《捣衣图》场景反响了古代妇女的劳作,不过该图源自南齐墨客谢惠连诗作《捣衣诗》:"衡纪无淹度,晷(gui)运倏如催。白露滋园菊,秋风落庭槐。肃肃莎鸡羽,烈烈寒螀(jiang)啼。夕阴结空幕,宵月皓中闺。美人戒裳服,端饰相招携。簪玉出北房,鸣金步南阶……腰带准畴昔,不知今是非"。
此诗为闺怨诗,描述了秋冬时节妇女在深闺中捣衣的情景,个中孤单忧郁、独守空闺的意味较为强烈。就画中女性而言,她们丰腴、慵
坦白说,画中描述的女性群像与宋代现实生活中的女性有着根本的差异,或者说作者在绘画时压根就没有表达现实的打算,这些按照唐宋诗歌文学作品勾勒出的女性形象,该当是作者心中空想化的表达。
诚然,在营造仕女画文学意象时,宋人显然受到当世盛行妆容的影响,不过能够看出,作者为塑造图像历史感,在衣饰高下了不少功夫。的确,现实生活从来都与真正的空想相去甚远,而营造空想化图像有时真的很须要陌生感。
二、宋代仕女画中的空想女性
历史上总不乏对空想女性的建构,实际上这是男权社会强加给女性的束缚。不过,很多女性也在自觉不自觉地将其视为心目中的空想状态。
在《礼记·内则》中对女性行为准则的规范随处可见,像"女子出门,必拥蔽其面,夜行以烛,无烛则止。道路,男子由右,女子由左"。
汉代董仲舒认为,"丈夫虽践皆为阳,妇人虽闺皆为阴","妇者,服也,服于家事,事人者也",这就为妇女定了"三纲"。班昭是东汉著名史学家班固的妹妹,曾写下《女戒》以倡导四德之仪,"女有四行,一曰妇德,二曰妇言,三曰妇容,四曰妇功。夫云妇德……。此四者,女人之大德,而不可乏之者也。然为之甚易,维在存心耳。古人有言:'仁远乎哉?我欲仁,而仁斯至矣'。此之谓也"。其后,每一朝代对女性的哀求皆以此为本,只管在不同政治、文化影响下各个朝代的侧重点会有差异,并衍生出新的空想,不过就实质而言并没有分开这一根本。
除了班昭,刘向所编的《列女传》也意在树立各种空想女性。众所周知,空想与现实每每并不一致,故而显性的空想常常会与现实或人性的隐性空想有所冲突,在处理这个抵牾时古人的举措值得关注。
边幅之美
在各种有关女德的文献中,不丢脸出总体上都哀求女性保持简朴、柔顺之美。除此而外,也有不少歌颂女性外面和妆容之美的,如《诗经·卫风》写道:"硕人其颀,衣锦衣。齐侯之子,卫侯之妻,东宫之妹,邢侯之姨,谭公维私。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hu)犀,螓首峨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此诗将美人庄姜描述的无与伦比。
常日而言,选入宫中的宫女,在作家的笔下每每成了边幅端丽、美姿容及姿质俏丽的代名词。《晋书》中对武元杨皇后的美做了这样的描述:"后少聪慧,善书,姿质俏丽,闲于女工"。对明穆庾皇后的描述:"后性仁惠,美姿仪"。
实在,秦汉期间空想女性的标准除了道德及品性上的完美,男性文人也非常重视女性的边幅之美。曹植《洛神赋》中对洛神姿容的描写令人神往。南朝墨客江淹《咏美人春游诗》对女性体态、边幅的描述同样让人难以释怀,诗云:"江南仲春春,东风转绿苹。不知谁家子,看花桃李津。白雪凝琼貌,明珠点绛唇。行人咸息驾,争拟洛川神"。
到了宋代,对付女性装扮意象的描写多了起来,像柳永的词作《玉女摇仙佩》中云,"飞琼伴侣,偶别珠宫,未返神仙行缀。取次装扮,平凡言语,有得多少很多多少姝丽。拟把名花比,恐旁人笑我,谈何随意马虎。细思算、奇葩艳卉,惟是深红浅白而已。争如这多情,占得人间,千娇百媚"。
文人是相通的,墨客词人对付空想中俏丽女性的想象,每每会影响画家对付仕女画的创作。在《满江红》一词中,秦不雅观写道,"绝尘标致,倾城颜色,翠馆垂螺双髻小,柳柔花媚娇无力"。晏几道在其《鹧鸪天》中云:"楚女腰肢越女腮,粉圆双蕊髻中开",这些作品中女性的美皆以其细腰为描摹工具。
在秦不雅观《生查子》一词中,李师师的仙颜被树立成女性的典范,词云:"远山眉黛长,细柳腰肢袅。妆罢立东风,一笑千金少。归去凤城时,说与青楼道。看遍颖川花,不似师师好"。那么,李师师果真如秦不雅观所言的那般美妙绝伦吗?有词为证,《大宋宣和遗事》写道,"鬓发軃(duo)乌云,钗簪金凤;眼横秋水之波,眉拂春山之黛;腰如弱柳,体似凝脂;十指露春笋纤长,一搦(nuo)衬金莲稳小"。
由上可见,只管传统上对付女性的道德哀求很高,但宋人诗词中鲜有表示,更多的是对宋代美女的姿容描述,反响了他们对心目中空想女性的审美需求,而这势必对仕女画的创作构成主要影响。
才情卓然
对付空想女性的审美需求,外面娇美是一方面,富于才情也是一个主要评价标准。历史上有关才女的故事比比皆是,诸如汉代的卓文君、班昭、蔡文姬等才貌俱佳的女性故事至今广为传颂。
除此而外,六朝期间有关女性才情的记述也不少,《世说新语》里就提到东晋宰相谢安的侄女及王羲之次子王凝之夫人谢道韫等,"谢太傅(谢安)寒雪日内集,与儿女讲论文义。俄尔雪骤,公欣然曰:'白雪纷纭何所似?'史子胡儿曰:'撒盐空中差可拟。'史女曰:'未若柳絮因风起。'公大笑乐"。
李冶、薛涛、鱼玄机及刘采春是公认的唐代四大才女,她们对诗文无不善于,遗憾的是其身份不是女羽士便是女妓,不过当时著名文人多与她们诗文唱和。如李冶,资质聪颖,终年夜后出家成了女羽士,但与刘长卿等诗文大家诗书往来不断。
进入宋代,女德教诲受到重视。在司马光看来,"是故女子在家,不可以不读《孝经》、《论语》及《诗》、《礼》,略通大义。其女功,则不过桑麻、织绩、制衣裳、为酒食而已。至于刺绣华七,管弦歌诗,皆非女子所宜习也。古之贤女无不好学,左图右史,以自儆戒"。由此可看出司马光对女子教诲的主见,即要将学习各种儒家经典及女教著作作为优选工具。
当然,对那些有学识的女性,宋代文人也持肯定态度。永嘉学派叶适表示,"妇人之可贤,有以文慧,有以艺能,宜其家室而已"。
宋代女性能诗善文的不在少数,据北宋魏泰《隐居诗话》载,"晚世妇人多能诗,每每有臻古人者。王荆公家能诗者最众"。即是说王安石妻子、妹妹及女儿都工于写诗,且"皆洒脱可喜之句也"。不仅王安石,大文豪苏轼的姐姐八娘也富于才学,她"幼而好学,年夜方有过人之节,为文每每有可喜"。
的确,宋代女才子数不胜数,她们琴、棋、书、画、经、史、诗、赋等,彷佛无所不能,虽说唐代才子佳人无数,而宋代远胜于唐。据《全宋文》载,光女词人就超过九十人,词作在三百篇以上;《全宋诗》辑录二百多女墨客作品;《全宋文》也收录十多位女作者文章。据统计,这些才女"上自皇室、贵族、士大夫之家的妇女,下至宫人、尼、道姑、侍儿、樵女、娼妓等等,为数可不雅观"。
不必说写下"生当作人杰,去世亦为鬼雄"大有男儿风范诗句的李清照,两宋间的另一位女词人朱淑真亦令人佩服。只可惜她的诗词后来"为父母一火焚之",去世半个世纪后,宋人魏仲恭才将其诗词整理编成《断肠集》,即便如此,"比往武陵,见旅邸中每每传颂朱淑真词",足见其才情横溢。
实际上,宋人关注她们,除了其文学方面不可忽略的才情外,亦与其不符一样平常女性道德准则的行为有关,而这要么成了男性批驳的缘由,要么成了猎奇之需。
因与文人脱不了干系,使得宋代艺妓多有能文者。有宋一代,文人狎妓之风盛行。欧阳修、苏轼等虽贵为宋代文坛俊彦,然而他们依然改不了对女色的偏爱。据记载,欧阳修对蓄妓、狎妓情有独钟。而苏轼身边也不乏歌妓,在其数百首词作中,涉及歌妓、姬妾的竟然占到五成。
不仅欧阳修、苏轼,其他如柳永、晏几道、秦不雅观、周邦彦、姜夔等文人士大夫都或多或少地存在与艺妓往来密切的记载。
浩瀚妓女打小受到歌舞、乐器的熏陶,后来又常常受到文人士大夫的熏染,于是文艺教化日益博识,自然博得文人的垂青。据《能改斋漫录》载,在西湖嬉戏时,某歌妓以另一种韵词更换秦不雅观词,这使"东坡闻而称赏之"。另据《隐居诗话》,梅尧臣得悉官妓王英英"善笔札,学颜鲁公体,蔡襄教以笔法。晚年大字甚佳",大为讴歌。
诚如今人方建新所言,"在宋代文人眼中,妓女是一个俏丽聪慧,多才多艺,有很高文学教化乃至熟习儒家经典的群体",恰是以,文人才会钟情于狎妓,这除了与他们风骚成性干系外,失落意的时候,妓女的才艺、多情、温顺还能让文人倍感抚慰。秦桧曾受到胡铨弹劾,结果后者遭贬,远赴岭南,一起上幸有侍妓黎倩陪伴,故而在多年后北回时慨然题诗曰:"君恩许归此一醉,傍有梨颊生微涡"。
显然,男性文人从充满才学的艺妓身上得到了猎奇,进而生出猎艳的抱负;在失落意时,她们又扮演着文人空想化的生理抚慰者,于是空想女性应具有的特质便成了男性所抱负的,这从文人仕女画中可看出端倪。
三、宋代仕女画中女性被窥视
只管所谈论的女性空间彷佛将男性排斥在外,而实际上男权社会中,女性一贯受到男性的支配与驾驭,这当然离不开她们的身体。唐玄宗与汉成帝对女性身体的驾驭如何,"环肥燕瘦"一词很好地表示了她们对杨玉环和赵飞燕体貌的审美哀求。此外,"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去世",则将男性支配女性身体的力量彻底暴露出来。
恰如《不雅观看之道》所写的,作者约翰·伯格认为,"在父权社会里,男性可以在广阔天地里驰骋,女性则为了生存,被迫寻求男性的保护,而这种保护,须要她们用自己作为商品来交流。女性是否拥有足够的魅力,给男性留下深刻的印象,将决定她们终生的幸福。因此,这也决定了女人永久只是男人瞩目的工具"。为知足"男人瞩目工具"的哀求,女性也就情不自禁地将自己变成了景不雅观——分外的视觉工具。
男性意识在仕女画中的反响
纵不雅观宋代仕女画,其人物形象每每不针对某一特定女性。以《调鹦图》为例,虽然画面的意涵与杨贵妃有关,不过就其妆容衣饰的宋代特色而言,显然,历史图像的严明性并没有得到画家应有对待。
这些女性形象千差万别,有的刻意将唐代仕女形象作为仿照工具,这在《捣衣图》里得到明证,女性身材苗条,举止轻盈,这种风格明显有别于唐代,而这该当是宋人对女性形象空想化的审美标准,显然,男性便是这一标准的设定者,并且主体来源于男性的诗文。即此而言,男性所想象的空想女性过着空想的生活,就成了仕女画描述的内容。
事实上,男性描写女性生活的作品不在少数。在《西圃词说·诗词之辩》里,清代词论家田同之将"男子而作闺音"视为唐宋文坛假托女性身份创作诗词的征象,"其写景也,忽发离去之悲。咏物也,全寓弃置之恨。无其事,有其情,令读者魂绝色飞,所谓情生于文也"。
这种男性借用女性口吻、模拟女性感想熏染抒怀达意的文学征象可以追溯至战国期间,《楚辞》中,屈原描述现实中的君臣关系时就曾以抱负中的人神之恋做隐喻。其后司马相如、曹植及唐代墨客李白、王维等,无不以女性身份留下干系作品。
柳永是宋代著名词人,他的词作里有不少代歌姬言的内容,这是其借用女性口吻来抒发自己的情怀。
罗兰·巴特认为:
"自有史以来,匮缺的论述恒是由女人实行的:女人栖定,男人佃猎、旅行;女人刚毅(等待),男人重复无常(扬帆而去,到处为家)。女人赋形予匮缺,为它纺织故事,由于她有的是韶光;她一壁纺织,一壁吟唱,织出来的歌词同时表达了滞定(通过嘎嘎作响的纺织)和空缺(在远方,行旅时疾时缓,车骑簇拥)。这么说来,任何一个男人只要一开口抒怀慕远,就一定倾吐女性的心情:这个等待中的,深受等待之苦的男人,很奇怪的,变成了女人"。
从罗兰·巴特之论,可以看出,在表达有类于女性相思、失落落等情绪时,女性或女性口吻自然会被男性模拟或借用。恰是以,描写女性生活及其生理的作品才会大量呈现。而这也该当是宋代仕女画为数浩瀚之由,由于以男性闺音为母题的创作给予了这些画作以灵感和启迪。
女性在仕女画中遭窥视
宋代有不少仕女画因此团扇的形式存在的,该团扇画的特点是小巧、方便,基于此,逐渐成为私密玩物。团扇本身是一个适宜私下消遣的器物,仕女图像托身于此,这样图像功能便无法在公开场合中实现,也就不可能"媚谄于众目"。
宋代团扇广为利用,大臣每每会得到皇家赏赐。既然如此,扇画也就蔚然成风。据《梦梁录·夜市》载,"梅竹扇面儿、张人画山水扇,并在五间楼前大街坐铺"。不仅"张人"善于在团扇上作画,宋人赵彦亦然,据载,他"开市铺,以画扇有名于时"。
不仅如此,女性利用团扇还多被宋代文人吟咏,甚至于团扇每每成了女性的代名词。在《贺新郎》中,苏轼写道,"手弄生绢白团扇,扇手一时似玉"。在《招凉仕女图》、《瑶台步月图》中,女性利用团扇的图像随处可见。
团扇不独女性在用,其他各色人等亦如获珍宝。司马光曾对自己的团扇爱不释手,称"玩之不替手,爱重心无穷"。这表明,画扇被男性、女性高度认可。既然如此,便于携带和收藏的仕女画就自然而然成了男性随时不雅观看女性的手段。
据《后汉书·宋弘传》载,"御坐新屏风,图画列女,帝数顾视之。弘正容言曰:'未见好德如好色者。'帝即为彻之"。这里记述了宋弘告诫光武帝,勿要过多不雅观看列女画像之事。
既然公开场合不便不雅观看,则私下窥视便最好不过。据干系资料显示,宋代市场上美人图像供不应求。据王明清《玉照新志》载,"秦妙不雅观,宣和名倡也,色冠都会,画工多图其貌,售于外方"。
以女性主义视角而言,俏丽女性向来是男性不雅观看的源头及内容所在。男性文人在公开场合窥视女性后,每每趾高气扬,而后将女性的仙颜描述下来,以便从视觉上对其霸占。实际上,就不雅观看或窥视女性而言,实质上是男性知足与实现性欲的表现。
事实上,男性在实际生活中是无法不雅观看到女性私密生活的,但是图像就不同了,一旦他们坐实拥有了女性图像,便可透过视线侵入女性的私密空间,从而仔细窥视她们的私生活,于是男性的不雅观看癖和窥视癖便借助这些"想象的替代物"得以知足。
宋代仕女画内容多涉及闺怨,而这种闺怨存在的标志为不在场却能对女性进行主宰的男主角。仕女画如此,某些文人的诗词亦对装扮台前的场景做出了合乎想象的描写,像《蝶恋花·紫燕双飞深院静》,作者秦不雅观就对女子装扮打扮的全过程进行了详细描写,"紫燕双飞深院静。簟(dian)枕纱厨,睡起娇如病。一线碧烟萦藻井。小鬟茶进龙喷鼻香饼。拂拭菱花看宝镜。玉指纤纤,捻唾橑云鬓。闲折海榴过翠径。雪猫戏扑风花影"。
词作不仅着眼于女性装扮之美的描写,亦对女子思念情人的幽怨进行了有力渲染,一位不在场的男主角尽显一旁,此人或为墨客自己。男性借助仕女图的瞩目,一方面视觉希望得到了知足,此外对付发生在庭院中的爱情故事,尽可能地将自己想象为男主角。
结语
宋代尚文,故而文化上的高度繁荣让人钦羡,这不仅表现在文学上,也反响在美术绘画上。宋代仕女画便是一幅幅流芳百世的艺术珍品。
仕女一方面指画家画的美人,其余也指官僚家庭的妇女,这两方面有着一定的交集。古人向来以儒家思想教诲女性,以便规范她们的言行举止,而实际上在文人诗作中很少看到,反响了男性文人对付空想化的女性的审美方向,那便是女性不仅边幅娇美,还要富于才情。
于是基于唐宋诗文大家的佳构力作,宋代画师发挥自己的想象,将不同风格的仕女图像呈现在世人面前。显然,这些仕女形象与宋代实际生活中的女子多有出入。
在男权社会中,包括仕女画在内的大多数人物画都存在着强烈的男性意识。仕女画不仅供应了男性空想化的女性形象,还被男性在实际生活中窥视,而这给了男性不雅观看女性以便捷路子。
实在,不论画作的主题如何,男性意识所勾勒出的空想女性形象,无不出于知足男性不雅观看须要之考量,故而扇面上仕女也好,装扮台前的仕女也罢,都是为了一个本应在场却缺席的男性存在,即此而言,画中人与镜中人都受他制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