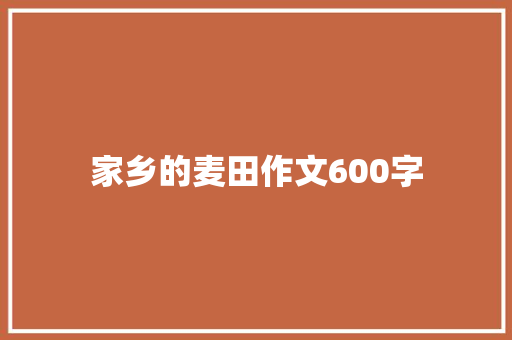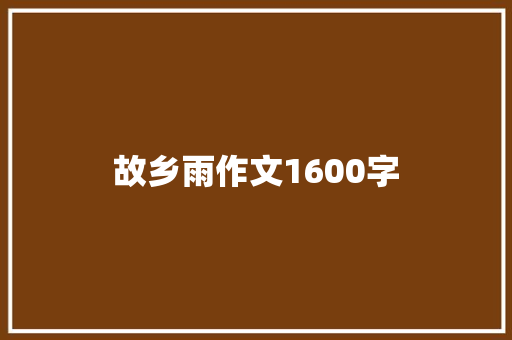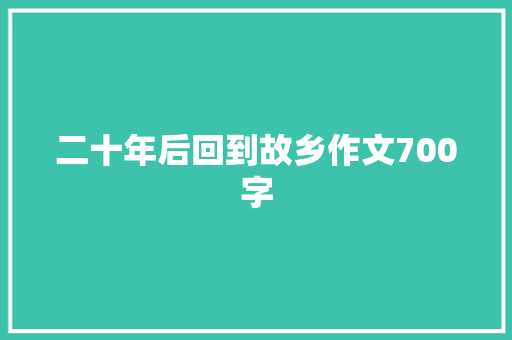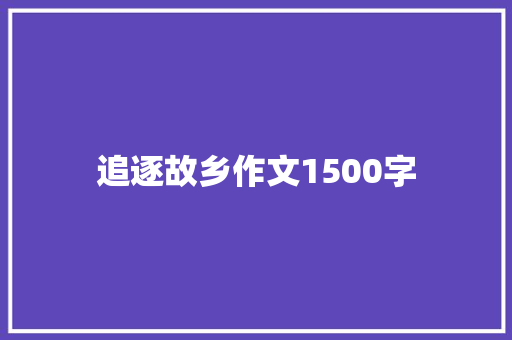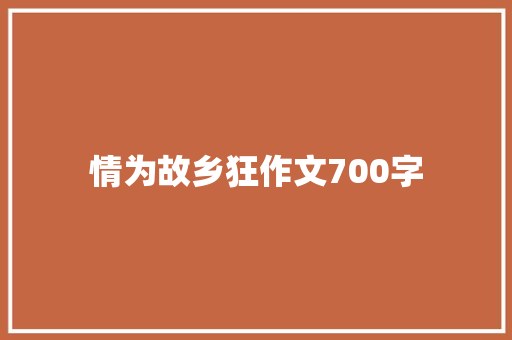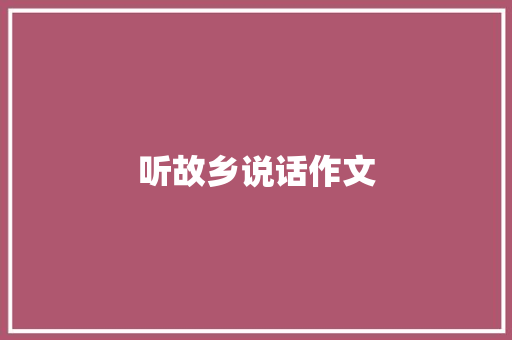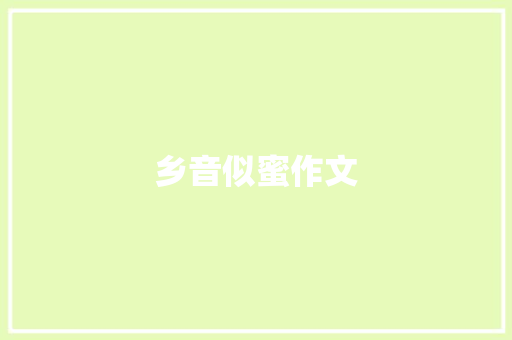《燃烧的麦田》是作家韩浩月新著,剖为上、下两辑,共21篇散文。这些文章原来是《湖南文学》“双城”栏目的专稿,每月一篇,持续了整整两年。
一贯爱读韩浩月的美文,只要有缘得见,便不会错过。但由于是期刊,读得断断续续,加上篇与篇之间连贯性不强,我对文章中的“我”并未给予太多的在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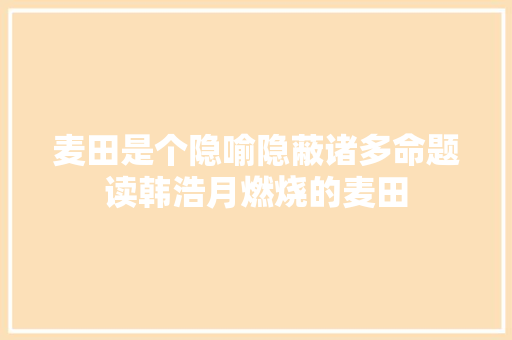
前两天看到韩浩月发在朋友圈里的短视频,我才知晓,那是一篇篇非虚构散文——上辑说的是他在外省生活当中的一些所思所想,一些个人生存状态的呈现;下辑则写了他在故乡碰着的一些人、一些故事和一些细节,诚挚真切真情。
韩浩月的故乡在鲁南郯城,是山东最南边的一个县,与江苏省接壤,地理上属于北方,但多少也有点南方景象的特色。他生于上世纪70年代中期,可谓“北漂”族中的精良分子——作家,文化评论人,影评人,出版有“故乡三部曲”,评论集《座无虚席》等20余种。
二
故乡是作家的生命起源,也是作家的精神归宿。
韩浩月写了包括《宇宙小镇》《陌生之地》在内等多篇表现外省生活的文章,但引发他“所思所想”更多的,还是生于斯长于斯的故乡。故乡与异域,从来都是孪生的,从异域看故乡,异域是延展,也是遥望。
“有的老人,一辈子也没走出过自己的村落落……我便是在这样的环境下终年夜的,童年以为村落落便是全体天下,少年以为县城便是全体宇宙,每一次生存环境的变革,都会带来发热般的体温变革,那是对付陌生的恐怖。我记得十二岁第一次到县城,就被四五层高的楼房震荡到晕眩。”(《陌生之地》)
让人感同身受的,还是他年少辰光那一场场难以忘怀的“苦雨”:“我住在村落庄的土坯屋子里,屋顶是稻草苫的,每逢下雨,无论大小,必漏雨……”以至那一串串雨滴,“从童年穿过了我的少年、青年期间,直逼我的中年光阴。”
高处的天,高处的风,高处的景象……皆为低层居住者无法领略的风景。韩浩月爱住顶层,而且“从小就喜好”,是否由于这个?私下揣测,这种“喜好”大概是缘于一位作家的理智和敏感,但更有可能是他想刻意回避岁月给予的尴尬,以是才会有“淋过雨的人,不会忘却带伞”的感叹。
雨水无孔不入,渗漏了墙壁,也打湿贫穷苍白的村落庄生活。韩浩月不满现状,逐渐有了离土离乡的动机:读月朔那年夏天,暑热未消,“几亩地的玉米,彷佛永久也掰不完。有一天晚上,掰玉米掰到半夜,在明晃晃的月光下,一个人掰玉米的动作显得无比不真实,夜晚的劳动,有一种不正当性,无论怎么勤恳,都被授予了盗窃的嫌弃。我便是从那个时候起,开始有了要永久逃离种地的初心。”(《燃烧的麦田》)
光阴总留给我们最真实的印记,在这浮华的凡尘之中,无论精神多独立的人,情绪却总在探求一种寄托,探求一种归宿。韩浩月如此这般剖开胸膛,让我们看到了那颗年轻的红彤彤的心。
三
“非虚构”散文是一种新的写作姿态,一种文学的求真实践。我之以是不厌其烦地摘抄韩浩月的原文,是想通过梳理作者的人生轨迹,从中透射出朴实的生存意识和生命状态,真切地还原作家生命深处的大众情怀与平民情结。
人生无非“生寄去世归”。“生寄”,是“在世操心”,是“尽形寿”;“去世归”,则是回到原点,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作为一位出色的时评作家,韩浩月会怎么想?
春节返乡,韩浩月带孩子上坟,那真切真情的话语,彷佛是给说给孩子听的,又彷佛是自言自语:“对付你来说,上坟是一件挺讨厌的事情吧。对我何尝又不是呢。且不说小时候不喜好上坟,成年后也不想,每次从县城去偏僻村落庄的祖坟上坟,都是一次困难的磨练,每次上完坟离开,都有如释重负的觉得。但是,又怎么能不去呢?那些埋在土下的人,是我们的亲人,是我们的来路,逢年过节的时候,怎能忍心他们的坟头,孤孤零零.....”(《带你回故乡》)
“我的家乡自古就有这样的传统,一个人走了,他生前用过的物品,包括穿过的衣服,盖过的被子,等等,越是贴身的东西越是要烧掉。这可以视为一场残酷的打消行动,也可以视为一种永恒的纪念……”
“白事的末了一个环节,送亡人去埋葬之地途经桥梁时,亲人要喊一声称谓,并加-句‘过桥了’的提醒,有的地方,还要扔一串纸钱,或者点一个鞭炮。我数次目睹或亲历过这一场合,每次听到‘过桥了’这三个字从口中悠悠发出之际,都以为车轮变缓、韶光加速、光芒骤亮或骤暗……”(《桥下桥上》)
中国人讲究圆满,生前有祖宗护佑,去世后有子孙敬拜,多好。但涉及死活命题,众人谁个敢言已经参透?古往今来,又有谁个敢言曾经参透?
每一位从村落庄出发的作家,大抵是离不愉快中那一方圣土的。从江苏高邮出发的汪曾祺说:“我念的经,只有四个字‘人生苦短。’由于这苦和短,我马一直蹄,独行其是。”
“未知生,焉知去世。”为人子为人父的韩浩月以平实的话语,道出了中华民族的传统丧俗,也写下了贰心中最为真切感想熏染:命若流星,唯笔墨永恒。
四
村落庄是熟人间界,无论是生老病去世,红白喜事,还是建房砌灶,参军上学……无一离得了酒。即便是世仇,亦可用一杯酒来化解。
粗粗数了数,收录在《燃烧的麦田》里的21篇文章,至少有11篇写到了或浓或淡的酒。特殊是那些书写故乡的笔墨,字里行间都飘散着醉人的芳香。“可以穷,但不可以穷得喝不起酒。”(《酗酒者与故乡》)“在故乡,一个人会连着其余一个人,一件事会连着其余一件事,而想要认识人、办成事,最好的办法是从一个酒桌到其余一个酒桌。”“萍又调集大家饮酒了,今年我们聚了三次,创造了一个新的聚会频率记录。”“那顿饭,大家喝了不少酒,喝完酒便会哭,独自哭,双双抱着头哭,哭累了换一个人再连续哭,类似的戏码,上演了多年,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多委曲和眼泪。” (《羁人与原乡》)
常听人调侃,酒风便是作风。这话难免不免有失落偏颇,但饮酒的确最能窥见一个人的脾气——厚道与狡黠,好玩与无趣,爽直与造作……尽在一杯酒中。
韩浩月饮酒,没架子不欺生,善饮之根基是否缘于那一次“酒精中毒”,我们不得而知,但他那豪迈之风格,其实让民气生欢畅。
2021年11月下旬,我与韩浩月老师重逢于兰溪李渔戏剧节。有天晚上,我们在兰江边上的一家小酒馆宵夜,由于脾气相投,他来我往,一杯接着一杯地喝。明天将来诰日一早,我竟想不起昨晚是如何回到宾馆的,只依稀记得韩浩月答应回京后送我一本新出的集子。
“宽心应是酒,遣兴莫过诗。”不久,韩浩月果真给我快递了《万物皆有光》,扉页上题签的,便是这两句杜甫的诗。而在书评《阅读的红利》中,我也写下了自己的真实心境:“一张酒桌,实乃一个江湖——说过的话,答应的事,实在是可以欠妥准的。”
最是“真”字打动人。这一回,他又寄来新著《燃烧的麦田》,并题签说:“故乡睡了,麦田醒着。”
五
记得郁达夫曾说,当代散文的“最大特色”是作家“表现的个性”。在《燃烧的麦田》中,韩浩月为流落者画像,以细腻灵动的笔触烛照他们的心灵,无疑是颇有“个性”的作家——喜好“在夜归的路上看过星星,在拥挤的人潮守望麦田”。(姜业雨语)
“麦田”实在是一个隐喻,而韩浩月便是那株被故乡滋养的幸运麦子。诚如东方卫视著名主持人曹可凡所说:“《燃烧的麦田》和他以前的作品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我相信这种变革是韶光和年事授予的,也是体验与思考授予的。但他同时也有不少稳定未变的地方,比如诚挚、纯粹、激情亲切。”
(作者系浙江省金华市作协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