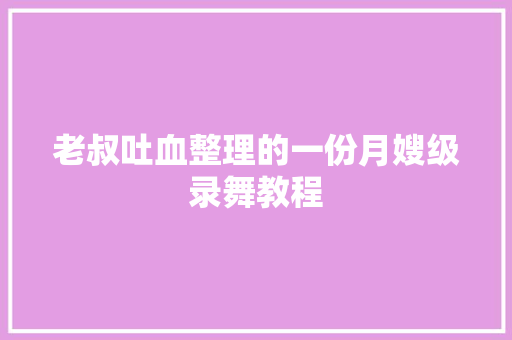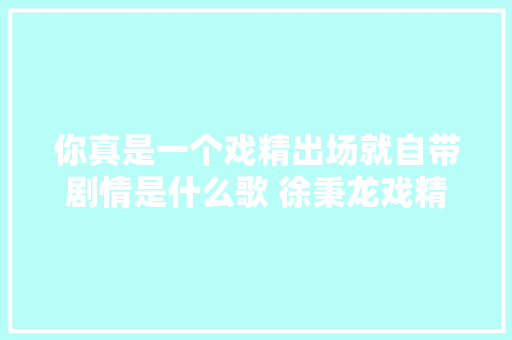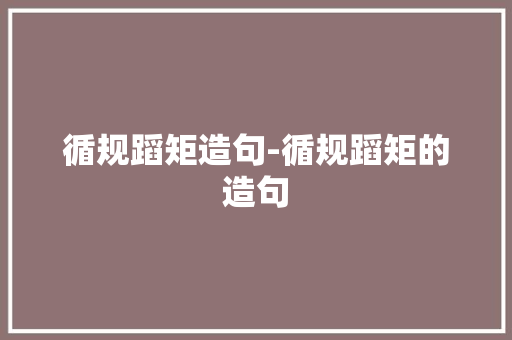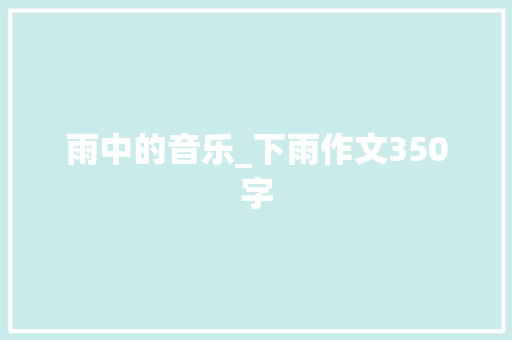让韶光慢下来
泡一杯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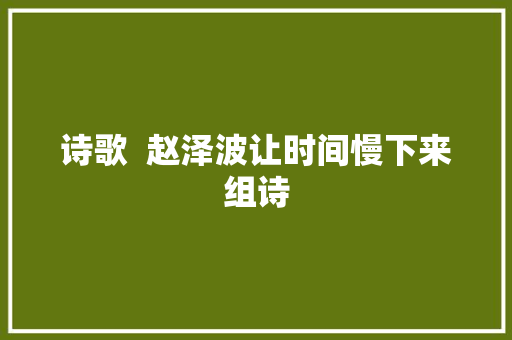
看茶叶起起伏伏
直至稳稳沉入杯底
泡一杯茶
看热气袅袅升腾
直至不再模糊双眼
汤色逐渐变浓
心情就开始透明
当汤色一点点由浓转淡
天色也一点点由明转暗
光阴就慢下来了
先是慢成一截
拉长的影子
末了慢成杯底的一滴
无嗅无味的沉默
一些事物原地不动,却在一步步走远
就这样,一棵老树
在我的影象里静穆了几十年
而今,我分明瞥见它
正从一张小小的方案图里
从粗糙的树皮里
从我手指的温度里
一动不动地
一步步走远
几天后,一个数着年轮的树桩
是它走过的足迹
很多时候,一些事物
也包括一些人
就像这棵老树
虽然在面前原地不动
却已在悄无声息中蚁行或飞奔
一步步走远
直至空空如也
那就走吧!
谁也无法掌握
一些真实的事物,以静穆的姿势
原地不动
却让我们清楚地瞥见
它们的背影渐行渐远
这些事物包括万能的时空
也包括此刻的我们——
我明明瞥见另一个自己
一点点地
从身体里逃离
从地铁穿越人间
自动扶梯一直迁徙改变
背影彭湃如流水
瞬间被伸开的深邃吞没
沿着一个个箭头指示——
人浮于世
终极都走向地下
飞驰于地下的列车
载着一张张来自地上的面孔
来来往往,进进出出
让人知道
地下也有匆忙拥挤的人间
地铁飞奔于另一个天下
窗外灯火拖着长尾
也追赶不上车厢里
任何一个人的一小段儿命运——
每一辆地铁只能承载你
一小段儿旅程
而车上的每个人
也只能陪你走完个中
一小段儿人生
地上繁华,地下繁忙
乘坐地铁
恍若穿越人间
一次次把人间悲欢
带到地下
又一次次把离合从地下
带回人间
城里的大树
跋山涉水,千辛万苦
大树们被当代化的工具连根拔起
然后,一夜之间
离开熟习的野外、村落庄和
脚下那些卑微如臣民的花草
在另一片坚硬的森林里落地
重新生根
统统都是陌生
连自己参与制造的景不雅观
都和人群一样陌生
再也没有聒噪的鸟鸣和树叶的合唱
有的是机器马达和人间的鼓噪
大树们习惯用长久的沉默
回望迢遥的村落庄
没有根基
统统都那么薄弱
再结实的拐杖也难以扶正腰身
再营养的点滴也治不了水土不服
稀少的泥土承载不起高大的站立
一场平常的狂风雨后
大树们纷纭倒下
稀疏的落叶
是它们末了的眼泪
没有倒下的大树和
树下劳碌的农人工
还在一直地共同移栽
一幕幕村落庄疼痛的风景
故乡的石缸
几十年没有遇见一滴水
你装下经年沉淀的岁月和
清亮透明的回顾
以是变得
如此沉重
斑驳粗糙的缸身
没有任何人文润色的图案
不成行的錾脚
笨重潦草
一如最初主人的出生
缸沿还小心地保留着
当年的细腻
那些被各种刀刃磨出的弧形
一如穿梭于缸边的
一代代亲人们
起起伏伏的人生
如今,洗尽灰尘
搬进重修的新居
你已重新注入老井的清泉
让一个关于水和缸、缸和水的
断篇故事从此接续
并保持生活的湿润
永不干涸
轻轻
蒲公英乘着风的翅膀
随意飞舞
我看到了一个词语
薄如蝉翼
柳丝拂动湖面
唤起几声鸟鸣
我听到了一个词语
如歌行板
你的嘴唇微微翕动
芬芳洒脱
我闻到了一个词语
气如幽兰
在经历过多沉重之后
总会有一个温暖的词语
牵着我的手
诗意般到来
让我卸掉尘土、泥泞和眼泪
健步如飞
她来无踪去无影
让我不得不写下这首诗
并铭记她的名字——
轻轻
尾月二十九或怀念爷爷
您的生日
是百口的节日
手执九十六载的漫长和波折
您用眼中低矮的沉默击退岁月
守护一个田舍百年的
疾风骤雨
云淡风轻
而今您拜别三年
怀念已芳草萋萋
在故乡的一座山上
您和老屋一起,为后人
坚守末了一抹乡愁
又到尾月二十九
本日,我们会用美酒和欢笑
擦亮这个日子
让关于您的统统
崭新如昨
无名坟
没有名字
也没有标志
就像坟旁的花草
通通叫不出
一个确切的名字
一个小小的隆起
即将被地平线淹没
有谁知道下面
一个曾经鲜活的生命
走过了多么繁盛热闹繁荣或者
多么寂寞的
人间
石磨
还在童年的那个位置
仿佛刚刚戛然而止
只是高下磨盘咬得很紧
像被一圈圈的故事粘合
一阵熟习的轰鸣
从磨缝中传来
磨盘还未迁徙改变
一把把金黄的岁月
就已钻进磨眼
被磨得粉碎
而那些推磨喂磨的人
早已走远
母亲的镰刀
银光闪闪
齿锋密密
母亲最喜好用这把镰刀
割倒谷穗和麦穗的成熟
割回青菜和柴禾的守望
割去刺藤和杂草的缭乱
母亲波折的身影
好似一把巨大的镰刀
在野外上一直的移动
镰刀挥舞之处
所向披靡
不知什么时候
岁月悄悄黏附在镰刀上
比镰刀更锋利
母亲在收割时
欠妥心
把自己也割倒了
如今,那把镰刀早已石沉年夜海
而倒下的母亲
在一片拔节声的支撑下
竟然逐步的站了起来
却再也直不起腰
直到有一天太阳照过来
我才创造,那把久已丢失的镰刀
原来并没有丢失
一贯稳稳的藏在她
苍老的身影里
连枷
连枷一响颗粒归仓
高高扬起的
是庄稼人藏了一冬的激情
重重的拍打
是对粮食爱得深奥深厚
枷板挥舞自若
节奏紧随心跳此起彼伏
“一夜连枷响到明”
村落庄自有生活的交响
会打连枷的人
手持沉重,内心轻盈
力量是一种幸福
从手心源远流长
再累,也要把自己谱成一首山歌
远远的唱响
碓窝
你像一个老人
佝偻在老屋门前
岁月在额头爬满青苔
一任窝里杂物丛生
深不见底
我藏着的那个童年呢
你把它藏在了哪里
舂米的繁忙
糍粑的飘喷鼻香
你仅有的功能不可或缺
制造古老村落庄最粗糙的劳动
那时候的窝底
像庄稼人的苦处浅而易见
他们习气在最底层
舂击出一条小路
安顿下一代代谦卑而顽强的生活
循着窝沿微微开裂的缝隙
我清晰地瞥见一个个熟习的影子
牵着我从里面
匆匆的途经
在龙泉驿遇见桃花
很多年了
没有读到这样旷达纵漾的诗行
漫山遍野
一如盛大的歌舞
泛滥成迢遥当年
粉红的回顾
多少年了
我背井离乡
怀揣八百里加急
错过你葱绿的眼神
错过阳光的手指
一错再错
而你还在这里
在龙泉古驿
不紧不慢,把自己一遍遍打开
直至彭湃成一片花海
只为本日这一瞬
炽热的遇见
前路漫漫
我将打马归去
一起向东,向东
我知道,你的呼吸
将在我急匆匆的马蹄声里
延绵成无尽的温顺
洛带薄暮
终于安静下来
夕阳一挥手
就把无数缭乱的脚步
逐一送回远方
七拐八弯的古街停滞了拥挤
开始整理一天急匆匆的呼吸
会馆、宫寺、塔楼、院落和牌坊
安详如初
让光阴的手指悄悄盘摸
尚带体温的包浆
我也安静下来
在余晖中回望伤心凉粉店里
客家小妹那一瞥火辣的回眸
一串带状的笔墨
溘然在掌心里飘舞起来
轻轻的遗落在一个
两千年的名字里
——洛带
在宝箴塞遇见岁月
沿光滑的石阶而上
岁月从消逝的棱角开始蔓延
厚重的黄荆木门缝隙
已盛不下一缕回顾
抑或欢快与悲哀
那口老井
还能捧出黝黑的液体
像眼泪或汗水
但已照不出过往的眼眸
一些东西早已在夜晚沉淀下来
却通过井底的暗道远远亡命
从此杳无音信
戏台的戏早已谢幕
被修复的木雕
故事也已泛黄
依稀的反应
来自游人的脚步
他们缭乱的命运
以模糊的背影为背景
正在台下匆匆上演
被粉饰的塞记
终于被岁月扒开
原形大白
那些被称作珍宝般的箴言
犹如散落的尘埃
在落地的那一瞬间
选择沉默
在宝箴塞遇见岁月
遇见百年孤独
在挥手之间,实在
每个人的自己也被遇见
且从此不再分离
雅安记
雅雨、雅女、雅鱼
一个雅字,一个个雅字
让我仿佛掉进一个
深深的温顺乡
不能自拔
一袭青衣
流淌多少缠绵故事
一眼温泉
融化多少体内寒冰
谁不说
温顺是你的名字
那就让我深深掉落之前
登上周公山
在梦里,做一回周公
然后雄性地醒来
走过上里
岁月在这里变得
无比清澈
彷佛统统流动的东西
都变得无比缓慢
包括目光、脚步和背影
我须要在二仙桥上坐下来
回望韩家大院的精美雕刻
看它如何镂空我的影象
五大姓氏如今散落在哪里
那些上演的家长里短
是否已被老戏台遗忘
走过上里古镇,才创造
自己还可以和自己对话
小桥流水,小雨薄雾
都是甜的呼吸
美的话语
作者简介:
赵泽波, 70后,四川武胜人,四川省作协会员。12岁开始揭橥作品,诗文散见于《公民日报》《作家文摘》《诗刊》《星星》《绿风》《草堂》《草原》《中国墨客》《知音》《读者·西部人》《青年博览》《大河》《阳光》《四川文学》《延河》《青年作家》《思维与聪慧》《散文诗天下》《岁月》《辽河》《作家天地》《山东墨客》《椰城》《少年文艺》《澳门月刊》《大海洋》(台湾)《澳华文学》(澳大利亚)《国际日报》(印尼)等数百种报刊。获各种文学奖十余次,出版诗文集7部。现居广安。
【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欢迎向我们报料,一经采纳有用度酬谢。报料微信关注:ihxdsb,报料QQ:33864057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