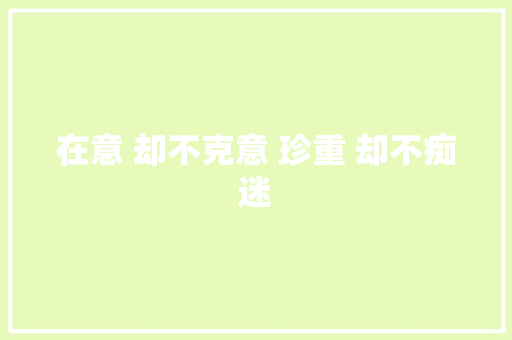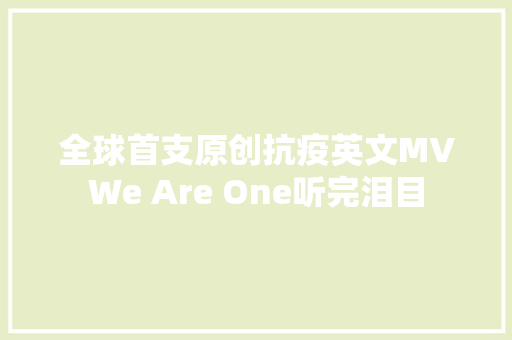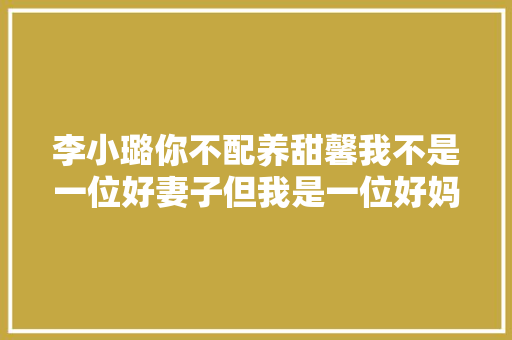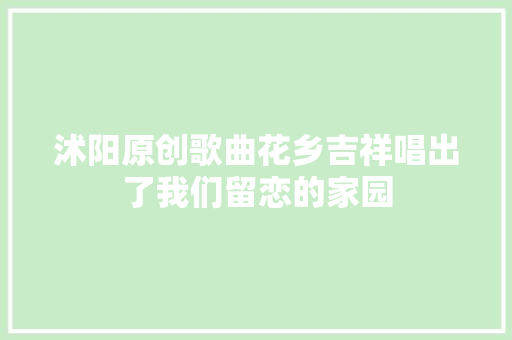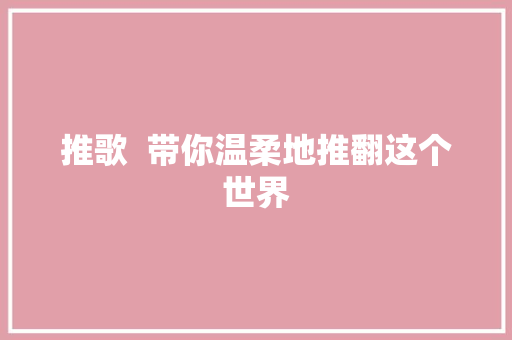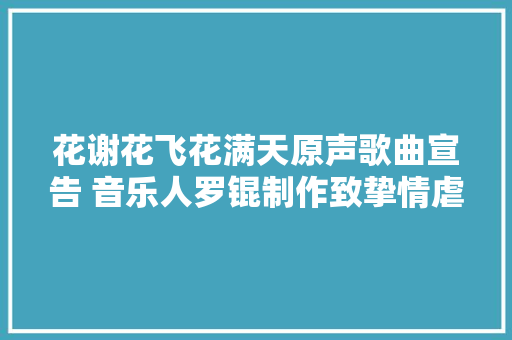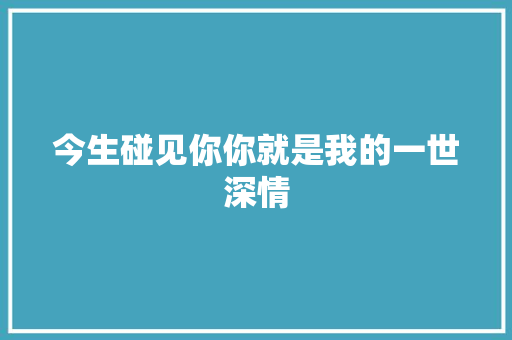一
十岁那年夏天,我的意识有些混乱,常常分不清上午和下午,昨天和本日。有时,我独自走进校园,呆呆地站在教室门口。我感知不到周围的安静和热闹,直到巡逻的值班老师见告我本日是周日,我才缓过神来。我的味觉也发生了奇怪的变革,尝不出咸味和甜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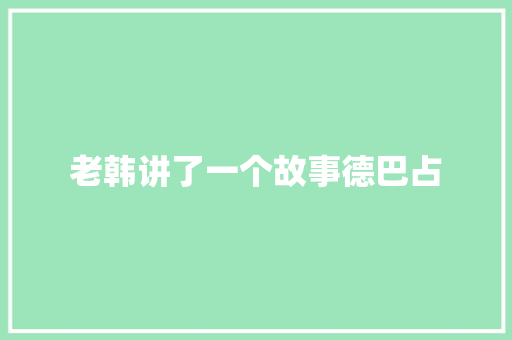
我只跟娜仁花说过这个情形。她比我小一岁,在村落北小学读三年级。我在村落西中央小学读四年级。她和她的额吉住在毕勒古泰山下的土房。那里是一片荒地,离村落庄有些远,周围没有其他房屋,土房显得格外突兀,像一只受伤掉队的孤雁落在山脚。
有一天下午,我领着小黑狗漫无目的地走在草地上,看到瘦弱的娜仁花戴着草帽背着背篓,穿着长衣长裤,正在用一把比她赶过一截的大铁锹挖着什么。我走过去讯问。她仰起微圆的脸朝我笑,又低头指着脚下一株叶片灰白的植物,说,我在挖防风呢,这东西晾干泡着喝,能减轻额吉的风湿痛。她的脸上布满了汗珠,神色有些发黑,两根马尾辫垂在肩头,大口喘着气,看起来有些无力,但是一双大眼睛闪亮闪亮的。她以前常常抱着作业本站在我家院门外,用这双大眼睛看我在不在家。
那天下午,我帮娜仁花挖出了好几根防风。后来我们去白杨林里的小溪边安歇。我跟她说了自己最近的奇怪情形。她猛地咳嗽了好一阵,然后抚着胸口从树荫走到阳光下,说,阿吉,你可能中暑了。我说,怎么会呢,中暑不应该是这个样子。她说,额吉说过,中暑严重的人会逐渐失落去意识。我说,可我的身体没有其他不适。小黑狗走到她身边吐着舌头。她彷佛不知道该说什么好,蹲下身抚摸了几下小黑狗的头,咬着嘴唇沉默了。我接着问她,你不热吗?她说,我最近特殊怕冷,有一点儿凉就受不了。风吹树叶,她脚下晃动着无数叶片的影子。她问我,阿吉,你坐过火车吗?我说,还没有坐过。她说,额吉说过,如果将来我能考上大学的话,就可以坐火车了。说这话时,她挺直身子望着天空,大眼睛里闪着光。
我接过背篓和铁锹,送娜仁花回家。走到她家院门外,她举起苗条的手臂跟我告别。阿吉,这是我们的秘密。我点了点头。
娜仁花说的秘密是指我和她之间特殊的互换。那些事情对别人来说不值一提,可在我们看来无比奇妙。我们在毕勒古泰山脚的白杨林里创造了一个泉眼,泉水在树下的草丛中变成了弯弯曲曲的溪流,两边飞舞着无数只蜻蜓和蝴蝶。后来这条溪流成了我们的秘密天下。我们还在土路上瞥见过刺猬。刺猬时而钻进草丛,时而又钻出来。我们担心它的安危,就把它赶进草丛,见许久没有出来,这才放心地回家。
这些事能成为我和娜仁花的秘密,紧张是害怕被那日苏知道。那日苏总背着大人陵暴同龄或更小的孩子。我曾经见过他的残酷。有一次,他和两个差错捉住了一只灰色旱獭。他们先是举起石头砸断了旱獭的后腿,再故意放开,等旱獭快要钻进洞口时,那日苏狞笑着挥舞铁锹砍了下去,旱獭从腰部被切成两截,临去世前还冒死扑向洞口,用半截身体徒劳地刨了几下土,就断气了。那日苏取出弹弓,对着旱獭的头部射击。鲜红的血浸湿了松软的黑土和绿草。空旷的草地上回荡着三个男孩的笑声。
这个场景让我做了好永劫光的噩梦。
而那年夏天,我身上的确发生了一些反常的状况。我莫名其妙地不再害怕河水。某个薄暮,我扎进村落东边的一条河里,不仅一下子学会了漂浮,还能在水里憋很永劫光的气。我能直视中午的太阳,能一口气跑很远的路,还能爬上十几米高的树。
那段韶光,我常常梦见自己长了鱼鳞、马蹄和鸟翅。我在教材上画了很多在天空中拍浮的鱼、长出翅膀的马和会说话的鸟。这些画已经完备挡住了铅印的笔墨。班主任问我,为什么画这些?我无法描述现实和梦境里的场景,直觉见告我,这些事不能说出来。
班主任拉着我的手,对额吉说,让孩子在家休养一段韶光吧。额吉抚摸着我的头问,你最近到底怎么了?我摇头不说话。额吉和班主任聊了很永劫光,我一句话也没有听进去,只是呆呆地看着天上的白云。班主任走后,额吉问我,可怜的孩子,你怎么哭了呢?我迷惑地说,我没有哭啊。当额吉抹去我脸上的泪水后,我才意识到自己真的堕泪了。
二
阿爸常常骑摩托车下乡,额吉忙着放牛,全体白天我除了上学,便是跟爷爷和小黑狗在一起。
有一天薄暮时分,额吉还没有回来,爷爷拄拐逐步走出院门,我赶紧跑过去,把爷爷扶到门口的大树下。爷爷摸摸我的头说,爷爷要去德巴占啦。我问,德巴占是什么地方,在哪儿?爷爷抬开始,出了一下子神,缓缓地说,那是一个极乐世界,在一个极迢遥的地方。我说,那只有坐火车才能去了。爷爷笑了,慈爱地说,善良的人都能去德巴占。我说,那日苏和他阿爸、阿吉一定去不了德巴占,那日苏总是残酷地杀害小动物,他阿爸也曾用皮鞭活活抽去世了一匹老马……听说,他阿吉也总是偷东西。爷爷望着远方叹了口气。那声音像微风一样柔柔,却重重地落在我心上。我想把那日苏陵暴我的事情偷偷见告爷爷,可是爷爷不知何时倚着大树睡着了。小黑狗不安地围着爷爷转来转去,嘴里发出呜呜的声音。
那天晚上,阿爸骑着摩托车回来,匆忙调集了好些亲戚。第二天凌晨,天没有亮,草尖上还挂着露珠儿,阿爸把牛车套在最老的一头黑牛身上,然后把爷爷躺放在车上。爷爷的身体被洁白的毡子包裹着。阿爸一手牵着我,一手牵着牛车,后面随着十几个人和小黑狗,向西方广阔的草原走去。我没有听到任何人的说话声和哭声,只听到牛蹄下的沙沙声、牛车的吱嘎声和小黑狗吐舌的声音。我们走了很长的路,后面的人们逐渐地停滞了脚步,末了只剩下阿爸、我和小黑狗。太阳升起来,远方涌现了群山。那些山在清晨的薄雾中不真实地晃动着。阿爸放开了黑牛。牛车连续有节奏地向群山走去……
爷爷走后,我回学校上学。只管我在各方面表现出正常的样子,但还是能感想熏染到从脑海深处时时涌动而来的一些莫名的思绪,但我隐蔽得很好,不轻易表现出来。我的脸上始终挂着沉默的表情。我面前的统统变得缓慢。有时燕子从教室的后窗飞进来,再从南窗飞出去,我能数清燕子扇动翅膀的次数。有时阳光照进教室,老师在黑板上写字,我能清晰地看到那些逐步掉落的粉尘。我的把稳力被这些细微的事物吸引着。
放学路上,那日苏带着两个差错不远不近地随着我。
我在家休养前的某个周末的薄暮,与小黑狗在河边玩耍的时候,那日苏三人领着大黄狗涌如今我面前。在这之前,他们常常将我逼到河边,让我举起书包站着不动。然后,他们拉开间隔,一人取出一个弹弓开始射击我头顶的书包。小石子儿噗噗地打在书包上,有几次打在我的手上。每次射击完,那日苏会恶狠狠地说,你敢见告别人,我就射你脑门。他凶恶的眼神吓到了我,我闭紧了嘴巴。
而那次,那日苏放开了狗绳。大黄狗竖起耳朵张着大嘴向我扑来,小黑狗绝不畏惧地迎了上去。两条狗撕咬在一起。这时,他们三人开始追我,我沿着河边冒死地跑。他们离我越来越近,情急之下,我闭上眼睛跳进了河里。奇怪的事情发生了。从不敢下水的我,竟然浮在水面,顺流游去。等我从浅流上岸时,河两边空空荡荡。
我沿着河边探求小黑狗。它倒在草地上,身受重伤,后腿差点儿被咬断,撕裂的皮毛下血肉模糊。我含着眼泪抱着小黑狗回家,它在我怀里一直地抖动。额吉往小黑狗的伤口处敷上白糖,又用白布缠住。那几天,小黑狗一贯趴在炕下的软垫上,就连哀号声都很微弱。我和额吉担心它挺不过去。但是没想到,一个星期后,它神奇地站了起来,而且缓缓地摇起了尾巴。它虽然暂时无法随着我跑,我心里却充满了欢悦。
几天后,我依照额吉的叮嘱,去给娜仁花家送牛奶和奶豆腐。那天刚下过雨,我和娜仁花想去看看泉水。可没想到我们在树林里碰着了那日苏三人。那日苏得意地说,这次你跑不掉了。他一时想不到用什么办法陵暴我,便拍打着一棵大树,用手指着树顶说,如果你敢爬到最上面的树梢上就放过你。
我和娜仁花想转身走开。但那日苏一把捉住娜仁花瘦弱的手臂,跟我说,你假如不爬上去,我就让她举书包。
一股恨意冲到了头顶,我真想给那日苏的脸上来一拳,可是脑筋里溘然浮现出被活活砍成两截的旱獭和鲜血淋漓的小黑狗。我手心里冒冷汗,捏紧的拳头松开了。我咬着牙开始爬树。我一根接一根地攀着树枝往上爬。他们边笑边拿弹弓对着我的脚射击。娜仁花发急地哭起来。当我勾住最高的那根树枝时,那日苏害怕了,从下面喊,行了行了,下来吧。我像没听见一样,我的身体变得非常轻盈,仿佛真的长出了一双翅膀。我一点儿也觉得不到恐怖。风一阵阵地吹过来,我拽着树枝左摇右摆。我看到了远处的风景,那里是爷爷消逝的群山。一韶光,我忘却了树下的统统。
过了许久,我听到娜仁花的喊声,阿吉,他们走了。我低下头,看到树下只有一个小黑点,是娜仁花。下来后,娜仁花问,阿吉,那么高的树顶,你不怕吗?我说,我刚才看到了特殊美的地方。娜仁花问,在哪里?我指着爷爷消逝的方向说,在很迢遥很迢遥的地方。娜仁花说,那我们将来坐火车去。我说,好,这是我们的秘密。娜仁花用力点了点头,她擦掉了眼泪,大大的眼睛里闪出热切的光。
那天傍晚,额吉抚摸着倒下的一头小牛犊堕泪。额吉说,挺不过去了。小牛犊一直地抽搐着,淌出的泪水就像树林里的溪流。额吉擦拭着小牛犊的眼泪嗟叹着说,可怜的孩子。额吉一边抚摸着小牛犊的后背,一边哼起温顺低沉的调子。
小牛犊在牛棚后面的菜园里停滞了抽搐。隔着一堵墙,传来母牛的叫声。我抱紧了小黑狗。
三
那日苏三人依旧随着我。
以前,一到周日,他们就让我带着写完的作业本到教室门口等待。他们很少按照说好的韶光来。我逐渐地分不清周日和周一,我的脑筋里充斥着奇特的景象。那些白云有时悬在空中安歇一阵,然后逐步飘走。我以为天地倒过来了。我常常躺在软绵绵的白云上,犹如躺在爷爷的背上,我举头能看到草原和牛群。我一度以为这不是,梦境,这是真实存在的现实天下。直到我耳边传来那日苏的声音,傻站着干啥,快进来。他把我拽进教室。他们将我的作业本传来传去,上面留下一片片黑乎乎的指印。
回到家,我用橡皮把那些黑指印擦净,抖掉一条条黑泥,心里才轻微舒畅一些。小黑狗的伤口已经完备愈合。它有了新的任务,随着额吉放牛。它没了以前的活泼,更像一个沉着的牧人。它的伤口上长出了更加结实的肌肉。
有一天,我指着远方的群山跟额吉说,那些山在动,像水浪,像云朵,忽远忽近,飘忽不定。额吉抱着我,哼唱了一段没有歌词的旋律,然后说,孩子,你说得没错,那些山真的在动。我问,额吉,你也看到了吗?额吉说,你出生前,在我肚子里时,我骑在立时,你一动,我就以为天下也在动。随着你终年夜,我也明白了,韶光也从来没有停过,世间万物都在动。小黑狗彷佛也听懂了额吉的话,摇了几下尾巴。我沉默了好一下子,问额吉,我将来也会像爷爷一样去德巴占吗?额吉没有回答,抱紧我连续哼唱温顺的旋律……
我的意识不仅混乱,而且模糊了。我只知道那日苏三人还在随着我,却回忆不出,我刚才是从学校放学出来的,还是从某个草地或某片树林里走出来的。我只知道自己正向着回家的方向走着,有时在梦里都走在回家的路上。
走着走着,我走过了秋日,走到了冬天。娜仁花已在中央小学读书。放学后,我们常结伴回家。我先送她,再回自己家。这件事被那日苏说得不堪入耳,只管班里除了他的两个跟班以外,没人理会这些。但我和娜仁花都有被侮辱的觉得。后来我们各走各的,只在周末偶尔在我家里一起看书学习,或去树林创造一些罕有的景物。那个泉眼还在冒着水,小溪流被落叶覆盖,逐渐结了冰霜。
娜仁花的咳嗽愈加频繁了,而且伴着沉重的粗气,每次咳嗽的时候全体人快要散架了似的,神色也越来越暗淡。额吉常常让我给娜仁花家送去食品和衣服。额吉长叹一声,说,真是一对苦命的母女啊!
我顺着额吉的目光望向毕勒古泰山脚,实在那里不远,一下子就能走过去,但有时又很远,怎么走也走不过去。
当第一个寒流袭来的时候,河水结冰了。某天下午放学后,那日苏三人领着大黄狗再次把我逼到了河边。那日苏大笑着说,你不是很会拍浮吗,现在倒是跳下去啊!
他抓起我的书包,使劲轮几圈再抛出去。冷风从冰冻的河面上呼啸而过,书包重重地摔落,传来文具盒碎裂的声音。他们三人的笑声更大了。
我踩着薄冰,一步步走过去,捡起书包,接着向对岸走去。那日苏溘然喊,别走,原地在冰上跳,不然我就放狗咬你。大黄狗狂吠着要解脱狗绳。河两岸的原野苍茫而空旷,天边几条长长的灰云下,夕阳正在西沉。我猛然向对岸跑去,脚下发出冰面不断裂开的声音。溘然,扑通一声,我掉进了河里。我用双手撑着冰面,身体浸泡在冷水里。那日苏三人慌张地跑了。我没有觉得到冷,只以为身体悬在半空,上不去下不来。我逐渐失落去意识,不远处涌现了夏季的群山,群山下晃动着爷爷赶着牛车的身影。我逐步闭上了眼睛。
我逐步走入一片广阔的草原。远处便是群山,我踩着优柔的青草向群山走去。我的速率越来越快。我长出一对翅膀飞了起来。快靠近山顶时,爷爷涌如今我面前。我惊喜地扑向爷爷,我们踩在优柔的白云上。而此刻,那些山长在了白云的上面。爷爷问我,我的孩子,你怎么来了?我说了那日苏的事,并问爷爷,坏人什么时候才会得到惩罚呢?爷爷说,成为坏人,便是对他最大的惩罚啊!
我一时没有明白,还想再问,爷爷却不见了。我惊骇不已,去追爷爷,却从云彩上直坠下去。这时,耳边传来额吉熟习的歌声。我猛地睁开眼睛。额吉正发急地守在阁下,神采干瘪,见我醒来,赶忙扶起我喂奶茶。我一张嘴,一股热乎乎的暖意流进体内。
额吉见告我,一个途经的牧民从冰窟窿里把我拽上来,托在马背上送回了家。我发了高烧,晕厥不醒,嘴里一直说着胡话。额吉找来村落里的大夫,给我输液,直到天快亮了,我这才醒过来。我丢失已久的味觉不知何时规复了,意识也清晰起来。
第二次寒流袭来时,阿爸回来了。阿爸检讨完我所有的作业本,说,儿子,你是我们村落里最精良的孩子。阿爸很少说这么温情的话,但他的话里透着一丝惆怅。他走出屋子,倚着院门,在寒风中吸烟。阿爸的背影像一座山。我还是不愿意跟阿爸和额吉说被陵暴的事。我内心深处隐蔽着一壁无法超出的墙壁。阿爸每次回来和每次出门前,第一件事便是抚摸着我的额头说,我的儿子越来越像男子汉了。额吉常常说,草原上的人畜都是缄默的。我从小心里装着沉默,千万个声音在我心里乱作一团,而后逐步归于沉着。
阿爸好永劫光没再出门,每天在家里跟额吉一起干活,打理着琐事。阿爸很少说话,隔一下子就去院门口,望着爷爷消逝的方向吸烟。
我给阿爸盛饭、倒水、擦鞋……干着力所能及的活儿。阿爸很少像额吉那样抱我,但我能感想熏染到阿爸对我的那种深奥深厚的爱。
表面越来越冷了。有一天下起了雪。阿爸跟我说,儿子,我们一起爬山吧。
北风凛冽,雪花打在脸上涩涩生疼。我随着阿爸来到了毕勒古泰山脚。阿爸默不作声地走在前面,我踩着他的脚印一步步往上爬。毕勒古泰山并不高,我们很快就爬到了山顶。周围没有别的山,这让视野变得极为开阔。山下的村落落像一幅幅油画,在风雪中有种刚硬的美感。娜仁花家的院子悄悄静的,一条苗条的炊烟缓缓向上飘散。
阿爸感慨,多美的村落落啊!
多美的原野啊!
阿爸多日惆怅的脸上终于露出一丝伸展的表情。他不再说话,目光望向村落落,也望向村落落以外的远方。我心底里涌起一股热流。某种说不出来的强烈的冲动和无声的惆怅同时撞击着我的心扉。
四
娜仁花和她的额吉到镇上看病去了。一贯到放寒假,她们也没有回来。走之前,娜仁花的额吉卖掉了家里仅剩的几只羊。她们家的院子里空空的。我白天写完作业就去白杨林里走动。有一天,我从树林里出来,沿着斑驳的小路往娜仁花家走去。这时,一大一小两个人影溘然从娜仁花家的院墙里翻了出来。我们劈面撞在一起。我吓了一跳,赶紧退却撤退一步。这时我才看清,这两个人是那日苏和他的阿吉,俩人各背着一个鼓鼓囊囊的编织袋,面色阴狠地看着我。他们环顾四周见没有别人,那日苏的阿吉便走过来在我屁股上用力踢了一脚说,前年便是你阿爸报警抓的我阿爸,我阿爸现在还没从里面出来呢,要不是本日有急事,我非得狠狠地教训你一顿,让你知道知道我的厉害。一旁的那日苏得意地跟我说,哼!
见告你,我阿吉的本事大着呢,别说是你阿爸了,连镇上的人都怕他,你阿爸不是苏木达吗?肯定贪了不少钱,我阿吉一封举报信,就让你阿爸吃不了兜着走!
那日苏的阿吉不耐烦地说,行了行了,别说了,我们快走。他一边走过去一边转头用凶恶的目光盯着我说,本日的事,你假如敢见告别人,转头我宰了你。
我吓得瘫坐在地上,看着他们的身影很快消逝在树林里。
几天后,院门口外来了两个穿制服的领导。阿爸约请他们进屋,但是他们没有进来。三个人就在院门口提及话来,两个领导时时时跟阿爸握手。没多久他们就走了。阿爸返回屋里后,开始擦拭院子里许久未骑的摩托车,脸上洋溢着久违的笑颜。额吉问,是不是有好了?阿爸点头说,诬陷我的那个家伙,前几天跟他弟弟一起偷东西被抓,把所有的事情都交代清楚了。
那天晚上,额吉动手做了烤羊肉,阿爸和额吉都喝了酒。他们的高兴里彷佛藏着深深的忧虑。阿爸说,哎,这么多年了,他们家人始终没有过敬畏之心,他们认为他们做的事天衣无缝,可他们忘了头顶还有神圣的永生天。额吉说,那日苏也是可怜的孩子,才多大就没了额吉,现在也被他阿爸和阿吉带坏了。
第二天,阿爸骑着摩托车往苏木报到去了。临走前,阿爸把我抱起来,在我耳边说,儿子,你已经终年夜了,是个小男子汉了。
我依旧保持着沉默,没有把那日苏对我做过的那些恐怖的事见告给家人。而知道我秘密的娜仁花却迟迟没有回来。快要过年了,村落里的孩子们穿着好看的衣服到处结伴玩耍。我终于没有忍住,走进牛棚问正在干活的额吉,娜仁花什么时候回来啊?额吉先是愣了一下,然后放下手里的干草,拉住我的手轻声问,孩子,还记得那头倒下的小牛犊吗?我用力点了点头。孩子,实在人和牛是一样的,牛有牛的命,人有人的命……
额吉连续用温顺的声音说着,伸脱手来抱紧了我。
我领着小黑狗,踩着冻硬的白雪,走进白杨林。那个泉眼已不再冒水,结了一层又一层的白冰,像是永一直歇的韶光。不远处是娜仁花家荒废的院子。落叶悄悄地躺在冻结的冰面上。我和娜仁花曾在这里憧憬过未来的空想,想象过城市和火车的样子。我在溪流边的雪地上画了一个长长的火车,车厢里写上了自己和娜仁花的名字。写着写着,我哭了起来,小黑狗焦急地围着我转。风吹过白杨树的叶子,吹过弯弯曲曲的冰面。阳光洒下来,冰面上闪动着无数个金灿灿的碎片。
我的眼泪彷佛变成了一条隐秘的河流,悄悄地流向那个我从未真正见过的,叫作德巴占的地方。(作者 阿尼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