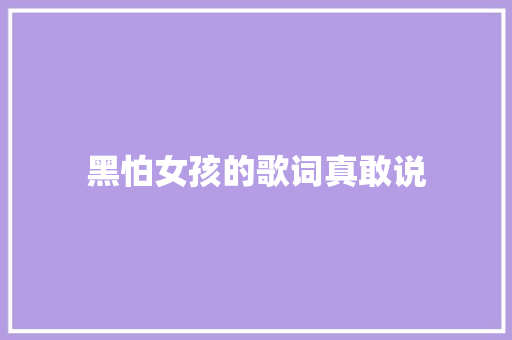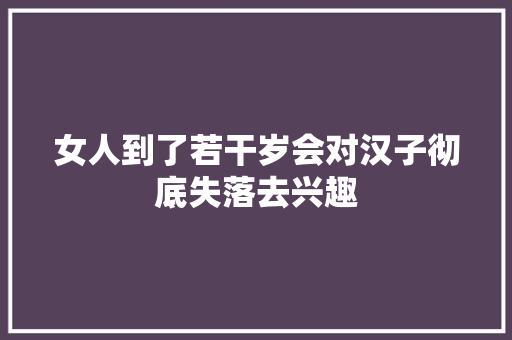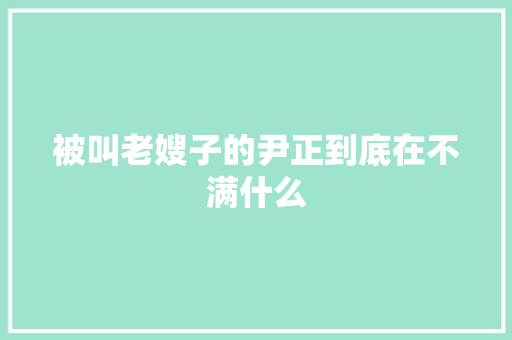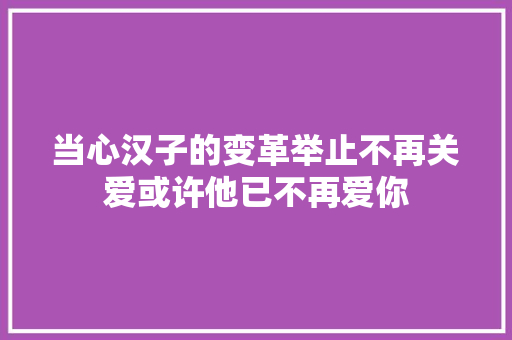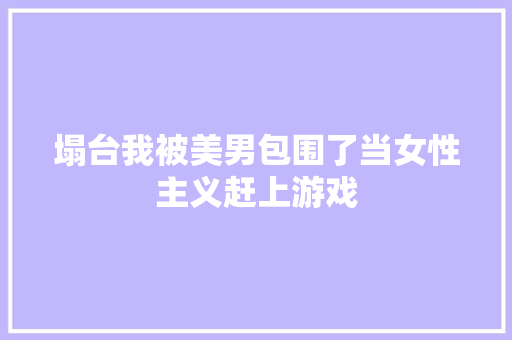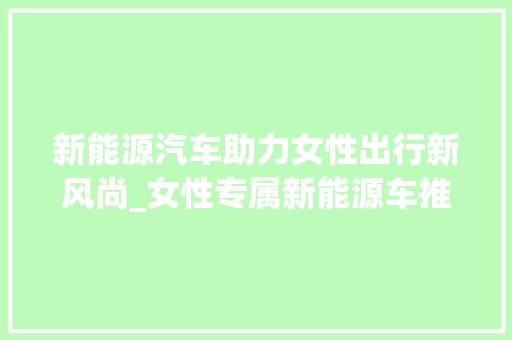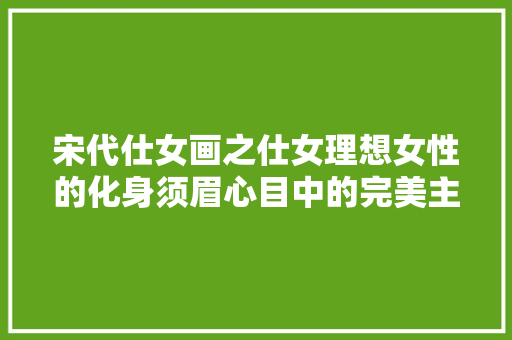娜拉,挪威剧作家易卜生代表作《玩偶之家》的女主角。她在剧中是一位中产阶级家庭主妇,曾为救丈夫之病私下借贷。多年之后此事意外被揭破,其丈夫却只顾自身名节,怒斥妻子不堪为人妻人母。娜拉于是发觉八年婚姻只是儿戏,丈夫不过视自己为没故意志的“玩偶”。失落望至极的她决心先“教诲自己”以“做一个人”,于是舍弃三个孩子与丈夫,关门离家。
“这出戏的目的,是在于让人们彻底理解问题所在,而不是要强制他们在这一分外案例中采纳这种分外的办理之道。”苏格兰剧评家威廉·阿彻(William Archer)曾直言该剧的意义。除了出走之外,该剧在欧洲上演时更多打动人心的是对爱情与婚姻实质的叩问,娜拉对家庭与自我的真切独白,以及环绕个体选择引发的诸多省思。而娜拉现身“五四”中国,险些经历了“乾坤大挪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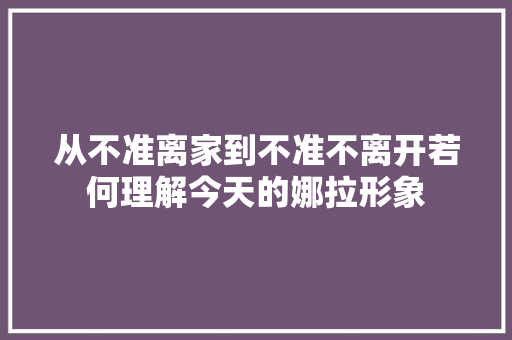
以胡适、鲁迅为代表的新文化男性知识分子对娜拉形象进行了“去性化”的改造。推戴个人主义、不惜与传统家庭为敌的“娜拉精神”曾让五四男青年难掩愉快,“且不论为何出走,走后如何,总之先走再说”。这些使得娜拉在中国的诠释权,从一开始就被男性攫取。以“人性”概括的男性本位叙事长期主导着娜拉形象,使得这一看似以女性之名的解放运动从一开始就并非专从女性自身需求出发,且个中影响延续至今。这些引起了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系副教授许慧琦的关注。
许慧琦,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历史学系博士,台湾政治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研究专长为近代跨国史、近代美国史、近代中外社会文化史、妇女史、性别与性欲史、民国史。代表作有 Emma Goldman, Mother Earth, and the Anarchist Awakening, 以及《故都新貌:迁都后到抗战前的北平城市消费(1928-1937)》《“娜拉”在中国:新女性形象的塑造及其演化,1900-1930年代》。
许慧琦曾以此为题作博士论文,并于2003年在台湾出版《“娜拉”在中国》一书。时隔20年,该书的简体中文版近日与大陆读者见面。通过20余年的不雅观察,许慧琦加倍确信,自20世纪至今,中国妇女问题的症结并非在于哪种社会制度,而是男性本位的思维。也便是说,近代中国新女性的最大难题,其实在于走着一条男性供应与辅导的路,同时还须面对男性本位的舆论各类不公正的苛责。这在娜拉形象的历史衍变中,尤为突出。
我们通过邮件采访了许慧琦,从《玩偶之家》进入中国聊起,一贯谈到这些年女性内部的“新旧”之争,以及背后宰制至今的男性本位叙事逻辑。我们创造百年前,被国人跳过的“娜拉之问”兜兜转转还是回来了。虽被推迟,但这次重面无疑意义重大。从各个层面而言,这都是这一代女性考试测验摆脱大叙事框架的关键一步。
下文为新京报与许慧琦的对话。
“乾坤大挪移”:
我们熟习的娜拉,并非原来的她?
新京报:如今在国人的印象中,提起“娜拉”,读者可能不会首先想到易卜生,却有可能想到鲁迅。在娜拉进入中国的过程中,鲁迅、胡适等当时的这些“新青年”,他们是如何改造“娜拉”这一形象的?
许慧琦:是,当代人这样的印象,清楚反响鲁迅与胡适这些引领新文化风骚的新男性,在引介“娜拉”入华的主要角色。我个人以为,在“娜拉”成为中国新女性形象的历史发展上,胡适扮演紧张的形塑者,而鲁迅则是此一形象转型的启迪者。或者说,虽然鲁迅在清末就先容过易卜生著作,但胡适才是将“娜拉”引入中国的不二媒人。
1918年,新文化运动最具影响力的刊物《新青年》,发行由胡适主导的“易卜生专号”。个中,胡适关键地以“娜拉”为主角,陪衬出一个具现易卜生主义精髓的新人理型。这个理型,反抗家庭专制、张扬个人主义,且抵拒相沿守旧。在胡适笔下,娜拉那句“救出自己”、“做一个人”的名句,响彻新文化云霄,让新青年男女创造希望。
《“娜拉”在中国》,许慧琦 著,空想国|上海三联书店,2024年7月。
当年,我进行娜拉研究时,一开始并未体会到胡适对娜拉实施着我后来所谓“去性化”的辞吐工程。但当我采取性别视角进行史料剖析与诠释时,创造他的论述策略,可谓乾坤大挪移,将娜拉打造为新青年男女的典范。这样的操作,既使胡适这样的新文化师长,成为女性权柄的提倡与辅导者,也使下一代的五四青年学子,成为相邀女同学一起“救自己”的同路人。但如此一来,中国女子不仅未能真正掌有主导娜拉走向的主体性,也仍屈居于受男人辅导与召唤的被动地位。换言之,在胡适率领下,娜拉初入中国匆匆成的“两性”解放,因此取代与溶解“女性”解放的独特性为代价的。
至于鲁迅对娜拉形象的贡献,紧张是他1923年,在北京女高师那场“娜拉走后若何”的演讲(来年便以笔墨出版),以及1925年的小说《伤逝》。这两份文本的意义,在于为几年前由胡适领衔掀起的青年男女出走、抗婚风潮,浇一盆现实冷水。鲁迅关于娜拉的思考与作品,写于进步思想界群趋左倾、阶级意识抽芽,且时局益发混乱的五四后。
《伤逝》电影剧照。
我认为,鲁迅对“娜拉”的理解与指涉,也不仅只于中国女子,而是广含众新青年男女。只不过,当碰着鲁迅一针见血点出的经济自主问题时,女子总比男子面临更为艰巨的寻衅。因此,只管《伤逝》中彷徨的绝对不但子君,也包括勉励她出走与之同居的爱人涓生,但只有因被涓生抛弃,黯然返回父家的子君,才会面临断港绝潢的绝境。
也是在这样的现实反问中,鲁迅提醒青年读者,除了汇聚出走的勇气与动力之外,更需培养走后得以自主的能力与坚持。这样的提点,涌现于中国在国共第一次互助期间;那是个从妇女运动到运动妇女的妇运转型期。鲁迅颇有先见之明,某种程度上暗示着个人娜拉的出走,迟早得回家或堕落;但若是由政党领导的集体出走,则可能柳暗花明。但如此一来,娜拉的出走命运,又再度与中国的国族命运,产生了千丝万缕的纠缠,无法完备节制在女子手中。
新京报:当娜拉被塑造为“新女性”的象征后,彼时不少女性纷纭以抗婚宣誓效仿娜拉。你在书中指出,虽然都是“出走”,但这背后却悄然从原版娜拉走出“夫家”变成中国娜拉走出“父家”。为什么在回顾这段历史时,我们须要把稳到这种转变?从走出“夫家”到走出“父家”,这背后的抗争焦点有哪些不同?
许慧琦:我确实以为,当时中国女子走出“父家”,与原版娜拉走出“夫家”,有主要的实质差异。以娜拉原版而言,当年娜拉与郝尔茂,应是自由恋爱而结婚。这样的婚姻结合,是无数深受包办婚姻之苦的五四青年男女,企求而难得的。娜拉与其夫,纵然经历自由恋爱,也不见得理解何谓爱情。他们只是努力扮演当时主流社会认定的夫妻角色,生儿育女过生活。易卜生透过娜拉的“觉醒”,紧张希望惊醒维多利亚时期的中产阶级,正视其家庭文化、婚姻不雅观与社会习俗的各种虚伪陈规,并期许男女都能有冲破现状,探索真正自我的勇气。
《玩偶之家》电影剧照。
中国在五四季期,效法娜拉自救精神的青年男女,必须先逃出自己的原生家庭,方有可能进入娜拉经由八年才觉醒的婚姻之门。这已经使中国的娜拉出走,往退却撤退了一步,无法与走出婚姻的西方娜拉,相提并论。更别说,民国期间的社会舆论,除极少数例外,对离婚妇女普遍极不友善。
归结来说,中国娜拉走出“父家”,是一种男女共同反家庭专制,争取个人自由的举动。也正因走出父家,是民国青年男女共同的抗婚举动,才会引发如此巨大的风潮。若只有青年女子单独倡议而行,“走出父家”之举,想必将轻易为礼教势力仍大的社会舆论摧折。因此,五四季青年男女的“集体出走”,是一种去性化的反礼教表现。走出父家门后的青年男女,纵然谈恋爱时,依旧多数坚持着男主女从,或男强女弱的社会性别生理。相较之下,原版娜拉走出夫家,则是女性独自必须承担后果的行为。这个中意涵,差异很大。
新京报:基于此,你在书中反复强调,娜拉在中国的诠释权,从一开始就被知识男性攫取,受到男性本位的当代性叙事的潜在影响。新文化男性多将妇女问题视为人类问题或文化问题,乃至此种论调的影响力持续至今。可否以娜拉的出走为例展开谈谈,基于推崇个人主义的“出走”,和从“女性权柄”出发的“出走”究竟有什么不一样?或者说,把男性的出走和女性的出走混为一谈,会有什么后果?
许慧琦:你所提这个问题,是我在《“娜拉”在中国》的简体中文版,才有的论述。两年前,黄旭东编辑联结我,表示希望出版这本书时,我轻微在序言结论处更新一下,以让这本20年前出版的书,不显太过时。但我很珍惜这个出版机会,加上自己已完成的新书主题,与《“娜拉”在中国》颇有呼应之处,以是我把握此机会,修正了很多旧版的内容。个中,关于男性本位的大叙事这部分,便是简中版最主要的新论点。
我在《“娜拉”在中国》的繁体中文旧版,表示此书拟“从性别政治的权力运作切入,来探究两性对‘娜拉’的诠释与挪用(appropriate),则可进一步理解新女性形象在近代中国被授予的意义,以及新女性论述的实质。”但当时,我仍以生理性别,来作为检视性别差异的区隔标准。也便是说,我所进行的性别剖析(gender analysis),仍未摆脱以男女的生理性征差异为根本的框架。
过去多年来,我的近代中外交流史研究,聚焦的多是男精英;由于他们确实是民国期间,尤其1930年代前,中国两性、婚恋与性道德论述的主导者。我创造,不少妇女或性别史学者,跟我一样,常将进步男性视为研究工具,并进行带有女性主义意识的剖析评论乃至批驳。但我逐渐创造,这样的研究取径,随意马虎让人坚持男女有别的误解,乃至强化人们认为男人压迫女人的不快意象。
事实上,历史上所有传统的父权系统编制、或近当代的男性中央社会,都有无数女性(不论积极热切或被动受迫)与之共谋。而这种在推动性别平权的道路上,依旧坚持男性上风的代价不雅观,便是我所谓的男性本位当代性叙事。不少欧美妇女与性别史家,回顾19、20世纪之交的性别文化转型时,陆续指出当时看似引领进步风潮的男性性学家,多以“性解放”(sexual liberation)来取代“女性解放”(women’s emancipation)。此二者之间的差异,正与“推崇个人主义的‘出走’”与“从‘女性权柄’出发的‘出走’”之差异,有异曲同工之妙。
当我们把女性的出走与男性的出走,混为一谈时,人们看到的只有以男性为人类原型的人的欲望与需求。就像胡适,他透过阐述娜拉特质所发扬的个人主义精神,从未顾及女性独特的生理条件、相对的性别劣势与经济弱势。此种论述的发展后果,便是延续着以男人为人类原型、以男性特质为优胜性别气质的既有男性本位代价不雅观。女人只能努力在个中,追求与男人一样成为“社会人”的代价。但与此同时,她们却难以摆脱男人可轻易卸除的“家庭人”重责。
娜拉的回响:
中西社会对《玩偶之家》的反应差异
新京报:接下来,我们回到这部戏剧当初引进海内时的情状。
《玩偶之家》在欧洲上演时引发的谈论,实在是有别于中国的。比如关于娜拉“出门”前的生理活动、是否要“放弃母职”的决议、以及当时中产的道德双标等,这些在20世纪娜拉进入中国时,险些都被过滤了。可否展开谈谈,彼时两地不雅观众反馈上还有哪些让你印象深刻的差异?这种差异此后又如何影响了娜拉在中国的形象走向?
许慧琦:当时,我从外国学者研究中,创造《玩偶之家》在欧洲上演时,引发各种热烈争议。而根据我那时搜集节制的中国史料,可创造中西社会环绕该剧以及娜拉表现而生的谈论,差异颇大。这充分解释文化与国情差异,如何可能影响并旁边大众看待婚姻、两性关系及性别角色。
在我看来,中西社会对《玩偶之家》的反应差异,很大程度取决于大众如何打仗这部作品。欧美社会(多数属中上阶层)的群众,紧张是自己进入剧院不雅观剧。然而,中国社会对该剧的接管,却多数是在进步男精英的过滤下进行的。胡适、鲁迅等新文化健将,从他们理解与诠释的娜拉言行表现,来授予这部剧他们认为对中国人有启示的意涵。
随后,中国社会――个中不少是中学或大学学生业余――的《玩偶之家》话剧演出,才陆续涌现。简言之,我们可以说欧美大众,多数因此不雅观众的身分,直接打仗或接管娜拉;中国大众,则较多以读者的身分,间接打仗或理解娜拉。这样的关键差异,导致中国社会对《玩偶之家》及娜拉表现的理解,基本上被新文化男精英主导/绑架。他们从该剧汲取他们以为主要的元素,并透过进步报刊传播开来。
章子怡监制话剧《玩偶之家2:娜拉归来》现场。
当时欧美社会不雅观众环绕娜拉所谈论的问题,既多元且态度差异很大。这便是为何我书中提及,当时乃至有人家举办宴会时,必须挂上“请勿谈论《娜拉》”的牌子,以避免客人见地相左,影响和谐气氛。不难想象,欧洲中产阶级,置身于19世纪男女有别且男外女内的性别文化中,对有三个小孩的娜拉走出家门的决定,感到震荡。
由于,若从当时中产阶级的空想男性及其特质来看,郝尔茂的表现并没有太“超过”。他既是一家之主,便须守卫自己的名声与道德。反之,身为家庭主妇的娜拉,则被当时欧洲社会天经地义认定应做家庭天使、丈夫后盾;为家庭捐躯奉献,是她的天职。以是,纵然某些不雅观众能理解她想做自己而离家的心态,却不尽然能接管这样断交的选择。
反之,《玩偶之家》与“娜拉”进入中国的契机,则是新文化男性想要唤醒中国人而生的。这样的差异,关键性决定了中国大众对《玩偶之家》的单一理解(亦即险些全将焦点集中于娜拉的出走),及娜拉在日后中国的形象走向。
《玩偶之家》电影海报。
新京报:的确,回顾二十世纪上半叶,我们实在会把稳到,与娜拉同期间进入中国的还有很多女性形象。比如英法百年战役的主要人物圣女贞德、小仲马笔下的“茶花女”等等,这些女性形象当时也显示出了各自的“革命性”。为什么终极在当时引发轰动的是“娜拉”?我们是否可以理解为,与其说是“娜拉”进入了当时的中国,不如说是当时的国人主动走向了“娜拉”?
许慧琦:没错。不少中外学者,已戳穿自清末以来,许多西方(不论真人或作品主角等)精彩女性的形象被引入中国。圣女贞德的大胆与爱国,相称相符清末革命气势高扬的机遇。茶花女,则如我书中所言,被晚清时人推崇为具有捐躯美德的女性形象。但此二者,或其他曾在清末自强救亡氛围中被译介的外国女性形象,到了以启蒙为主轴的五四,便不尽然合时宜。如我在上个问题所述,当时的中国人,实在绝大多数是间接认识娜拉的。依此,我会说,是当时曾留学外洋的新文化男精英,主动创造、并号召国人走向娜拉。
新京报:你也在书中谈到,这和清末民初社会层面女性意识的抽芽有关。在你看来,这个期间海内觉醒的女性意识和同期间欧洲盛行的女性意识有何异同?如今回看,这种抽芽本身又蕴含着若何的机遇与陷阱?
许慧琦:浩瀚关于近代中国妇女与性别史的中外精良学术著作,已经交相凸显清末民初女性意识的抽芽,或清末女性主义思想的涌现,与国家的危急存亡局势紧密干系。这确实反响出近代欧美与中国发展女性主体意识的差异。
首先,欧美鼓吹女性意识的主导者,是中上阶层的白人知识女性;随后,才逐渐扩及于不同种族、阶级的女性。中国则在清末先由传教士与维新派男性为先驱。诚然,秋瑾、陈撷芬与何喷鼻香凝等留日女子,透过创刊、组织与办学堂等办法,积极推动女性权柄。但真正让其成为清末进步阵营逐渐正视的课题之人,仍首推梁启超等有广大思想影响力的知识男性。20世纪初的英美社会,接管高档教诲,独立自主、有专业技能的新女性,开始在社会霸占一席之地。同期间的中国,评论辩论女性权柄者,紧张在争取女子有为国家社会奉献的本事与机会,而非如西方女性主义者争的是自身权利与自由。
20世纪以降的中国女性主义发展,实无法回避既受国族论述刺激而生、却也受其框架限定的历史事实。这也正是你问题所点出的“机遇”与“陷阱”。这个让中国男性乃至不少女性受益的女性主义运动发展模式,却也是至今女性和女性主义仍得面临的困境。
“娜拉之问”:
百年前被跳过的问题还是回来了
新京报:时至今日,娜拉的形象依然深入民气,但风向却有些变革。你在绪论中也把稳到,如果说“一百年前,是不准娜拉离家;一百年后,(则是)不准(娜拉)不离开”。
这种风向的变革在近几年间催生出的,是海内新旧女性群体之间的分解与女性选择的日益窄化。如今回顾,我们大概正惊异地创造,百年前曾经被跳过的那些问题——“娜拉为何要出走”“娜拉有必要出走吗”,在本日险些不得不重新面对。为什么这些问题在本日会被重新提及?它们在妇女运动史上处于若何的位置?
许慧琦:当代人,似随意马虎对各种进步思潮或运动,抱持某种直线提高的历史印象;亦即都是随着韶光愈加进步。当然,很多人也都晓得,事实并非如此。近百年中国的妇运史,或谓女性发展史,是段持续受各种外界(男子主导)的动力驱策与拘束限定的抵牾发展过程。
百年前,中国人没有机会问“娜拉为何、或是否有必要出走”。百年间,中国女性,以及中国男性,究竟经历了哪些发展?
《让娜·迪尔曼》电影剧照。
1950年代后,台海两岸的妇女发展虽不尽相同,却先后经历了整体主导性的妇女事情/运动,以及再度受欧美女性主义思潮启示而创生新一波新女性(主义)或多元性别运动的阶段。乍见之下,当代知识女性,比百年前显然更具社会竞争力。她们拥有传统女性没有的教诲程度、专业技能、经济能力、国际眼界、法律资源、社会网络,以及生养/避孕科技等。但当代女性,有事情,不代表能完备经济自主;可以独身,不代表没有雷霆万钧的亲友社会压力。就算找到相爱结婚的伴侣,也不代表她的家庭重责,能被公正分担。
生产虽有育婴假与其他津贴,却不代表她的升迁与职涯不受影响。卡在外家、夫家、丈夫与儿女的各种需求之间,常常让已婚职业女性疲于奔命。这些扮演社会、职场与家庭多种角色的怠倦费力,或许非百年前年夜半是家庭主妇的中国女子可以想象。女性面对这些新发展、新变革与新寻衅,是否须要以出走来表现?这答案,或许见仁见智。不同缘故原由,导致不同女性选择离开婚姻,“做自己”或“教诲自己”。
至于,为何中国人绕了一大圈,才面对当时原版娜拉出走的干系问题,或许该当说是中国女性某种摆脱大叙事框架的进展吧!
中国女性被给予的,是做像男人一样的“人”的机会。浩瀚史学、人类学与社会学等研究,早已显示这样的解放路径,对“女”“性”(包括女人的生理功能与社会性别特质)的不公正与摧折。改革开放后,骤见之下,彷佛女性得以解脱当铁姑娘的去性身分,但阴魂不散的传统两性代价不雅观,却跬步不离。
我想,娜拉想先教诲自己、做一个人的决心,在当代中国确实仍不过时。或许,我们可把“娜拉之问”,视为中国女性乐意打破各种被给予的进步与权利之网,正视自己所欲所求,以做自己婚姻与人生“主人”的灵感。
新京报:这些年,女性主义内部的热点话题之一是女性如何面对各自身上那些“既新又旧”的繁芜性。你在书中提到,实在这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也同样存在,社会层面民众自我解放与改变的速率不一,制造了“新思想旧道德的女性”,也使得很多旧式妇女成为捐躯品。这也间接导致“新女性和旧女性都成了男人的俘虏”。可否展开谈谈这个不雅观察,以及你是如何看待女性内部所谓的“新与旧”之分的?
许慧琦:我以为最令人厌烦的,是那些被视为女性身上“既新又旧”的特质,很大程度来自于男性本位的眼力与标准!
社会怎么不拿类似的标准,来看待男性呢?当年,五四一堆嘴里唱着自由恋爱的新文化健将,都是允从父母包办婚姻、乃至娶妾享多人之福的男人。“言行不一”,险些成了近代提倡女性主义或妇女解放的知识男性共同特色。
在我刚完成的新书书稿中,我比较多一点阐述这种将女性群体区隔新旧的策略,正是男性本位论者的厌女意识展现。学者已经指出,厌女者(不分男女)常常喜用分而治之的伎俩,夸奖拉拢其肯定的女性(群体),同时批驳惩戒其不认同的女性(群体)。
的确,民国时的新旧女子之分,绝对不但面对婚姻的态度,还广含教诲程度、思想视野、专业技能及身体本色(例如不裹足不束胸)等方面。但当时所谓旧式女子,最被新文化人诟病的重点之一,即去世守贞操不雅观。1920年代以降,不少支持女性主义的男知识人,批评许多女性具有新思想旧道德。谁人中,包含他们抱怨新女性分明接管恋爱自由思想,却在遇人不淑时悲痛寻去世,何必呢!
会这么说的男人,分明缺少同理心,无法共情女子在践行“恋爱自由”的性爱结合过程中,可能遭遇的严重生理冲击与道德反噬。然而,实则女性不论新旧,都很难摆脱以男性本位的代价不雅观来核阅自己的内化生理。
《让娜·迪尔曼》电影剧照。
新京报:很永劫光里,女性主义抗争的是一种“男性叙事”,但深层次的“男性本位叙事”却鲜少被把稳到。为什么后者会更难被创造?以及你在书中也指出——综不雅观20世纪至今的中国社会的发展,解释妇女问题的症结,并非成本主义或社会主义,而是男性本位的系统编制与思维。为什么这么说?
许慧琦:我很高兴你提出这个问题。男性本位叙事与男性叙事,有很关键的主要差异。最大略的界说,男性叙事即男人的言说与论述;男性本位叙事,则因此男性履历、视角和代价不雅观为中央的叙事办法。男性本位观点中张扬的男“性”,不但指涉生理男,还包括被提高为具有代表人类普世代价的男性性别特质,例如理性、自主、力量、任务感及冒险精神。
这意味着,男性本位叙事,除了男人的辞吐之外,也常常包括认同男性特质的女人辞吐。若女性主义只知抗争某些男性叙事肯定男性、抑低女性的显性厌女情结,却忽略辨识出男性本位叙事一边表达支持女性主义、一边批评其不认同的女性表现所流露的隐性厌女意识,那么男女不平等的现状,只会被延续。
吊诡的是,近代中国诸多女性主义论述,很多属于男性本位叙事。不论是清末女革命志士,或投身中共革命大业的女同道,甚或以摩登女子表现为耻的职业女性,常常表达出男性本位的代价不雅观,以此期许哀求女界同胞,自主自强。男性本位叙事,并不反对男女平权;由于男女平权,只是许可女人拥有男人已有的权利。男女平权,并不(尽然)表示男人须要转让他既有的权力与上风;也不表示女人向来被认定的(生理条件与社会性别特质)弱点与(家务劳动、照护老幼等)天职,便就此消逝;更不虞味着女人就此拥有想怎么做自己、就怎么做自己的自由。或许正是在百年来中国男性本位叙事从未遭寻衅的吊诡发展下,如今娜拉当年想救出自己、做一个人的呼声,依然能让浩瀚女人感叹地发出共鸣。
我想,近代历史发展至今,大致证明了,不论哪种社会,若未能动摇男性本位代价不雅观,则各种哀求法律保障的女性权柄会困难重重。由于,国家宪法、政府立法、系统编制改革,对保障女性权柄虽主要,但在男性掌权、男强女弱代价不雅观主导下的社会机制,落实起来仍可涌现各种不利女性的偏差。更遑论,让女性争取有机会做男性做的事情,虽使她们有更多的发展空间,却可能反向强化社会认同男性特质的代价不雅观。
此外,我在进行《“娜拉”在中国》研究的过程中,体会到妇女解放运动太常聚焦女性在公领域的权利与表现,却忽略家庭这个落实男女平等时,最应改变的核心。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比较重视公领域,而相对忽略私领域的运动重点,多少重复了男性本位不雅观重公轻私(衍伸为重男轻女)的思维。家庭/家务这个从古至今都被视为女性紧张的活动空间、性别角色扮演与性别特质表现的场域,其代价并未因女性争取在男人专擅的公领域活动后,就被提升。家庭至今,仍被多数人认定为女性再怎么三头六臂,仍须要兼顾之天职。当代女性在公私领域的双重包袱(double shift),同时存在于成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国家。
曾有长辈见告我,不少大陆家庭,实在都是女人当家;太太不烧菜乃至不用顾小孩,这样的情形或许不少,却无法粉饰中国或其他社会,仍普遍存在家务劳动、教诲内容、职涯升迁与角色扮演(冲突与否)各方面都利男的趋势。我认为,正是那种肯定男性特质、重公轻私、认定社会高于家庭的男性本位代价不雅观,羁绊了女性。
重回《玩偶之家》:
在解放女性的同时,也解放男性
新京报:下面回到这本书。《“娜拉”在中国》初版于2003年,最初基于的是你在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系研究所求学期间的博士论文。你最初是如何关注到这个人物形象的?或者说,关于“娜拉”的各类叙事中,最初引起你研究兴趣的那个原点是什么?
许慧琦:是的,这本书的初版,是我2001年毕业于政大历史所的博士论文,题目都没变。我硕士时的论文主题,是十八世纪末的西方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当我读博班后,开始思考研究主题及领域时,自觉或许近代中外性别思想互换史,会比纯泰西史,更适宜留在台湾、而非赴欧美读书的自己来研讨发展。
其后,我在某本关于近代中国史的书中,读到作者提及“娜拉”,及其作为新女性形象,对五四新文化人的影响。那样的简短阐述,勾起我的兴趣。我认为被当时人塑造为新女性形象的“娜拉”,是个开展近代中外性别史研究的好题目。自此,我就开始关注并挖掘史料,以及古人对娜拉或近代中国新女性的研究。
若回忆当时引发我研究娜拉的原点,我可能会说自己很想理解,这个西方剧作的女主角,究竟为何得以在民国期间的中国社会,引发如此多谈论且发挥影响。当年,我的研究重点,更多是在爬梳与剖析娜拉在五四之后的民国社会,被建构为新女性形象的发展演化过程。大约在起初,我就把稳到当时中国人对娜拉“出走”的高度关注。我也逐渐理解,早时西方社会对娜拉的谈论重点,与中国读者有主要差异。这个差异,让我以为是切入探索近代中外性别思想互换的好视角。
新京报:我很好奇,你是否在戏院中完全看过这整部剧?当时是在哪里看的,又有哪些私人的感想熏染?
许慧琦:实在,我是在早已完成博论,且将之出版成专书之后,才于2006年在台北不雅观赏一位德国导演改编的“娜拉”。该剧全由德国演员以德语演出,且将结局从原来娜拉走出家门,改为她枪杀丈夫郝尔茂。当时看完该剧后,我曾在日记中写下,表示还是比较喜好易卜生原作的结局。
日后我教书时,曾选择放映Claire Bloom与Anthony Hopkins主演的1973年英国“玩偶之家”电影,给学生不雅观赏谈论。我个人挺喜好这个相称忠于原作的电影版本,或许由于我确实比较偏好开放式结局。觉得上,那给男女主角双方,都有改变自己的机会。
《玩偶之家》电影海报。
新京报:对付本日的读者而言,你以为“娜拉”这个形象值得思考的还有哪些?
许慧琦:一如百年前胡适等男精英授予娜拉的去性化特质,我认为今日读者,不论男女,仍能从娜拉身上得到跨性别实质的启示。当代男性本位不雅观连续当道的社会中,最大的抵牾,大概是许多男人眼见女人被赋权,而产生自身权势被削弱的精神阉割感。
女人愈独立,愈显得男人不主要,也就剥夺了男人可在婚姻与家庭中享受的家主优胜感。男人为数渐增、感想熏染渐深的相对(于过去男人享有上风的)虚弱感,反向引发了强烈的厌女情结。实则,男人的历史包袱与压力,或许是不少女性主义者忽略的。我想,若女人也可同理“当男人真不随意马虎”,或许女性主义的两性平等、适性发展主见,会更受到男人支持。
我以为女性主义的真谛,不但在争取男女形式上的平等,更应重新设定(reset)男/女特质与两性关系。让男人也有重新适性做人的机会,不须总是背负得活得像个男人的重担。我常以为,正是那种(在家中常常是父亲加诸儿子的)“必须当个阳刚男人”的特质期许,把浩瀚男人压得喘不过气来,转身痛恨女人。
从女性解放实在牵扯男性解放的向度来说,《玩偶之家》或许不但希望为娜拉那样的妇女,争取觉醒自主的机会,也故意解放郝尔茂那样的男子,卸下维多利亚中产阶级丈夫的刻板重担,重思自己想做若何的人。
从这种两性互助共情的视角,来检视娜拉形象,可说这是个仍足以启示男女都“走出舒适圈”的思想意象。若无郝尔茂因故显露“本色”,扮演了八年贤妻良母的娜拉,无从被刺激而决心教诲自己,真正做一个人。同理,若无娜拉的“觉醒”,郝尔茂更无从被奉告自己的婚姻,乃至于自己,出了多么大的问题。易卜生没把两人的结局写去世,或许正意在藉娜拉之举,让她与郝尔茂都有重新做人的机会。
《玩偶之家》电影剧照。
新京报:末了,你曾旗帜光鲜地提出:“光要女性出走还不足,还得让男性回家。”为什么说后者同样也是必要的?
许慧琦:这个判断涌现于我新版的结论。这句话,确实是我过去二十多年研究与思考的某些心得归纳。犹如上个问题的回答,我深觉家庭是个女性主义者须要花更多力气来对付的关键,以便打破男性本位“女性主义论”的盲点。若不直捣黄龙,松解女性被加诸的家庭角色与家务任务,且翻转男女代价不雅观的性别阶序,则怎么哀求女性在公领域发展,都属刻舟求剑。
再从性别出发,省思“出走”的意涵:可以说,男性都被许可对家庭发展出“长期出走”的心态。他们被教诲期许着赢利养家,并成为一家之主;他们也被期许并许可将生活心思,紧张放在事情与公领域活动上。这不尽然是每个男人想要的生活。有些男人想花更多韶光陪小孩,跟妻子一起在家里分担家务;但他的上司与同事都彷佛天经地义认为,他应以事情为重。实在,很多男人也常常无法做自己。娜拉那股“我要看看究竟是我错了,还是天下错了”的志气,确实可以启示鼓舞当代男女,也年夜胆反抗社会对付“男人应这样(表现),女人应那样(表现)”的刻板性别不雅观。
《娜拉在中国》缕述了各种哀求中国女子出走的男性本位大叙事。个中,我们确实见证浩瀚女性走进社会后的各种优胜表现。但那些从认同男性本位代价不雅观出发,主见出走的女性,若非家中有佣仆帮忙家务照料儿女,便是以(仍是男性本位的)大我为重,轻视家庭(及其隐含的女性)代价,哀求女性必须进入社会贡献。
综而言之,女性光是走出家庭,办理不了男女不平等的问题。我主见所谓“让男性回家”,乃广义包括让男人把心思放回家庭(翻转重社会、轻家庭的公私领域利害势),正视(夫、父与半子等)家庭角色,扛起身庭事情,培养家庭美德,与经营家庭关系。
若不如此,当代女性就算连续打听“为何与是否要出走”,仍无法真正办理问题。
采写/申璐
编辑/走走
校正/薛京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