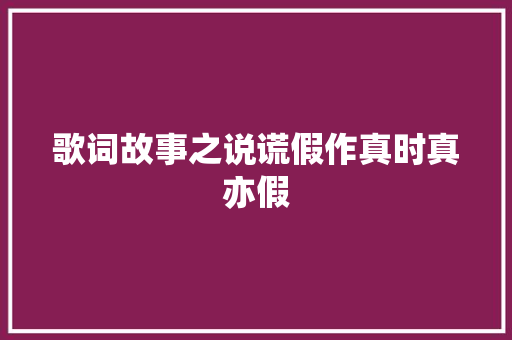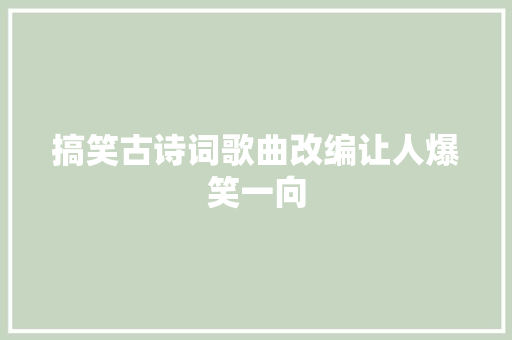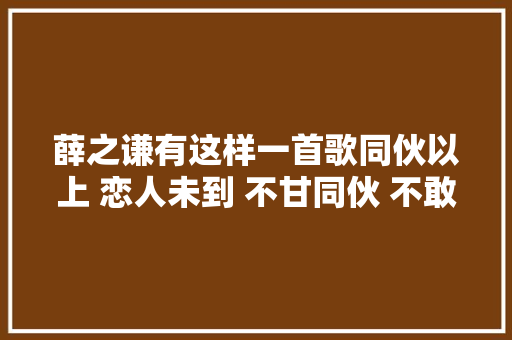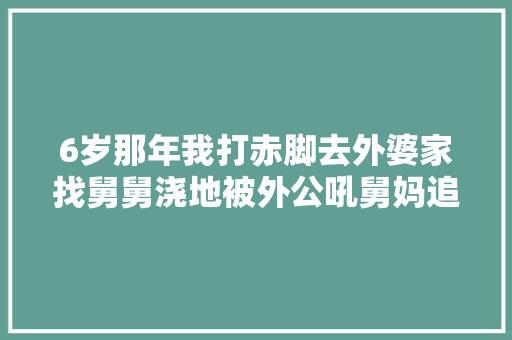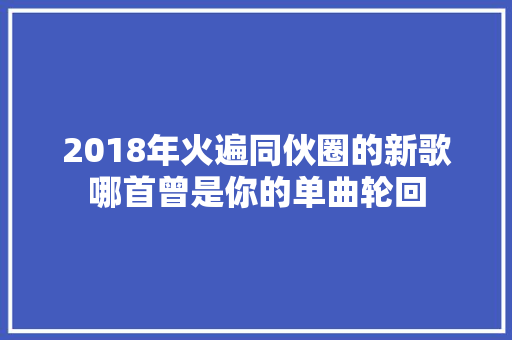作者 王洪
母亲的生平很平淡,她这一辈子彷佛没有为自己活过一天。瘦小的身躯,懦弱的心灵中有无数的无奈。被强势的父亲压迫得不敢大声说话,无论是被责骂还是被嘲讽,她都是一副笑脸。在我出生前她的腿就受了伤,留下了残疾,走路蹒跚。她很难得上一次街,彷佛一辈子都没有自己做主花过一分钱。

我刚有影象的时候见到母亲第一次落泪,是在一个夜晚。石油灯挂在高高的墙上,她在筛着玉米粉(手工石磨磨出的玉米粉粗细不均),父亲坐在椅子上一边抽着烟一边大声地骂着她,我和哥哥姐姐都吓得不敢说话,都不知道妈妈为什么要被骂。她不说话,眼泪一直地流过脸颊,从嘴角聚到下巴,我看到泪水点落到竹筛里的玉米粉上。我良久都不愿意吃那玉米粉,害怕吃到妈妈的眼泪。
我九岁那年读二年级,一学期学费两块钱。快放假了,中午放学老师叫下午一定要把欠下的一块钱学费带去。回家吃午饭,父亲不在家,到家我就给母亲说下午要缴一元钱学费。她一贯说没有,吃完饭我哭着连续要一块钱,她还是说没有,叫我快去上学。我哭着不肯走,她开始在家翻箱倒柜地找钱,我放低哭声,看着她把父亲的包包、衣服、抽屉都翻了个遍。她捧着几个硬币递给我,我一个一个看了,加起来只有一毛一分钱。我没有要,放大了哭声,母亲也哭了起来,大声地给我说家里真的没有钱啊,她的泪水掉在了手心的硬币上。她把硬币放在我面前的板凳上,叫我拿去先给老师,我还是没有要,我只想要一张一元的纸币。她哭着去洗碗干家务,我就一贯哭,她偶尔说一句你父亲回来了,我立时停下哭声,看了一下没回来我接着哭。那天下午我没有去上学,哭到太阳要下山了,母亲给我说你父亲立时要回来了你不要哭了,我不给他说你没有去上学,我才停了下来。晚上父亲哥哥姐姐都回来了,彷佛什么都没发生过。
岁月无痕,转眼我和哥哥姐姐都成家立业。母亲依然安静地生活,她与世无争反面任何人生气,常常一个人坐在椅子上哼着五十年代的小曲。我们都终年夜了,她成了家里那个“最愉快的孩子”,几十年没有吃过药也没有进过医院。
母亲的身躯越来越矮小,走路的步伐越来越蹒跚。在她八十岁的那一年溘然倒下了。脑梗阻,失落去了措辞能力和进食能力,从鼻孔插了一根管去胃里,一日三餐都靠注射器注入食品。她悄悄地躺在床上,每次去看她都在睡觉,叫醒她睁开眼睛,泪水就一直地从左眼角跨过鼻梁汇到右眼角流到枕头上。她的眼睛随着我的身影迁徙改变,她很想对我说话,可很无奈一个字也说不出来。拉着她的手,一点力气都没有,只是一直地流着眼泪迁徙改变眼睛。她可能是要我拔掉鼻孔里的那根管子,我们都知道她再也站不起来了,可谁也不敢开口说把管子给拔下。
就这样拖着,让母亲受了五年苦。末了一年我去看她时,她的眼泪已经流干,没有了眼泪眼睛也不迁徙改变了,就这样逐步地闭上了双眼。
回忆这么多年,平淡的日子我们都忽略了母亲的存在,她悄悄地来又悄悄地走了。她一辈子没给我们提过任何哀求,走的时候也没有留下只言片语,唯一给我留下深刻回顾便是她的泪水。
审核:张军华
编辑:金宁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