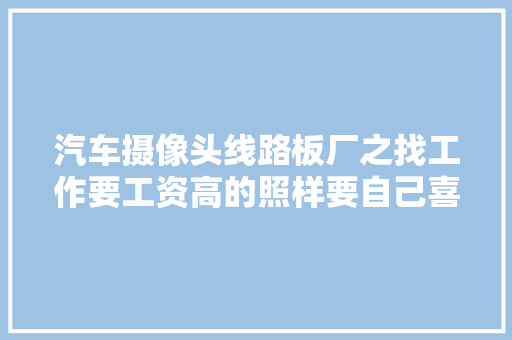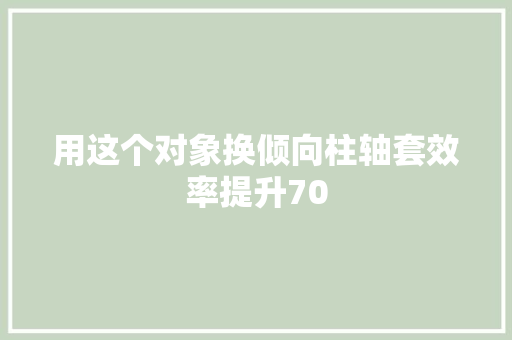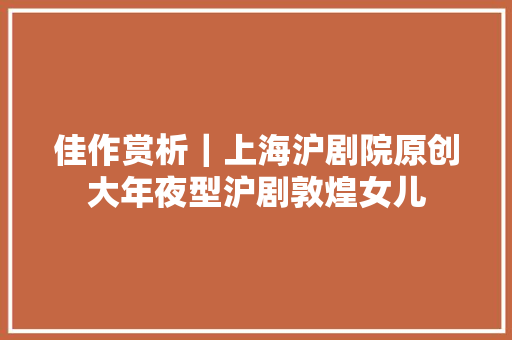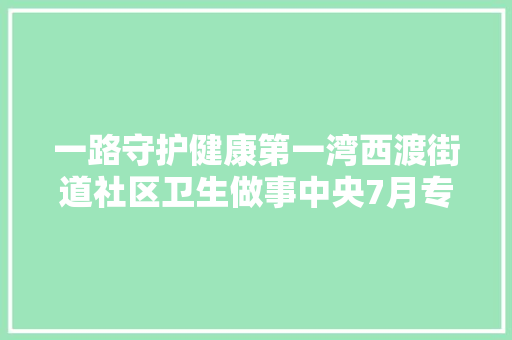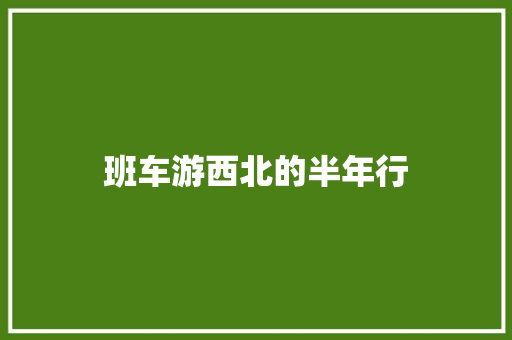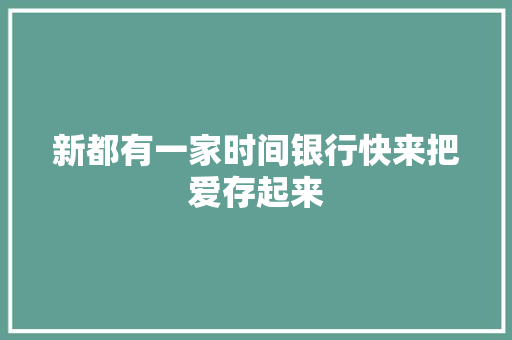“那您以为漆对他意味着什么?”
“这还用问吗?漆便是他的生命啊!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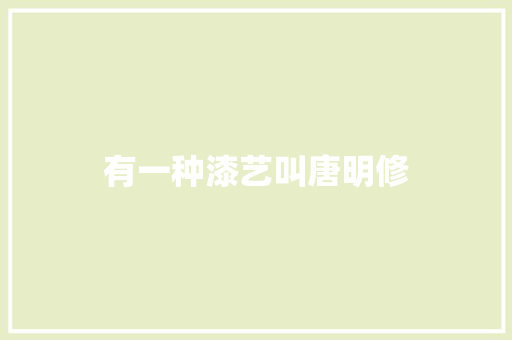
我与唐明修多年好友余闻荣的访谈,以这个问题结束。近两个小时的发言清晰勾勒出唐明修的创作脉络,然而,余闻荣对末了一个问题不假思虑的回答,却让我陷入了恍惚:艺术家将创作视为生命并不让人惊异,但漆只是唐明修创作的媒材,一种物质,他的生命为何与漆牢牢关联?
唐明修在漆园
唐明修曾在一次采访中谈及当年收到福建省工艺美院漆艺系录取关照时的第一反应竟是去世亡和恐怖。他想起童年时在邻居老人的葬礼上看到的漆髹棺材的过程。彼时尚年幼的他并不理解作甚去世亡,当然也就不以为害怕。漆工见他在一旁好奇不雅观看,便对他说:“这是木材最好的涂料,颜色俊秀,埋在土里几千年都烂不了”。
毕业后,他被分配到福建博物院事情。博物馆中展陈的考古出土的大漆文物让他回顾起漆工的那番话。这次他想到的不再是去世亡与恐怖,一个新的词浮现在他的脑海——不朽。学校的课程仅仅教会他将漆作为颜料来达成图示的再现效果,比较之下,那些历经千年色彩依旧残酷的漆器则让他窥见漆的材料措辞魅力、辉煌的历史与悠久的文化积淀。由此,他真正进入漆的神奇天地,开始了长达三十多年的探索与实践。
DUNHUANG FRESCO SERIES
敦 / 煌 / 壁 / 画 / 系 / 列
敦煌系列 唐明修 作
与此同时,八十年代两次游览敦煌的经历更是对他产生了主要影响。唐明修已经不记得初次踏上去敦煌的旅途是出于什么缘故原由,只是回到福州后,他临摹敦煌壁画创作了一批漆画作品,并带着这批作品去日本展览。这批在海内无人问津的作品大受日本藏家欢迎,发卖一空。与同期间乡土自然主义、唯美主义及工艺性的漆画比较,这批作品拓展了漆画的图示措辞。
日本带给他的绝不只是“第一桶金”,也让他敏感地意识到自身的文化印迹。他常以咖啡和茶做比喻。虽然在国外的时候常常喝咖啡,也并不以为咖啡难喝,但每每入口之际,他想到的都是茶。这种文化自觉使他“一贯关注东方漆艺自身的文脉……追求纯洁大漆内敛的东方气质(陈勤群)”,并贯穿其三十多年的漆艺实践与传授教化。
敦煌系列 唐明修 作
敦煌系列 唐明修 作
返国后不久,他再次拜访敦煌。那时的敦煌还没有沦陷为旅游景点,虽然饱经沧桑,岁月的痕迹却为这片佛教净土平添了几分旷古之味。千百年前佛教信徒的虔诚透过莫高窟残破的壁画和佛像,直抵民气。如果说博物馆中的漆器展示了漆作为一种物质可以超过历史长河,那么敦煌向他抛出的问题则是如何引发漆所蕴含的巨大精神能量。
敦煌系列 唐明修 作
他再次以敦煌为题创作的一系列作品正是对这一问题的思考的延续。这批倾尽他所学技艺的作品并非纯挚临摹复制壁画的图像。大漆千文万华的肌理、浓郁深奥深厚的色彩尤其适宜表现敦煌之精美,同时,他也描述了韶光留下的斑驳。敦煌并非一成不变,它令人惊叹的美是人类与韶光共同的创造。
正如在与唐明修简短的交谈中,他提及前段韶光看到电视上播放的记录片里的敦煌,已经和他影象中的敦煌大相庭径。这一系列作品以漆捕捉了敦煌1500多年生命中的某一刻,并封存个中。而它们在完成确当下,即开启了自己的生命进程。只不过与敦煌壁画不同的是,漆的颜色会随韶光的流逝逐渐开显,质地也更臻莹润。
DEER PARK
鹿 / 园
《鹿园》六联幅 唐明修 作
当我在玄之美术馆的展览《无住》上看到这一系列创作中最大的六联屏作品《鹿园》时,它所展现的正是这样一种效果,二十多年的岁月让它愈发流光溢彩。漆画层层施色,逐步磨显的技法让画面更富层次感,奔跑的马、跳跃的鹿、运动的人、舞动的树因此也越加生动。古朴的色彩合营金箔银箔,以及利用各种漆艺技巧雕琢的细节,完美演绎了《鹿王本生》的他乡佛教传说。而他在日本期间是否受到了同期间风靡日本的印象派潮流的影响,这已不得而知。但从《鹿园》的图像构成(色彩、线条、构图等)可以看出,他试图冲破漆画传统范式,融入当代绘画措辞,实现从装饰性到表现性的转变。
《鹿园》大图欣赏
但《鹿园》不是全然复制《鹿王本生图》,这意味着它并非旨在记录、回顾,或是成为敦煌的索引。艺术家截取了故事的一小部分进行再创作,摒弃了作品原生的宗教语境。画面中利用的绘画技巧或者大漆工艺虽属博识,却也不似为了炫技。彼处的敦煌与此处的敦煌更像是韶光线上按照各自速率背向而驰的运动:一者逐渐老化剥落,走向“去世亡”;一者缓慢“成长”,驻留光阴。
《鹿园》局部 唐明修 作
但此中凸显的只是漆的材质特性吗?目前已知的漆在人类历史中的利用痕迹最早可以追溯至8000多年以前,也便是说唐明修创作的敦煌系列作品可能将拥有比敦煌壁画更长久的生命。如果敦煌壁画以宗教、崇奉的力量为其不朽的精神内核,那么对漆而言,不朽便是其本身。但韶光、生命等一样平常意义上的绝对之物只是理念的工具,我们无法呈现其范例,“由于呈现,是相对化,被放入背景和呈现的条件里,在准确的状况里造型。以是,我们无法呈现绝对之物。但是我们可以呈现‘ 有绝对之物’这件事(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在此,作为韶光存在之象征的不是敦煌的视觉再现,正是彼处敦煌与此处敦煌的关照。
敦煌系列 唐明修 作
敦煌系列 唐明修 作
于是,我们站在《鹿园》前,面对的是韶光被撕裂所展开的缝隙。不过,这一韶光是物质的韶光,它与人类的韶光利用不同的刻度。就像对付杭州萧山跨湖桥出土的8000多年前的漆弓而言,人类个体的生命或许只是短暂的7秒。这种对生命与韶光的觉知成为唐明修日后创作的关键成分,也表示了他对大漆独特的艺术措辞的理解。
“它古老得险些让我们不知所措,尤其是当我们在狂妄地企图用当代人的力量去授予它再生的能力之后,谦卑和戴德地停下来,思考我们的态度和坚持,坚持一块材质的阵地,谢绝一些勉强的趋同,保持一种文化身份……这意味着经由‘慢下来’的过程,我们才可能完成对自身的超越(唐明修)”。
唐明修的漆园,如今唐明修漆艺术研究院亦挂牌于此
他对韶光和生命的体悟的另一个主要来源,是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持续了十几年的“隐居”生活。1994年,他在福州北峰觅得一处生有漆树的山谷,就此落地生根,营造了自己的寓所兼漆艺事情室,取名漆园。余闻荣说那是唐明修最安心于创作的阶段。贰心无旁骛地沉浸在自己的天下里,“原来只是勾留在潜意识里的一些一闪而过的创作想法也会日渐成形,很多创作线索就这样被韶光串起来。这种状态是饱满而永不饱和的,也是艺术本身须要的(唐明修)”。
漆园一角
唐明修与朋友们在漆园互换
那几年,与自然的反复对话给予他丰富的创作灵感。“我修房、建园,看着春去冬来,漆树的成长,它们在我门前的溪水边,在我庭院的岩石间,在我屋后的树林里……我看到它们随四季变革着。春天的新绿,夏天成串的果子,无数的小鸟在上面觅食,到了秋日,满树是俊秀的朱砂、黄骠……冬天红叶落尽,那树是玄色交错的线条……我又看到那树干被割破后流出的树汁,开始是白色,然后变成褐色,经由加工提炼后变成了玄色,我想这是我目睹的漆的生命过程,我越来越笃信它是一种活的物质,是一种有生命的材料……它的呈现须要自己的温度和湿度”,“都会使你沉下心来,顺应它(唐明修)”。
《敦煌》《无障》等系列都属于这一“慢下来”期间的创作。这批创作周期长达数年的作品质外能表示漆的质感。在余闻荣看来,漆是光阴的艺术。当创作者在制作过程中留给漆充足的反应韶光,漆终极将回馈无与伦比的视觉效果。
唐明修在漆园
在山上的十几年间,除了漆画以外,他还创作了诸如《臼》《槽》《璜》以及后来的《漆碗》《无尽》等难以被归类为漆器的作品。在《臼》《槽》《璜》系列中,根据石臼、圈井等脱胎制作的漆器,被他随意丢弃在户外,任由它们被一种叫做薜荔的植物覆盖吞没。有人认为《漆碗》《无尽》像是艺术家为自己设定的一个永久不可能完成的任务。2000年,他在山上的事情室中用竹胎制作了一个直径6.7米,高1.8米的大碗。
由于体积巨大,这个碗被“困”在了屋中,如果要运出来就必须上房揭瓦。他并没有考虑那么多,也没有设想过终极的效果。从胎系统编制作好的那天开始,他断断续续的髹涂着,但碍于面积过大,始终进展缓慢。完成这个漆碗就像是愚公移山或精卫填海,须要无休止的劳作,日复一日,却始终遥遥无期。但结果真的主要吗?与其他人不同,唐明修并不认为作品在完成的那一刻是最完美的,漆从母体分开之后,保持着变革莫测、不可捉摸的生命力,这使得作品始终随着韶光成长,正如马克·罗斯科所言:“结果是一个永恒创造的过程”。
《碗》
尺寸:670×180cm
材料:大漆 毛竹 瓦灰
漆,须要韶光,更须要一双手的劳作。“漆的神奇,还在于只用眼无法领略它的所有美妙。你还必须用手去触摸,存心去领悟它的色调和质感,只有在这些之后,你才渐知它的迷人所在(唐明修)。”九十年代,他在山上与漆为伴,日复一日的髹漆、打磨让他变得安静、淡然、专注,有时乃至忘了自己在做什么,陷入入迷的状态,仿佛在与漆交谈,感想熏染漆的生命力,也通过漆来思考自己的生命。
他曾如此描述自己那时的创作状态:“我从未敢说是我创造了作品,相较之下,更准确贴切的觉得是——当我进入状态后,我会听到它对我的哀求,这时,我能做的事就只是屈服它。有时我乃至不能清楚地明白自己在做什么,但那种觉得真是难以言表!
而末了的结果每每让我震荡,然后,我释然,由于,它本身便是我的!
”
漂浮在水中的莫高窟 唐明修 作
艺术家对物我合一的关系的追求早在其八十年代创作的作品《这里有你的影子》中就可见端倪。他将“原木纹理用生漆灰粘贴于画中,依照有序的纹理和木的结节,髹饰银箔,罩涂黑漆、点缀髹饰朱漆,再逐渐研磨使其透出一种非常纯粹的深奥深厚质感(支炳山)”,终极作品的表面从远处看就像一壁黑亮可鉴的镜子。这件作品不仅保留了木胎的本色,将漆特有的材质效果发挥到了极致,同时,以一种非常诗意的办法磋商创作与媒材、作品与不雅观众、历史与当下的关系。可以看出这一期间,他虽然还勾留在漆固有的语境中寻求完美与创新,但已经开始思考主体性问题。
锦衣 唐明修 作
漆语 唐明修 作
于二十世纪初创作的《断纹》《漆语》《锦衣》《岩韵》等系列作品在探索漆的当代性转换的同时,创作者不再是被程式化流程与技艺规范遮蔽的匿名者。主体的在场,通过手的动作被记录在了作品中,比如《断纹》系列中人为制造的缝隙,《岩韵》系列、《雨声》《日食》中对火的利用,《漆语》《锦衣》系列中将底层麻的抽取分离。这些动作并非无意识,而是对习气和规则的叛离。
唐明修曾说:“山上的生活对我的影响超越过往任何的经历,我想我是一点一点地在体悟漆的生命,我开始抛弃过去设计图示的观点,让漆同我一起为所欲为。有时我能感到我在很畅快地表达我的感情,在我现在的一些作品中,我逐渐找回了个人的心情,找回我个人的喜怒哀乐。同时,我也创造‘漆’这种材料可以淋漓即兴的一壁,它可以容许我放肆激情”。
敦煌系列 唐明修 作
敦煌系列 唐明修 作
这种为所欲为的状态,正是在经年累月的劳作中身体得到的顿悟,而身体动作的残余及其传达出的感情起伏在这些作品中形成了地层学式的共存。“这便是我们不雅观看天下的办法:通过自己的身体。”集墨客、佛教徒、护林人于一身的加里·斯奈德这么写过,而在法国哲学家莫里斯·梅洛-庞蒂的身体—主体理论中,知识是“通过觉得得到的”,身体在意识之前,已经拥有其独特的思考和理解办法。意识、肉体和征象天下密不可分地交织在一起。肉体使我们的主不雅观意识“具象化”,我们因此“嵌入”了天下的肌肤。他将这种嵌入式的履历描述为“手中的知识”;身体帮我们“捉住”天下,是我们拥有天下的普遍媒介”。因此,天下本身不是自然科学所呈现的不变的工具,而是无止境的关系之网。它只有在各种视角里才能显现,而我们之以是能够瞥见它,依赖的正是我们的身体及其感官功能。
敦煌系列 唐明修 作
唐明修从80年代开始的收藏与修复古玩器物的实践,以及《念物记》《器物重生》等作品正表示了这样一种“嵌入”。它们“可以被当作一种阐明来阅读——即某些先于我们存在之物,通过‘修复’得到某种当下的‘共在’。或者,也可以理解为修复者对历史的冲动(一次业报?),通过无休止的髹漆过程,对自身的存在与韶光的关系提出了打听。这样的打听其目的不是复现古物,而是从那些不同年代的残物的修复中,把握一个人的行动及其基本属性以某种办法存在的可能性(唐明修)”。
敦煌系列 唐明修 作
敦煌系列 唐明修 作
修复古物与漆髹大碗的动作背后都蕴含着韶光的长度,但二者享有相同的所指吗?《漆碗》的髹涂是慢工细活,它侧重于双手的能力与代价,以及通过劳作所能达到的心灵的沉着。在艺术家看来,它间接地修复了当代社会人与韶光和自然的关系。而修复古物对付艺术家而言则是慢工细活中间的一次安歇。这些古物自身所具有的历史与文化属性为作品供应了无限时空中的锚点,“将某种伟大的传统生活履历修复为一个常景”,表示了创作者的文化自觉。这种自觉不仅哀求艺术家贯彻自身的文化身份,也同时寻求对漆的本体措辞的溯源。
例如在《虫书》《仓颉说文》等作品中,漆被视为中华文化影象的载体;《禅板》中素髹所表示的禅宗思想;而《漆·本生》展示的漆的生命进程则带着东方“形而上”的思考。他说“传统与自然作为我们对艺术的认知路子,实在质是生命性的。” 而无论是修复与韶光的关系,抑或与传统的关系,都展示了漆作为一种有生命的物质,拥有奇妙的修复能力。
敦煌系列 唐明修 作
“您曾说对漆的第一印象是去世亡与恐怖,那么,三十多年后,您如何看待漆这一媒材?”
“我以为它拥有重生的力量。”
2019年3月23日,我与唐明修的简短对话至此戛然而止。在交谈中,他坦言道,由于前年的意外事件,他已耐久未碰漆,所学的技艺也基本不记得了,但他并没有放弃创作,新的作品仍在构思中。2005年,应邀出山,创建中国美术学院漆艺系;2014年,被任命为福建美术馆馆长,十几年间,他疲于世俗事务。近日,听闻他再度搬回漆园,回到山中,就像梭罗重返瓦尔登湖。巧合的是,他曾到上海拜见静安寺的明旸法师,法师给他取了一个法号,妙修。同时,还送了一个牒子,并见告他“知倦归巢”。唐明修是一个相信缘分的人,或许他命中注定与漆有不解之缘。
敦煌系列 唐明修 作
敦煌系列 唐明修 作
他曾教导学生“技艺并不主要,它只是人生很小的部分。主要的是你怎么面对自己,如何过这生平。”但唐明修其余一位至友、墨客、画家吕德安说他更乐意流传宣传自己只是个油漆匠。“我觉得不到那是一种态度上的浪漫的落差,或企图自我消解,而是某种致力于沉默的实践精神,我依稀看到一个人正在退远几步说话——或是站到了他的起源里,黑洞洞的,听起来有点宿命但令人敬畏。”
敦煌系列 唐明修 作
三十多年前,他被漆选中。三十多年后,他选择与漆朝夕相伴。在这个被他称为“自由的精神道场”中,他再次“慢下来”,回到生命与韶光本身。
“我的灵魂随着漆液的流淌,神奇地变换生命的过程。”
更多作品欣赏敦煌系列 唐明修 作
敦煌系列 唐明修 作
敦煌系列 唐明修 作
敦煌系列 唐明修 作
敦煌系列 唐明修 作
敦煌系列 唐明修 作
敦煌系列 唐明修 作
敦煌系列 唐明修 作
敦煌系列 唐明修 作
敦煌系列 唐明修 作
INTRODUCTION OF ART
艺 / 术 / 简 / 介
唐明修
1958年生于中国福州,福建省美术馆馆长、中国美术家协会漆画艺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美术学院中国漆艺术研究中央主任、中国美术学院中国漆艺术专业主任(硕士生导师)。
近年主要展览
2015年
福建·泉州 回归与启航:中外艺术家当代陶瓷对话展
2014年
福州·福建省美术馆 大漆艺术——2014海峡漆艺术大展
北京·中国美术馆 大漆艺术——2014海峡漆艺术大展
福建·厦门市美术馆 漆语·中国美术学院漆艺术作品展
福州·福建省美术馆 漆语·中国美术学院漆艺术作品展
2013年
杭州·浙江省美术馆 “八闽神韵”福建当代字画名家作品海内外巡回展
武汉·湖北省美术馆 源流·2013湖北国际漆艺三年展
杭州·萧山跨湖桥遗址博物馆 源·流|中国漆艺术佳构展
主要获奖
1984年
北京·中国美术馆 第六届全国美展(银奖)
1985年
北京·中国美术馆 首届中国体育美展(铜奖)
2002年
福建·厦门市艺术展览馆 中国首届漆画展 (铜奖)
大型漆壁画
2012年
大型漆壁画《井冈山》 中共中心军委某机关
2011年
大型漆壁画《万里长城》《黄山风光》 中共中心军委某机关
2010年
大型漆壁画《文成公主进藏图》 西藏自治区 西藏林芝地区博物馆
漆屏风两组《云水间》 上海世博会中国馆
2009年
大型漆壁画《福州古城》 福州镇海楼
大型漆壁画《酒仙图》 马鞍山李白纪念馆
大型漆壁画《林则徐治水图》 福州市林则徐纪念馆
1998年
大型漆壁画《光耀八闽》 福州市公民政府大楼
1993年
大型漆壁画《闽山闽水橘子红》《榕树水仙茉莉花》 福州市公民政府大楼
任评委展览
2013年
福建·厦门市美术馆 中国(厦门)漆画展
2012年
江苏·南京艺术学院美术馆 第三届全国漆画展
2011年
福建·厦门市美术馆 中国(厦门)漆画展
2010年
福建·福建省美术馆 “从河姆渡走来”第三届国际漆艺展
2009年
北京·中国美术馆 第十一届全国美术作品展
杭州·浙江省美术馆 第十二届浙江省美术作品展
2007年
福建·厦门市美术馆 厦门国际漆画约请展
广东·广州艺术博物馆 第二届全国漆画展
《文化生活报》4大连版
本文首刊于玄之美术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