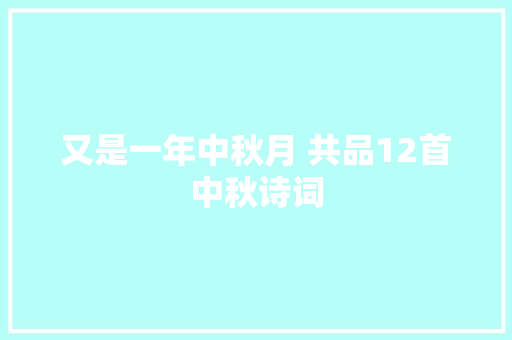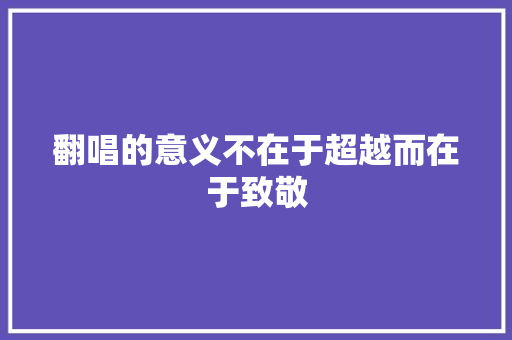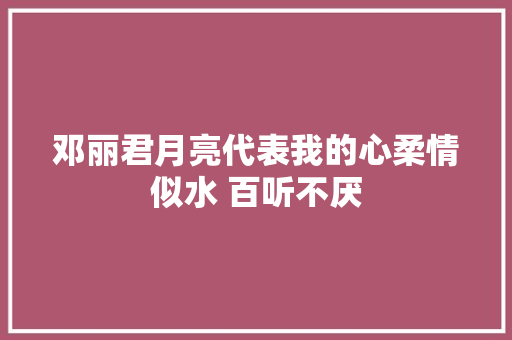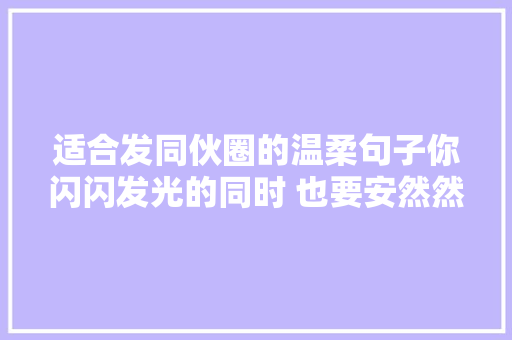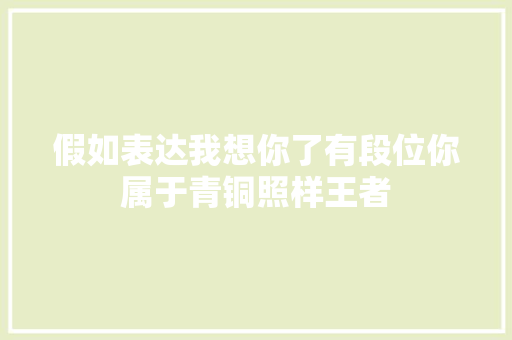也照着富人
玉轮照着东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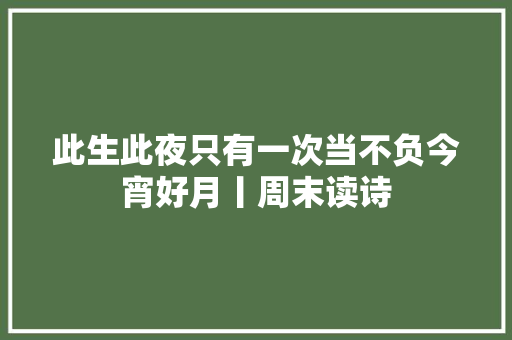
也照着西方
玉轮
脉脉无言
从不争辩
大概
玉轮是地球的一个梦
地球是众生的一个梦
你是我的一个梦
感激你入我梦中
《望月》(三书)
祝福大家华枝春满,天心月圆。
没有玉轮的中秋节
/ /
《一剪梅·中秋无月》
辛弃疾
忆对中秋丹桂丛,花也杯中,月也杯中。
今宵楼上一尊同,云湿纱窗,雨湿纱窗。
浑欲乘风问化工,路也难通,信也难通。
满堂唯有烛花红,歌且从容,杯且从容。
/ /
又到中秋。去年这天,我专程乘火车,带着从亚洲超市买来的月饼,去S湖边看玉轮。风已很凉,堤岸树影中的长椅上,低头坐着一个醉汉,此外别无他人。我下到水边,坐在石头上等,双黄红豆沙月饼,也在一旁陪我静候。
久等不见玉轮出来,也不知玉轮会从哪边出来,将近十点,斜对岸山后透出亮光,玉轮终于要升上来了!
我锁定那个方向,瞩目良久,亮光却始终不动,原来是灯。夜气寒冷,天空阴云不定,只好放弃,吃着月饼往镇上走,我并不爱吃月饼。
回到小旅社,偶至后院,不虞撞见一轮明月,月色皎幽,清光含情,那一刻,我分明觉得到是在一个梦中。回房间后,开头这首诗在纸上落成。
玉轮是什么?我不知道,但这不妨碍我看玉轮。关于玉轮的诗,写不完,也读不完。纵然下雨,纵然无月,中秋也依然是玉轮的节日,以缺在的办法,玉轮依然在那里,被我们瞥见,被我们惦记。
辛弃疾的《一剪梅》,就写于一个没有玉轮的中秋节。今年中秋,总会忆起往年中秋,“忆对中秋丹桂丛,花也杯中,月也杯中。”那年的中秋节,回顾真是美好,有月有人,有花有酒,花光月影摇荡杯中。那年是哪一年?投南以来,削职闲居,报国无门,济世无望,反而屡遭权臣弹劾,英雄末路,壮气蒿莱,连玉轮也减了清光。
何况今宵无月,酒倒是有,强为登楼,但见“云湿纱窗,雨湿纱窗”。南方秋季大抵如此,南人或不以为苦,遭贬流亡的北人,却实难消受,国恨家愁,云雨般郁结心头。
假如有玉轮,尚可暂伴行乐,痛饮忘忧,可惜连月亦无。“浑欲乘风问化工,路也难通,信也难通。”切实其实想要乘风上天,去问问造化之工,为何今晚没有玉轮?然而,路也难通,信也难通。个人的小小哀乐,在宇宙间算得了什么呢。
“满堂唯有烛花红,歌且从容,杯且从容。”好在还有烛花红,还可就满堂烛光,饮酒歌唱,永夜漫漫,歌且从容,杯且从容。好在还有诗,天上无月,诗中有月,诗不会忘却你。
这首词二、四、六、八句,回环复沓,叠韵尤美。生存的缺憾,或多或少,可借由文学之美来修复填补。
清 陈枚《中秋诗意图》
此生此夜不长好
/ /
《阳关曲·中秋月》
暮云收尽溢清寒,银汉无声转玉盘。
此生此夜不长好,明月明年何处看?
/ /
爱看玉轮的苏轼,想必也爱过中秋节,想必每年中秋都写一首诗吧,流传至今的中秋诗词,大半都在他名下。“明月几时有,把酒问上苍。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这些句子已化入集体意识,中秋夜一看到玉轮,我们就想起《水调歌头》,就会情不自禁地吟诵。上片诗情实在来自李白的《把酒问月》,李白与苏轼两位大墨客,差不多垄断了汉民族对玉轮的文学想象。
丙辰中秋,苏轼欢饮达旦,挥毫泼墨,写下千古绝唱《水调歌头》,兼怀乃弟子由。这一年,兄弟二人久别相逢,欢聚赏月。苏轼填词,调寄《阳关曲》,王维的《渭城曲》绝句,宋初歌入《小秦王》,后更名为《阳关曲》。听其名即知词的内容将涉别情。
词题“中秋月”,自有人月圆之喜。“暮云收尽溢清寒”,起初月被云遮,待暮云散尽,转觉清光寒且多。月光如水,由“溢”字见得。“银汉无声转玉盘”,天河本即无声,此处反写,彷佛本来听得见声音,那是由于近,无声的觉得来自银河逐渐淡远。玉轮像一只白玉盘,在空阔的天宇,悄悄地迁徙改变。
此生此夜,只有一次,佳会难得,见少离多,故当尽情欢快,不负今宵好月。“不长好”的意思,还在于良辰美景,生平能有几次?兄弟分离在即,不是确定的事么?“明月明年何处看?”这句用问号,表示未知,明年中秋你在哪里,我又将在哪里,谁知道呢。足迹梦影,不是人生的常态么?
“此生此夜不长好,明月明年何处看?”对仗天成,妙手偶得,叠字唱答,仰对明月,太息人间只是悠忽一梦。
南宋 马远《举杯邀月图》
世事一场大梦
/ /
《西江月》
苏轼
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
夜来风叶已鸣廊。看取眉头鬓上。
酒贱常愁客少,月明多被云妨。
中秋谁与共孤光。把盏凄然北望。
/ /
关于此诗作于何时何地,以及北望怀想的是谁,不同选天职歧论者有不同的说法。或认为苏轼于1080年作于黄州,北望所想乃是汴京和宋神宗,题为“黄州中秋”;或认为于1097年作于儋州,所望所思乃是子由,题为“中秋和子由”。抛开这些已经无解也无所谓的辩论,总之,这年的中秋节,苏轼很孤独,心情可归结为一个字:凉。
词中每一句、每个字,都透着凉意。发轫便气氛凄凉,“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时节入秋,景象转凉,秋凉,或作“新凉”,秋日的新凉使岁月忽然转向。从去世亡的方向看,世事不过是一场大梦。如何知道是梦?只有梦醒,醒来时才创造,原来是个梦。夜晚就寝中所做的,是小梦;被我们称之为人生的,是大梦。小梦易知,大梦难觉。
人生几度秋凉?这场大梦何其短暂,不过几度秋凉,转眼之间,忽然就到了终场。“夜来风叶已鸣廊”,风吹树叶,回廊上阵阵鸣响,风声凄凉。“看取眉头鬓上”,同样是衰谢,同样是将至的去世亡。
“酒贱常愁客少,月明多被云妨。”独客异域,情面冷暖,中秋谁与共孤光?把盏凄然北望。望到了什么?仍是悲惨。
苏轼并非一味旷达。无论发生什么,心中都不动感情,只有旷达,那样的人该有多恐怖,那不是旷达,该是麻瓜吧。旷达的人,首先是不自欺,然后再超越自己。
《水调歌头》词曰:“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苏轼那夜欢饮,醉意飘然,直欲乘风归去,飞往天上宫阙,但转念又止,他怕高处不胜寒,还是回到了人间。苏轼终归是眷恋人间的。而在这首《西江月》中,遍人间也寻不到温暖,情何以堪?他只好把盏北望,聊藉回顾取暖和,聊以思念自燃。
写到这里,举头忽见玉轮,不知何时已升起,来到我的窗外,在对面公寓楼顶上空,有些朦胧,阁下几缕微云飘浮。尚未满月,但也很美,不可思议,孤悬天宇,这么近,那么远。
我们看的是同一个玉轮吗?是李白、苏轼、辛弃疾看过的玉轮吗?抑或我们都只是梦见自己看到了玉轮?我的意识在宇宙之中,还是宇宙在我的意识之中?
且有大觉而后知此其大梦也。大概,我正梦见我写下这篇笔墨,而你正梦见一个叫三书的作者提出了这些吊诡的问题。
作者/三书
编辑/张进 李阳
校正/陈荻雁 赵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