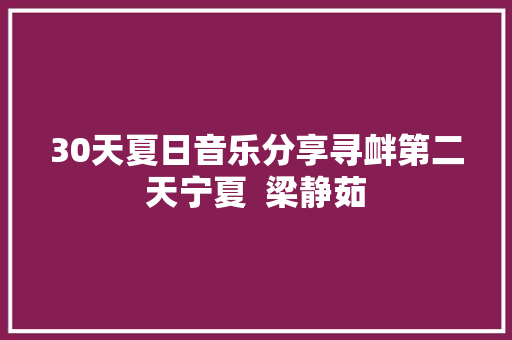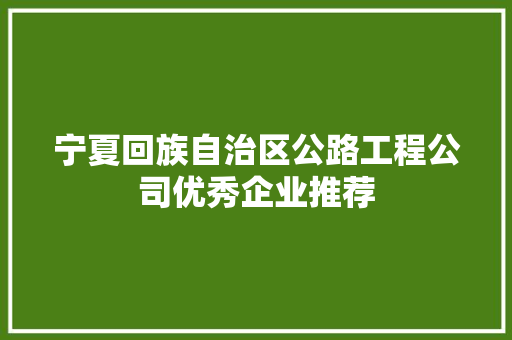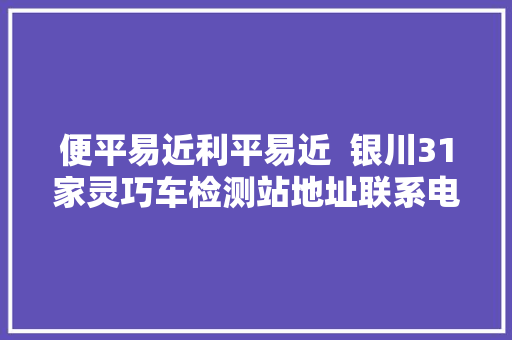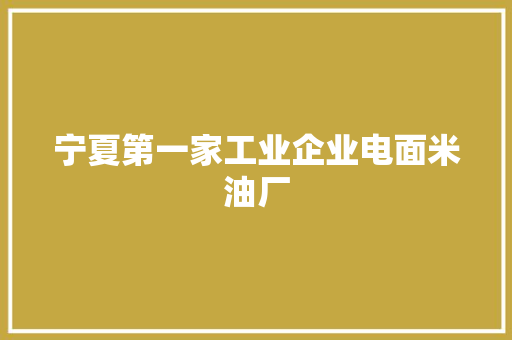在《贤良》大红以前,苏阳早便是西北民谣摇滚圈极富盛名的音乐人。他虽然出生在浙江温岭,但却在银川终年夜。90年代, 还是重金属青年的苏阳,把摇滚乐带到了宁夏川;2003年开始,三十多岁的苏阳又把摇滚乐套用在宁夏特有的,也是他最爱的民歌形式“花儿”中,把宁夏川的民谣民歌带给了全天下。
本日要讲述的城市,便是宁夏。身居西北要地本地的宁夏,背靠贺兰山,悠久的西夏文化在这里形成,古老的黄河文明从这里发源。提起宁夏,很多人的第一个印象便是那里地皮贫瘠、河水浑浊;那里的人们肤色黝黑,脸上全是被风沙打磨过的皱纹;那里“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那里满是望着关山月,哼着塞下曲的愁苦旅人;渡河的人们坐在羊皮筏子上,看着河那边荒凉沙漠上逐步前行的骆驼队,唱起孤独的歌谣。然而真正的宁夏川并不是这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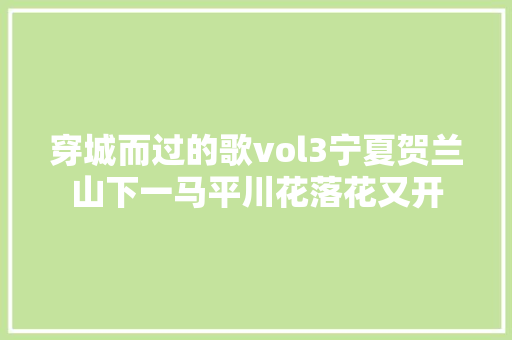
宁夏有个俏丽的外号——“塞上江南”,自古以来也有“天下黄河富宁夏”的说法。有人说,贺兰山下的宁夏实在不属于西北。由于贺兰山对风沙的阻挡和黄河在这里放慢速率,宁夏平原上的景象条件生存和栽种条件都相称好,以是才有“塞上江南”的美称。歌曲《宁夏川》里如此唱道:东靠黄河西靠贺兰山,金川银川米粮川。
95年,布衣乐队在宁夏银川成立。很多人从《罗马表》开始认识布衣,殊不知这支成军二十载的乐队早便是宁夏音乐的中坚力量。苏阳的歌扎根于花儿,扎根于宁夏的民谣,而比较之下,布衣的音乐则更有力量,更摇滚化(觉得两支乐队的差异就像九宝和铁骑)。实在,风格并不是决定一支乐队好坏与否的标准,无论什么风格,他们通报出的都是从宁夏这篇地皮上传出来的,最纯粹的声音。
去年夏天,我有幸和几个好基友去了银川和中卫,看到了黄河在沙坡头的大拐弯,吃到了心仪的羊杂碎,走过了当初大话西游“发生”过的地方,见识到了真正的宁夏川。这是我这么多年第一次踏上西北的地皮,老天爷乃至在我自己先到的那一天送给了我一场大雨(听说银川很少下雨,这见面礼实在太大),紧接着又送了我一起的晴天。
银川是座“移民城市”,有人说,在银川乃至连骂人的话都不能统一。“人们心里怀念的都是那个从来没有怀念过的家乡”,这或许是对银川最得当的形容。最让我惊异的还是银川市里的湖和湿地。听说由于历史上黄河数次改道,使得银川市内湖泊湿地浩瀚,古有“七十二连湖”之说。行走在这座湖城之上,乃至有种坐在一艘名叫“银川”的大船飘荡在大西北的荒原中的觉得。但实在银川的市区和很多大城市一样——你很难说这里是真正的“宁夏”,真正的“西夏”。提醒我这里是宁夏的,除了比其他城市多的清真寺和清真饭铺,还有街上大大小小的苏阳的演出海报。
但中卫就又是另一种样子。“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说的便是黄河在沙坡头这惊艳的一拐。沙坡头的沙漠在干热的空气和强烈的阳光下就像火炉一样,但你看到黄河水面上晃晃荡悠的羊皮筏子和两岸绿色的植被,才会以为这里真的是“塞上江南”。很多人从陇海线一起走来,走过嘉峪关,走过张掖,来到腾格里沙漠末了来到中卫,都会感叹这里切实其实便是江南水乡。而从中卫走出的两位极富盛名的音乐人,更是宁夏民谣的符号——他们便是赵已然和赵牧阳。
1963年,赵已然出生于宁夏中卫。他的歌声,无论翻唱还是创作,都带有浓重的布鲁斯和西北民歌风格。在这方面,迄今为止,尚未有过任何华语歌手达到过他的境界。他的演唱和吉他技巧同样民间、随意而又堪称博识,带有浓郁的沧桑情怀。赵已然的80年代老歌不但把他自己的青春变成一场无可挽回的旧梦,也足以凝聚更多人的悲欢离合,将苦酒和热泪融化成嗟叹。赵已然经历了无数的人生坎坷,也曾颠沛流离,靠借钱和亲友接济为生。2000年前后,一群人和他一起生活在北京东边的屯子。几年的韶光里,宁夏人、山东人,外地的摇滚乐手在那里出没。从那时起人们都叫他“赵老大”,直到现在。网上有太多关于赵已然的故事,他大病一场,落魄的生活就像西北的荒原,但他的歌还是那样,沧桑又满是情怀。
1967年,宁夏中卫,赵老大的弟弟赵牧阳出生了。比较于大哥的困顿生活,赵牧阳年轻时名声更加响亮——呼吸乐队、赤色部队、窦唯、超载乐队、鲍家街43号、许巍......他互助过的音乐人数不胜数,担当鼓手参加的乐队更是各个大名鼎鼎。也正是奔波在那个并不发达的摇滚时期,赵牧阳才更明白中国自己的音乐是多么主要。因此他从“西北鼓王”,转型而成为了一位民谣歌手。西北民谣的洒脱狂放和秦腔的独特韵味也被他表现得漓淋尽致。
关于宁夏川和属于它的歌,属于它的故事,本日就讲道这里吧。引一句乐评:“音乐的神秘力量,从地皮而来的声腔所具有的这片地皮的精魂,这精魂对这片地皮的揭示力量,是无法阐明的,更为歌词所无法承载。歌声一起,板胡一拉,中国西北角上干旱的地皮、苍凉的黄沙滩和土房、黄色的没有一点绿色的村落、冬天枯草边那结实的冰,俱在这种声音中涌现,详细而坚实,就像那片厚土一样。而家乡贫穷倔强的祖辈、还在故土里讨生存的父母兄弟姐妹、那些被下层生活和发达希望双重煎熬的人们,也在这种声音中涌现了。还有那些离乡背井的人们,疏弃了农田,去城市盖屋子,去南方工厂的流水线,与不支的身体和瞌睡儿作战。‘他们为劳碌后的低人为无法维生而争吵,哭,为生活的一点点改进而从心里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