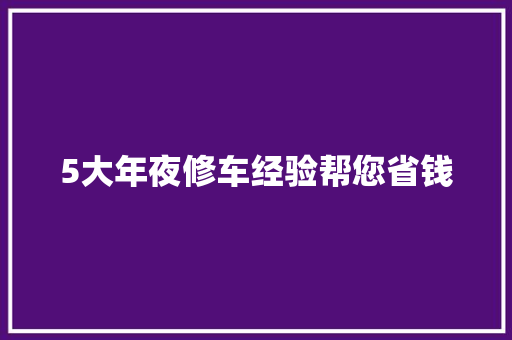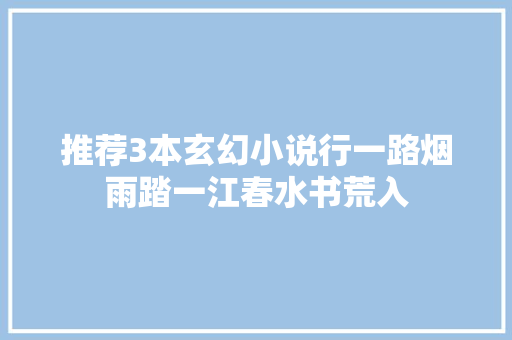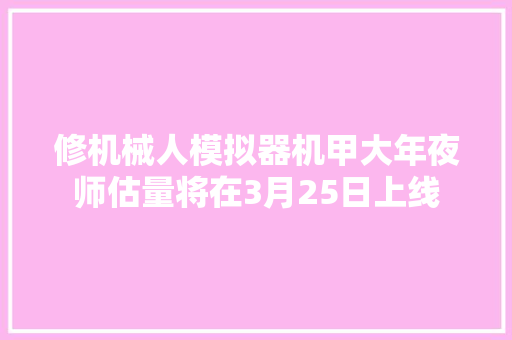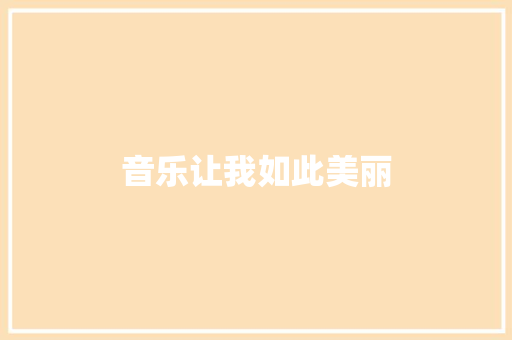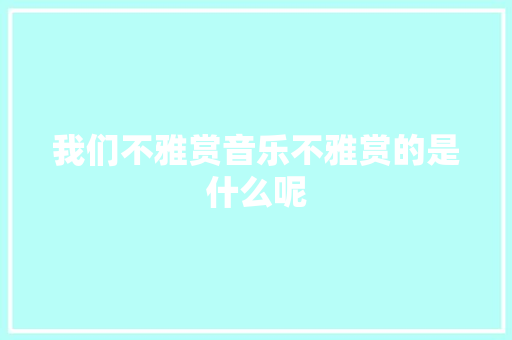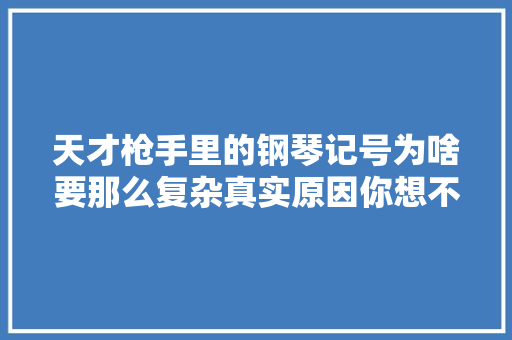这不但是个例,如今的影视作品中,白莲花已经不吃喷鼻香了,反而是“恶女”形象大行其道。
去年的金马奖上,就有一部“全员恶女”的电影大放异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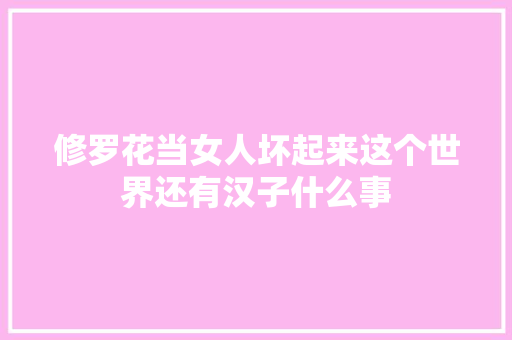
7项提名,并终极斩获最佳影片、最佳女主、最佳女配3项大奖。
等到现在终于出了资源,看过之后菌菌只想说,《血不雅观音》你值得拥有。
从海报上就可以看到《血不雅观音》透着一股诡异和惊悚。
影片的叙事表达也是这样,套用台湾传统的念歌形式,说书人阁下是冥王、是可以窥见世间的阴阳镜,全体环境犹如错落诡异的地府,让这个故事有了一种茶余饭后惊悚八卦谈的视觉。
虽然本片涉及“灭门血案,政治斗争,政商勾结,炒土地,黑吃黑”等浩瀚敏感政治话题,但导演却没有严明布局,而是拍摄成了这样一部诡异妖艳的奇情片。
菌菌很喜好这种风格,就像是在欣赏一朵从幽深湖底长出的猩红血花,花瓣掉到水里面,虽然腐败了,但颜色仍旧很鲜艳。
《血不雅观音》还有一个名字:《修罗花》。
修罗花,便是我们常说的彼岸花。
传说彼岸花开在地狱的黄泉路上,它代表去世亡,因此也被称为“去世亡之花”。
片中反复涌现的彼岸花也暗示着,棠家三代女人,活着犹如身在地狱,深受折磨。
故事环绕着一户官宦之家的三个女人展开,引申出三条故事线。
这三个不同年事、不同身份的女人,就像是这朵“修罗花”的三个组成部分——
母亲棠夫人(惠英红 饰),是这朵修罗花的根。
她是棠府地位和身份最高的一个人,节制和影响着全体家庭的命运。
表面上,她是一个做着正经买卖的古董贩子。
为官太太们买卖古董首饰,一起喝喝下午茶。
私生活却一点不“古董”,私底下,她是官商勾结中穿针引线的中间人。
行事调皮低调,毫无马脚。
在《血不雅观音》里,棠夫人有太多个面具。
粤语、国语、台语三种措辞交织在一起,共同构成了一个繁芜的女人,每一种措辞都代表着一个面具。
若说两个女儿都保存着一定程度上的自我与超我,进入到棠夫人的阶段,就已经有足够的心气与手段扒掉年轻时候的伪装,大胆地开释着自己惨淡的本我。
表面上看来她面孔和蔼,见了谁都是一副菩萨眉眼,导演给她披上的面具也奇妙非常——
念佛。
写书法。
在众夫人的聚会中,打扮永久比别人素净,不抢风头。
而这个女人一旦撕下假面,可太有趣了。
在她的天下里,情绪只是用来知足贪欲的工具。
可以说,棠夫人便是片中最为“妇黑”的一个人。
大女儿棠宁(吴可熙 饰),是这朵修罗花的花。
她有着美艳的外面和曼妙的身姿,是棠府的交际花。
棠宁是棠夫人的人肉武器,母亲利用她睡服了一个个男人,精神上极度薄弱空虚,烟酒不离手,而且还染上了毒品,每天不吃安眠药都无法入眠。
乃至会用酒送安眠药,绝不吝命。
被母亲的强权管束,被官商之间的虚情假意裹挟,她险些没有自由。
母亲在台前演戏,陪着夫人们谈论衣服珠宝,端茶倒酒。
风风光光的做好表面文章。
棠宁就要在台下增援,买通官员,讨价还价。
母女俩一唱一和,一黑一白,明修栈道暗渡陈仓。
但是,棠宁内心深处极度厌倦这样的生活,看似狂乱地生活着,却正好是片中的独醒者。
在她身上,故意欲反抗的挣扎与叩问,但更多的是识破现实的无奈与沉沦。
小女儿棠真(文淇 饰),是这朵修罗花的茎。
一方面,她正处于发达成长的期间,直接影响着棠府未来。
另一方面,她连接着这朵花的首尾两头,由于棠真实际上是棠宁的女儿。
棠真年纪尚小,却已经有了一副完美的假面。
在大人面前乖巧无比,有着与年纪不相称的光滑油滑圆融,乃至有一丝阴郁。
在棠夫人的调教下,她无言地领悟着大人们的天下。
什么话该说,什么话不该说。
什么事情该做,什么事情不该做。
一个眼色,她就能明白个中意思。
而假面背后,是“不被爱”的原形。
冷淡的表情下,是一个极度渴望爱与被爱的小女孩生理。
因此,影片中棠真的两场偷窥也别故意味,一场窥见性,一场窥听爱,性和爱构成了一个发育期少女对情绪的模糊想象。
在菌菌看来,棠真的线比起其余两条线,有着更强大的张力。
一边是小女孩还没完备褪去的纯白和对爱的迷恋,一边又是母权掌握下的扭曲成长,即将爆发出弘大的力量。
文淇怎么演这个多重复杂性的角色,可太主要了,而文淇的表现绝对是预期之上,创历史的年纪最小最佳女配得主,可不是瞎拿的。
大概这便是所说的天生吃这碗饭。
就像《嘉年华》导演文宴所说,“他们可能还不理解自己在演什么,但在他们身上有演戏的天才。”
棠家三个女人,一代都对另一代说,我是为你好,你要活得像个人样。
她们都曾试图逃脱掌控,试着得到自由。
但结果却一个比一个惨。
而家庭背后,是更错综繁芜的社会网络;女权背后,是更惨淡强大的男权;迷局背后是另一个大局,环环相扣,离奇弯曲。
但也正是由于想讲得太多,无论在人物关系、情节和主题表达上都相称繁芜,这反而让电影变得太满,电影的“超负荷”挤压了不雅观众的思考空间与电影本身的空间。
而导演的故事讲述又过于隐晦和细碎,原形要不雅观众一点点猜出来,乃至看了几遍过后仍有新创造。
这大概便是为何《血不雅观音》豆瓣评分没上八分的缘故原由。
在一个采访中,有问编导杨雅喆:
“好多人以为这部电影好繁芜,你怎么看?”
杨雅喆答道:
“很繁芜吗?该当是吧。
我的剧本画工笔画习气了,会一贯往里加细节。可能有人会以为雕工太细,但我自己以为,做编剧便是要有这样的职业道德。”
“把剧本当工笔画,一贯往里加细节”,有多少编剧乐意这样吃力不谄媚呢?又有多少不雅观众乐意花韶光去再三回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