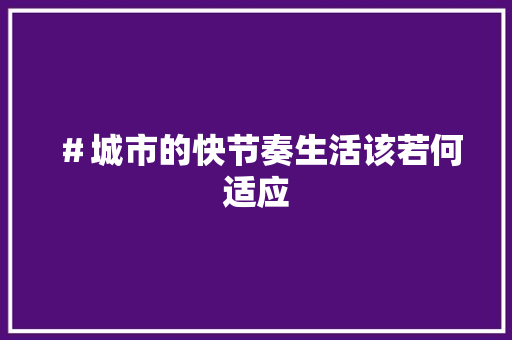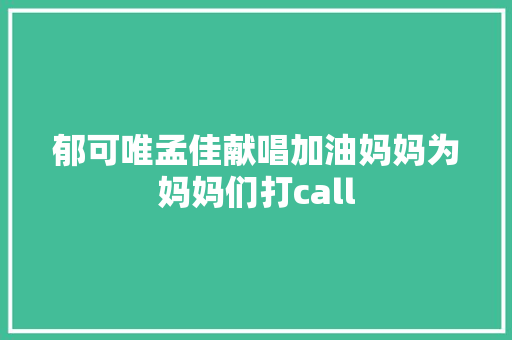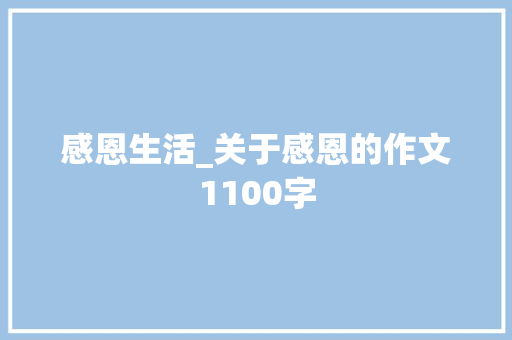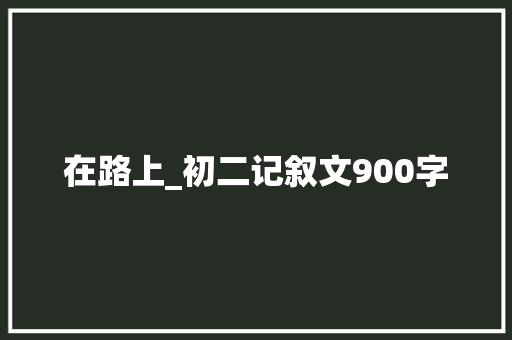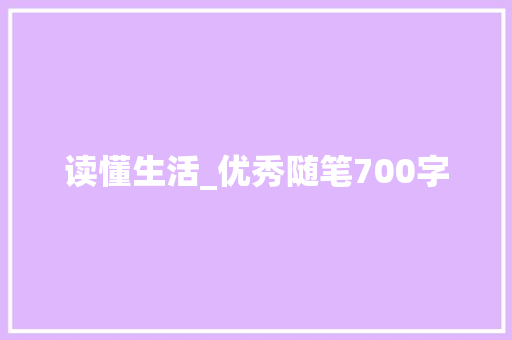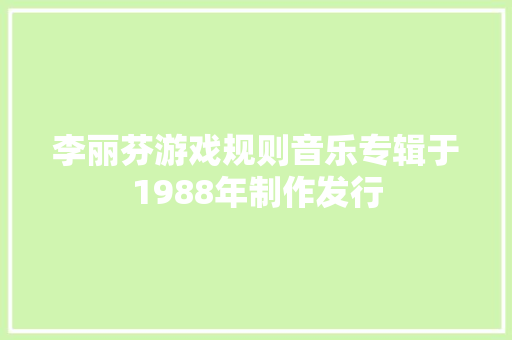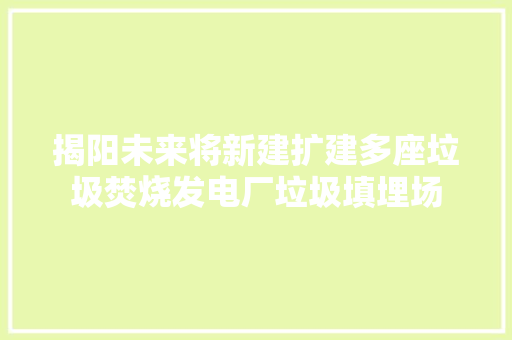陕西大剧《装台》
在央视1套正式收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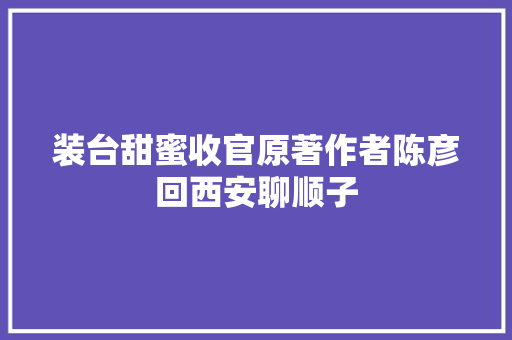
播出期间
无论是屡次创下的收视新高
还是高达8.4分的豆瓣评分
都见证了该剧当之无愧的
2020年荧屏“剧王”地位
当“刁顺子”和“蔡素芬”的故事甜蜜落幕
剧集外
大众对同名小说原著
陕西文学创作的关注热度
仍持续飞腾
18日下午,《装台》原著作者陈彦回到家乡陕西,现身西咸新区文化大讲堂,在诗经里·老舍戏院,带来“统统从生活出发”主题讲座,并首度和乡党、读者面对面互换《装台》戏里戏外,以及关于文学创作的故事。
“装台”背后
是小人物的奋斗、哑忍和韧性
陈彦曾创作《迟开的玫瑰》《大树西迁》《西京故事》《装台》等多部戏剧、文学作品,小说《主角》获茅盾文学奖。但无论哪部作品,他的笔墨每每直面生活在城市里的普通人,展现伟大的时期变迁,“真实”“深刻”“动听”“接地气”“正代价”“正能量”等词汇,险些成了这些作品不雅观后感中的通用语。
由于《装台》的大热,“说说装台是怎么回事”成为陈彦这次文学讲座的开场白,他说《装台》的源起,是自己在陕西省戏曲研究院做院永劫,认识了一个小名叫“生生”的普通人朱冬平,“我做院长的时候,当时搞了个活动叫‘西安每天有秦腔’,就意味着戏院要每天翻台,事情量很大,因此雇了大量农人工进行装台事情,这群工人的工头便是生生。由于白天演员们还要彩排,装台只能在当晚不雅观众散场后至越日清晨演员进场前赶工进行,工人们非常辛劳,只有在装台结束和剧院交卸的间隙,就地睡一下子。冬天里,我很多次在晨跑时,瞥见生生他们就蜷缩在剧院院子的暖气井盖上安歇小睡”。
由于当时的办公室窗户正对着后台出入口,陈彦每天看着这群装台人劳碌。在离开戏曲研究院后,他溘然感到装台人的形象和装台画面越来越多、越来越强烈地涌如今自己脑海里,“主角在赢得阵阵掌声的时候,正是幕后人最劳累的时候。舞台那样俏丽的地方,背后到底有多少人做出捐躯和奉献,我特殊想把他们展示出来。他们的奋斗、哑忍、韧性,都是我们中华民族非常须要的一种精神”。陈彦说,写《装台》,也和自己的此前一部作品《西京故事》有关——《西京故事》同样写了一群农人工的故事,“写得意犹未尽,我以为彷佛自己当时脑筋里边还有一种新的认知,还须要连续书写”。
用笔墨向所有伟大的普通人行瞩目礼
相对付《装台》原著,电视剧版《装台》更为妖冶和轻松,陈彦认为,这是由于两种艺术载体的表达办法和受众不同,他同样非常喜好电视剧的改编,“改编得很温暖,改得很好,我深深敬仰”。陈彦说:“除了《装台》,我还写过一部小说《主角》,其实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每个人都是装台人,我们每个人也都在舞台上唱过主角或正唱着主角。我希望通过小说,让大家能更多去关注那些伟大的普通父母、普通老百姓,我们该当给所有伟大的普通人行瞩目礼。”
在陈彦看来,文学须要书写史诗、赞颂英雄,同样也需有一种巨大的悲悯情怀,“从天下到中国的文学、戏剧创作都有一个特点,早期起步都写的是英雄神话、英雄悲剧,但逐步的,文学创作视角开始转向关注普通人。比如西方文学作品里,雨果的《悲惨天下》里冉·阿让这个小人物,在那么悲苦的人生中,仍闪耀人性光辉,还有《巴黎圣母院》,都是对小人物最深切的关注;中国文学作品中,《水浒传》《儒林外传》《红楼梦》等,都开始关注底层人物的生活、命运。天下文学与中国文学都是共通的,须要这种书写,这是一个巨大的群体”。
“凡能长久存活者,一定带着民间视角,带着浓浓泥土与灶火气”,陈彦如此说。鲜为人知的是,为了写好自己作品中的农人工群体,在陕期间,陈彦除了和装台人们成了朋友,同样在本职事情之外,穿梭在木塔寨、东八里村落、西八里村落等农人工生活聚拢地,“我认识了靠打饼20多年把三个子女都养活成大学生的农人工夫妇,也在流动劳务市场里见到过远方亲戚,这些普通人在城市培植、市民生活中无法缺失落,但他们每每是在无数的隔挡板之后,奔波在风霜雪雨中,在终极非常美的场景之下,他们却悄然拜别”。
陈彦因此感慨,这里有很多东西值得作家们,乃至更多文艺事情者去思考,“我们的笔触和眼力不能每天都朝着光鲜,而把这些忽略掉。现实生活给我们供应了广阔的素材,什么是个中能让民气灵能震颤的?”
“根性”的东西
永久在民间在脚下的泥土中
电视剧《装台》热播,引发热议的不仅有故事和演员演技,同样有个中极具西安特色的满满烟火气。陈彦在西安生活几十年,剧作家创造生活的锐利视角和耐久的文学积累,酿出这部作品别具一格的风味。“我为什么要写这个故事,这群小人物,由于这是我最熟习的,几十年和舞台打交道,我‘拿得住’。作家要写熟习的生活,你熟习了,被打动了,自然会去写,也才有打动别人的可能”。
陈彦认为,一个地域的作家一定有一个地域对其的授予,“然后你该当用这种授予,去反哺你的艺术创作,在放开眼界的同时,也不要忘却深深扎基本身的地皮。陕西这块文艺厚土上,让我们更加读懂这句话的意义:《诗经》里有《风》《雅》《颂》三部分,《风》这部分就来自民间;柳青、路遥、陈虔诚、贾平凹……他们笔下的作品,无不都是深入生活的绝佳表示;长安画派提出‘一手伸向传统,一手伸向生活’更淋漓尽致表现出脚下的泥土,对创作的意义”。
陈彦感慨,在这个时期,很多东西在网络上能方便搜索,复制粘贴,“但我认为用脚去丈量生活,仍是作家最主要的书写办法,由于根性的东西永久在民间,在脚下的泥土中”。至于自己,陈彦说,他依然还是希望多推涌实际主义题材作品,“我还会连续写下去,并且仍旧关注小人物的生存状态”。
文/图:西安报业全媒体 孙欢丨编辑:谈密丨审核:韩东辰陈颖丨部分图片来自网络转载请注明出处
来源: 西安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