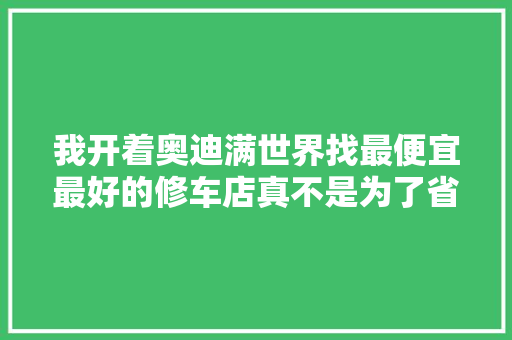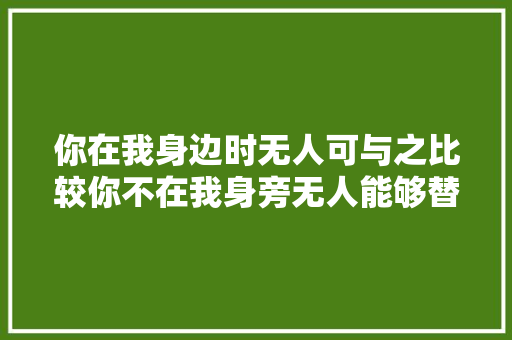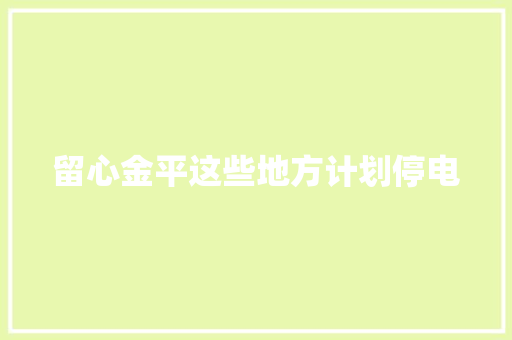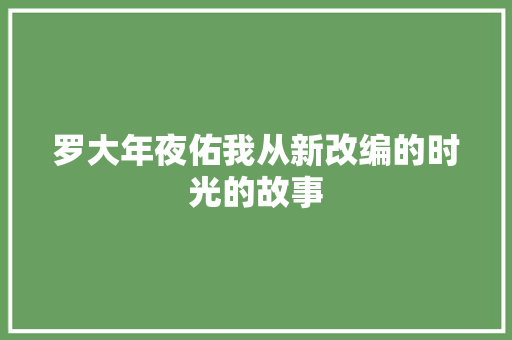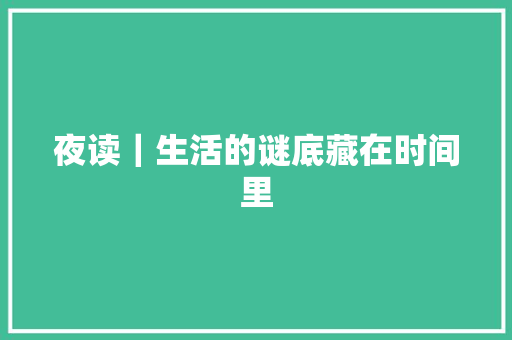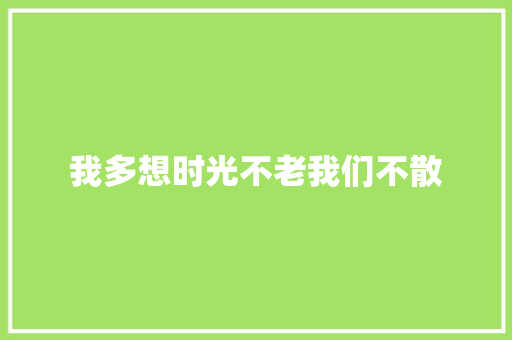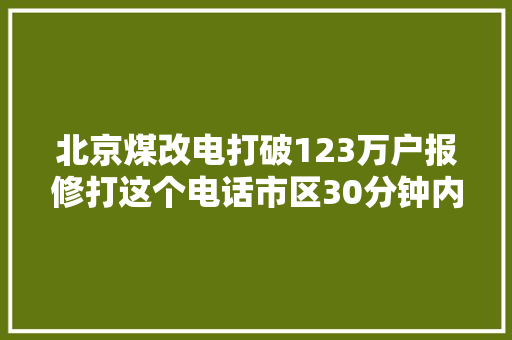我又开始孤独,想起了心中的秘密,我曾经失落去的、深深爱着的他。听凭自己老去也无法解开的秘密须要回到曾经去解开⋯⋯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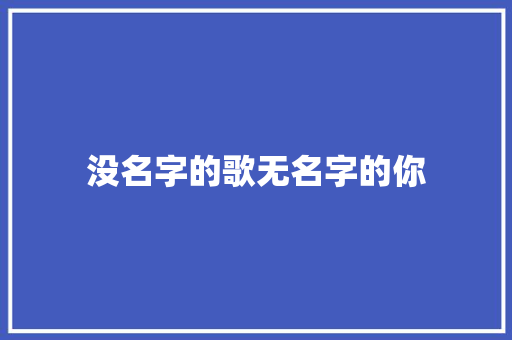
罐头公交是我在南城小镇里的交通工具,它略显矮小的车身涂着大大的绿色汽水DM,像一罐雪碧。酷热夏天里,伫立在公交停靠的间隙,你会听见启开雪碧拉环的奇妙声音,扑哧!
柠檬味的芳香迎面而来,晶晶亮,透心凉。夏天,开了凉气的罐头公交,是我最愉悦的秘密基地,然而秘密指的是另一个他。
白色便携式耳机环抱在耳边,一件淡绿色的休闲西装置着卡其色的拼接九分裤是我的最爱,他的脸我不敢看,朦胧般的对视充满诗意,而我失落忆了。等我醒来,罐头公交已经由站,我错过了自己的站点,“秘密”却坐在了我的身边。我的秘密是他,氧气男生,呼吸都显得愉快。
他总是和我一起并肩坐过十三站就下车,均匀一站六分钟,统共七十八分钟的韶光。我总能断断续续听完手机节目单里的一张CD,由于一张CD的韶光是七十四分钟,而多出的韶光,是我与他互换的空隙。他总是说:“对不起,我要下车了。”而我也只能微笑,说:“感激你借我一只耳机。”
2
卡拉扬是一名如《爆裂鼓手》般的指挥家,也是一个年夜大好人,他定义了一张CD的韶光必须装得下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而我感谢这一首歌的韶光如此漫长,漫长到脉搏已经习气了感情的跳动,漫长到避免了我的尴尬与腼腆,我以为不会有男生喜好我这样普通的女生,而他是我的意外。
“想玩猜歌名的游戏吗?”他出乎猜想的说话声刺激了我所有的感官,我说:“好啊。”
耳机里前奏已经响起,《小苹果》和《最炫民族风》当然难不倒他,但当像《喷鼻香舍丽舍》《梦想家》这样的法语歌和俄语歌,他都能倒背如流的时候,我险些想要尖叫,天呐,我的老伙计,看在上帝的分儿上,我们为什么不找间咖啡馆喝杯咖啡呢?我送他外号Music Man,他说叫他“超耳侠”。他不仅能听声辨曲,还能听见许多迢遥而又细微的声音,比如坐在公交最前头举止娘炮的老男孩,他的男基友正在电话那头叮嘱他一定要穿粉赤色的小内裤,而为什么是粉赤色,超耳侠却闭口不言,直到本日我才明白,粉赤色代表爱情。
3
和超耳侠相处总能碰着许多有趣的小事,比如坐在我们对面的女士,她正表情微醺,眯眼沉浸在耳机音乐里无法自拔。超耳侠打趣地说:“和尚只在我梦里,如果你摸脸又亲亲。猜猜看她听的是什么歌。”“这什么鬼?”我举起拳头想要示威,但却怎么也想不出熟习的歌曲,“还是你说吧。”我无奈地耸耸肩,超耳侠说:“张明敏的《我的中国心》。”“怎么可能?”“怎么不可能!
”我直起腰赌气想下车,却听到对面的女士隐约哼出几句歌词:河山只在我梦里,祖国已多年未亲近。如果你摸脸又亲亲?超耳侠已经笑得满地打滚。
我亲了他,我们恋爱了。
4
和所有的情侣一样,我们在闹市区的街道里牵手,在粉刷了赤色油漆的电话亭里拥抱接吻。电影院的黑,让统统更显得神秘而猖獗,我们坐在公园,看夕阳怀抱熙熙攘攘的人群。他舔着在KFC买的蛋筒,我问他:“你叫什么名字?”他说:“有首歌叫‘没名字的歌,无名字的你’。”我问:“谁唱的?”他说:“黎明。”“唱给我听!
”我跺着脚嗔道,活像个撒娇的小媳妇。
爱是没名字的歌
留给这世上无名字的你
就算该当忘却
偏不记得忘却
要让来日你想起
曾拥有那段情怀是多细腻
用我歌中每个细节轻吻着你
⋯⋯⋯⋯
我没因超耳侠没有见告我姓名而生气,反倒以为相互不知道姓名也好,毕竟感情或许太快。我本来就很普通,普通到有些现实,他或许是某个有名音乐制作人也说不定,毕竟娱乐圈的事情本来就充满了隐蔽与秘密。我相信韶光会打败统统,相信他总会见告我的。只是我忽略了韶光每每不等人。我的韶光不多了,父母要去合城生活,而我不得不离开,我决定向他坦白。
5
夏天,开了凉气的罐头公交,是我最愉悦的秘密基地。
我和超耳侠坐在老位置上,他听我说了很多,没有挽留,只是沉着。我以为自己仿佛拥有了超能力,我能听到车厢里人们的呼吸声,虽然本日车厢里坐满了人,但我仍以为冰冷。我哭了出来,呜呜地很眇小的哽咽。
超耳侠看着我,溘然一反常态,大声喊道:“司机停车!
”我以为他要离开我了,想着四周的人,埋开始哭得更凶了,但他却吼道:“司机!
停车!
”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司机没有停车,但车前却溘然燃起一把大火。人们错愕失落措地拥挤着,推搡着,超耳侠踹开了车门,人们蜂拥而出,我被他拽出了火场。我吓得往外奔跑,跑了有二三十米,但当我转头,超耳侠却不在我身后。他说:“车里还有人,我能听到!
”烟雾笼罩了罐头公交车,我看不清楚人影,逃出来的人们相互拥抱着,脸上露出了恐怖的神色。超耳侠没有回来,公交车燃烧殆尽。
一场事件,受伤三十五人,个中重伤两人,罹难八人。我不知道超耳侠的名字,我再也找不到他了,我和父母去了合城。
6
我在合城生活了五六年,找到了一份适宜自己的事情,做幼儿园老师,过着所有普通女孩子该当过的日子。但我没有屈服父母的意愿,和相亲的男人结婚,我嫁给了一个喜好坐循环巴士的男人。我仍旧喜好坐公交车消遣,戴着耳机听着歌,循环在陌生的城市里。有个男人坐在我的前面,他微胖的肚子出卖了他翘翘的屁股,一条粉赤色的内裤羞涩地露出了笑颜,我嫁给了他,去了他的老家。
就这样沉着地生活,五年,十年,十五年⋯⋯日子过得飞快,在一个安静的晌午,我和孩子们望着满脸皱纹的他在摇椅上安详睡去,再也没有醒来。我又开始孤独,想起了心中的秘密,我曾经失落去的、深深爱着的他。听凭自己老去也无法解开的秘密须要回到曾经去解开。我独自一个人又搬回到了南城。
超耳侠或许没有去世。我在超耳侠的小镇里心满意足地住了三年,五年,七年。待在满是罐头公交的小镇里期盼黎明。
我戴着耳机坐在老位置上听着歌:
就算该当忘却
偏不记得忘却
要让来日你想起
曾拥有那段情怀是多细腻
仿似是全没痕迹一段传奇
但偷偷冲动你
⋯⋯⋯⋯
扑哧!
伫立在公交停靠的间隙,我听见启开雪碧拉环的奇妙声音,柠檬味的芳香迎面而来,晶晶亮,透心凉。夏天,开了凉气的罐头公交是我最愉悦的秘密基地,然而秘密指的是另一个他。
白色便携式耳机环抱在耳边,一件淡绿色的休闲西装置着卡其色的拼接九分裤是我的最爱,他的脸我不敢看,朦胧般的对视充
满诗意,而我失落忆了。等到我醒来,罐头公交已经由站,我错过了自己的站点,一个同样满面皱纹的男人却坐在了我的身边,我的秘密是他,氧气男人,呼吸都显得愉快。
“谁在乎歌声背后曾爱过的你,仍渴望歌中每节都可抱紧你。”
他对我说:“你听的是《没名字的歌,无名字的你》。”
(此文摘自捌匹马作品 《咦,你彷佛喜好我》,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