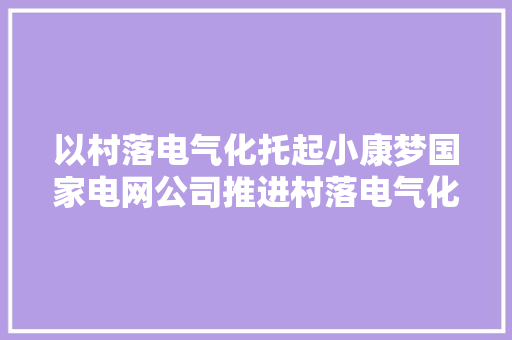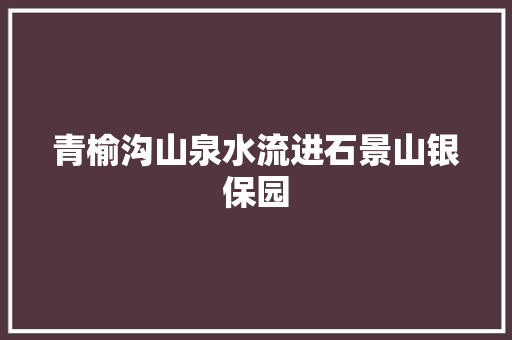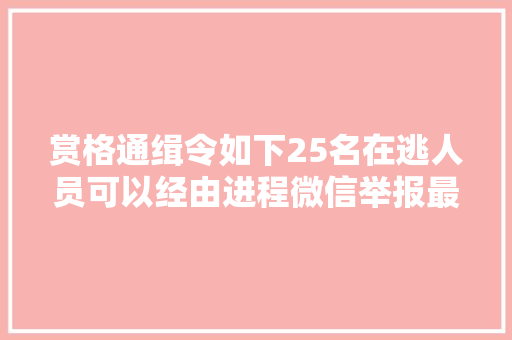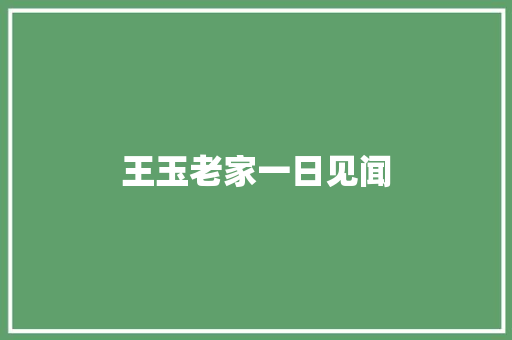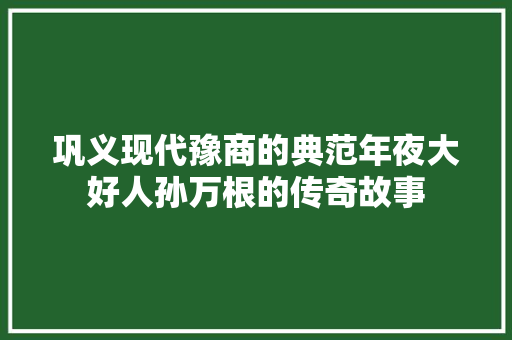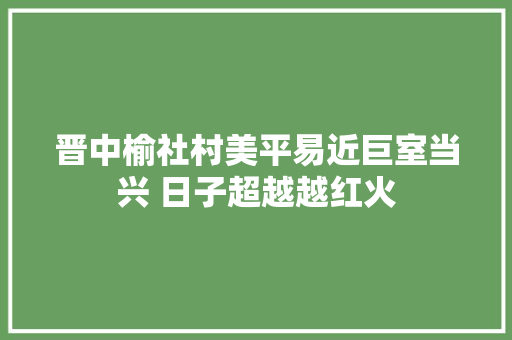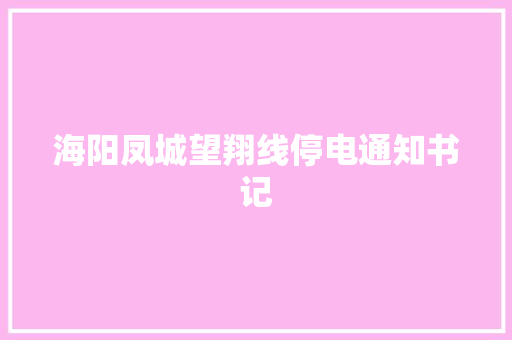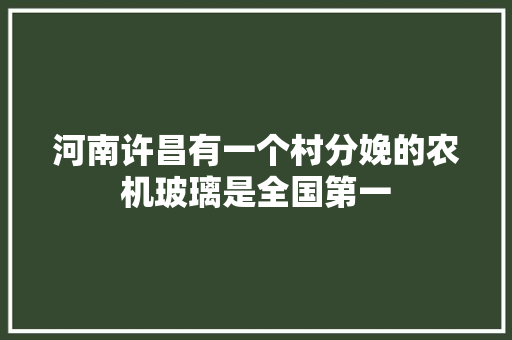12月9日,从木里县城出发,一起颠簸十个多小时,终于抵达木里县俄亚乡俄亚大村落,这里是云南省宁蒗县、玉龙县、喷鼻香格里拉市和四川省稻城县、木里县5地交界处。
远了望去,鹅卵石“堆砌”的村落落犹如一座巨大的蜂窝,隐伏于龙达河边。带路的同道见告我们,这座村落庄已经有400多年历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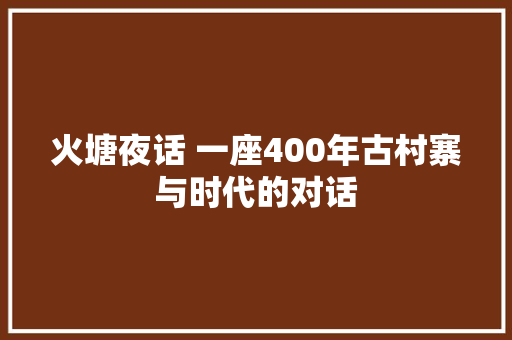
入夜,村落野寂静,循着村落里那边那里最亮的灯光,我们拐进一座名为“东巴堆栈”的院落。堆栈主人东巴本地和妻子东巴基玛激情亲切接待了我们。
一线故事
谈论
一座堆栈起起落落的买卖经
●对付现状,妻子显然还不算满意,她随手扔下手上两只正在拔毛的鸡,嘟囔了一句
堆栈门口,挂着东巴笔墨雕刻的木质门牌——这是在随后一天的采访中,我们在村落里唯一能够寻到的关于东巴文化的笔墨符号。
更多纳西族人的印记,则渗透在俄亚大村落人的衣食住行里,比如火塘。
男主人东巴本地端着一盘当地盛产的“丑橘子”,把我们迎到火塘边坐下。村落支书呷若、第一布告丰子虎已经期待在这里——他们当天的一项主要任务,是和东巴一家商量堆栈后续经营的事。
俄亚大村落位于喷鼻香格里拉环线,与有名于世的稻城亚丁、泸沽湖、丽江古城的间隔皆不敷200公里,自古以来便是行旅、贩子、马帮歇脚的驿站。东巴本地说,已经记不清自家从哪一代开始接待过往客人,但真正开堆栈还是20多年前的事。
从一两间客房到现在两楼一底的院落,“东巴堆栈”越做越大。“我们是第一家开的,也是现在客房数量最多的。”东巴本地用有些拗口的普通话自满地说,这几年扶贫政策好,自己修屋子改造屋子都没有给太多钱。但对付现状,妻子显然还不算满意,她随手扔下手上两只正在拔毛的鸡,嘟囔了一句,“屋子倒是好,但最近连个客人都没有。”
一年中有大半年都没什么客人,这也是最近几年让呷若、丰子虎有些头疼的事。几百年来,只管地处大喷鼻香格里拉交通要道,但眼瞅着稻城亚丁、丽江古城名气越来越大,俄亚大村落却始终没能吃上旅游这碗“饭”:去年,全村落人均纯收入6000元,紧张还是依赖栽种、养殖和外出务工,旅游收入险些可以忽略不计。
回顾
一场持续一个月的困难拉锯
●“每天开一次会,开了整整一个月,末了不明晰之。”忆及此,呷若无奈地拨了拨火塘里的木柴
俄亚大村落不是没有资源:除了地理位置,这里还被认为是东巴文化保留最完全的地域之一,有“丽江看古城、俄亚看古寨”之说,全村落200多户房屋依山而建,连为一体、自成蜂窝状的奇特布局,被列为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俄亚大村落也不是不想发展旅游:脱贫攻坚以来,当地陆续投入1500多万元,完成村落内步辇儿道及排污举动步伐改造,大街小巷全部铺设石板,老旧实木构造房屋全部进行抛光,并涂上清光漆进行保护。“便是为了哪一天也能发展旅游。”然而,让村落支书呷若没有想到的是,旅游的想法还没开始,就被“扼杀”在摇篮里。
那是持续一个月的困难拉锯。村落里的最初想法,是把大村落居民全部易地迁居到附近区域,全体大村落腾出来交由外来投资者进行整体开拓。“每天开一次会,开了整整一个月,末了不明晰之。”忆及此,呷若无奈地拨了拨火塘里的木柴。
“搬出去,我们的文化就没了。”东巴本地承认,自己也是持反对见地的人之一。
东巴基玛记得,丽江刚发展旅游那会儿,很多外地人跑到村落里收购老物件,“有点年代的窗户板都被买走了。”她有些懊恼,自家门口的那块木招派司样去年堆栈改造时才新挂上去的。
期待
一个追逐“见世面”的操持
●对付提升做事品相,东巴基玛对堆栈进行了第一步“数字化”打造——在各个消费场景都放上“支付二维码”;所有客房WiFi全覆盖
一方面怕外来人打扰村落里的安宁,另一方面却又期待更多外地人到来。
在东巴本地的影象里,有两件事特殊值得一说。一是环喷鼻香格里拉公路修通,两车道的柏油路让村落里一下子热闹起来,“以前松茸二三十块钱一公斤都没人买,现在都卖两三百了,自己想吃都吃不到。”另一件事是去年县里组织的一次稽核,他作为稽核团成员去了上海、杭州学习开办民宿,“别的不说,人家房间干净得很咧!”东巴本地瞥了一眼正在一旁打理鸡内脏的妻子,提醒她睡觉前把垃圾提到房间表面去。
东巴本地的操持是不才一步堆栈改造时,把所有房间都贴上木条,“我看表面民宿都这么干,看起来干净,原生态。最好咱们附近几个村落还能连起来,大家一起搞旅游,不然客人来坐一下子就走了。”
呷若和丰子虎遗憾的是,没有像东巴本地一样去过表面“见世面”,就连最近的丽江也没有去过。但是对付如何发展村落里的旅游,他们也有自己的想法:一是保护好当地传统,二是提升做事品相。
保护传统从保护全村落14户东巴开始,每位东巴都是当地歌、经、书、画、占卜、敬拜文化的传承者。作为个中一员,瓦古向展示了一段婚嫁祈福的“经诵”。
对付提升做事品相,东巴基玛对堆栈进行了第一步“数字化”打造——在各个消费场景都放上“支付二维码”;所有客房WiFi全覆盖。“我还打算拍一些照片传到网上。”她说。
“表面都在说‘体验式’消费,我们的特色农产品、纳西文化,也可以体验……”聊到愉快时,几位主人彷佛已经忘却客人存在,用纳西语互换起来。
手记
说普通话的孩子们
12月10日一大早,我们在村落里碰着的第一位小村落民,是5岁的扎西卓玛。
沿着石板台阶,小姑娘一起蹦蹦跳跳跑到我们跟前,“我家在杀猪,去吃猪肉好吗?”用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小姑娘迫切地问,“去吗?现在就去好吗?”
再过两天便是当地的新年。俄亚大村落的这一天,是在家家户户杀年猪的热闹中开始的。大人们忙着做猪膘肉,放假在家的小朋友则忙着打下手。10岁的生根杜基和9岁的甲吉的紧张任务,是打扫村落头拱桥边的石梯——村落里的扶贫公益事情,他们家也承担了一些。
十几级台阶打扫下来,生根杜基脸颊已经微微泛红,“20多分钟就能扫完,这样你们就不用踩到脏东西了!”会说普通话的孩子有时候也充当父母的小翻译,碰着外来客人,他们比父母少了一丝羞涩,落落大方,侃侃而谈。
孩子们说,普通话是在河对岸的俄亚中央校和幼儿园学的。那是全村落最俊秀显眼的建筑,几栋几层的白色楼房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当年我上学,须要骑马一个星期去学校。”呷若说,现在村落里的孩子上学很近。
很近,也是俄亚大村落的孩子与未来天下的间隔。
□四川日报全媒体 谭江琦 胡敏 唐泽文 王云 侯冲
来源: 公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