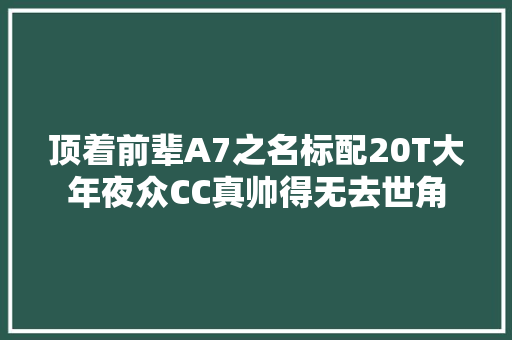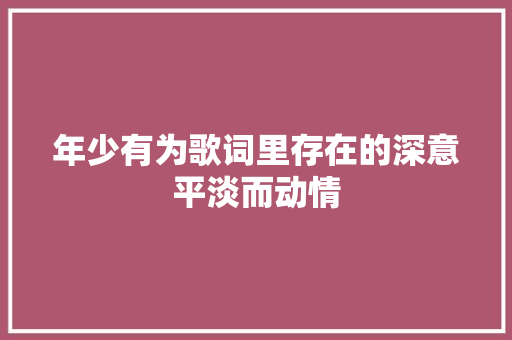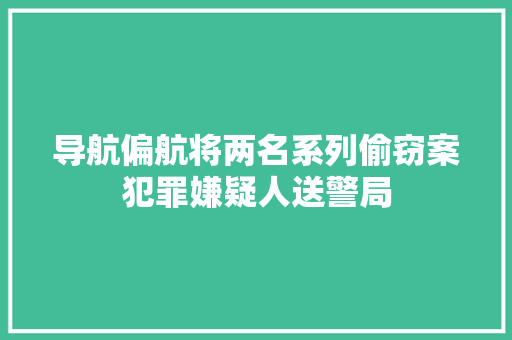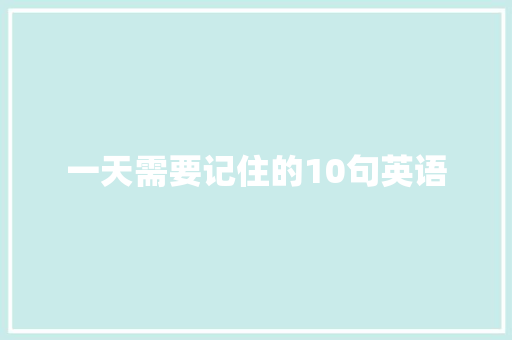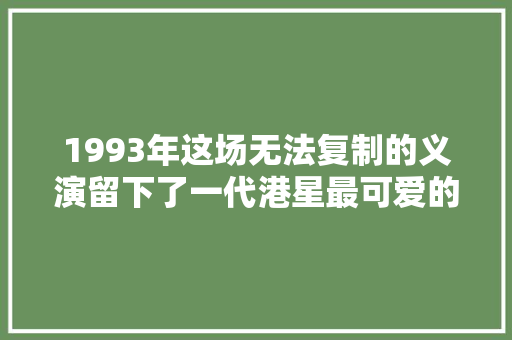第一次听到《鹿港小镇》是在大学一年级,那个时候轰轰烈烈的城市化还没有开始。中国城市里的样子和屯子虽有差别,但不大,有些地方乃至过去一百年来都没怎么变过。便是在这样的环境里,我第一次从他的几首歌曲,如《超级市民》、《未来的主人翁》,当然这首《鹿港小镇》里听到发生在海峡那一边的城市化:
歌词中说的是一个来自鹿港的青年在台北这个大城市中事情,找不到心灵归宿,但又不愿回去、或回不去家乡的感想熏染。作为不雅观察者的罗大佑师长西席感叹道:\公众家乡的人们得到了他们想要的,却又失落去了他们拥有的\"大众。罗大佑把经济高速发展的城市,通过小镇青年在城市中的彷徨生活,与小镇的变革联系在了一起。

当时只能懂得他唱出的一半——\"大众我家就住在妈祖庙的后面,卖着喷鼻香火的那家小杂货店\"大众,还有\"大众我的家乡没有霓虹灯,鹿港的街道,鹿港的渔村落,妈祖庙里烧喷鼻香的人们\公众。由于对付身在大陆而言,没有霓虹灯的鹿港更靠近我们的现实。他歌唱的\公众鹿港的清晨,鹿港的薄暮\公众也正是我们所经历的清晨与薄暮。而\"大众繁荣的都邑,过渡的小镇,徘徊在文明里的人们”则比较难解,更不要说“台北不是我的家”这一句了。霓虹灯不是挺好吗?大城市不是挺好吗,为什么还说“台北不是我的家”呢,不大懂。只是那时随着反反复复地听和哼唱了无数遍,直到每句歌词都烂熟于胸。却并不知道,未来我们还要目睹歌中唱的事情在现实中发生无数遍。
听不懂的那一半,答案就在歌的末了一段。那当然也是这首歌最神奇的部分。唱完“徘徊在文明里的人们”这末了一句之后,大段电吉他响起,正当听众以为歌曲就要结束时,溘然罗大佑意犹未尽,分开原有的歌曲旋律,叫嚣出罗大佑标志式的长句子—— “啊,听说他们挖走了家乡的红砖砌上了水泥墙,家乡的人们得到他们想要的却又失落去他们拥有的,门上的一块斑驳的木板刻着这么几句话,子子孙孙永葆用,世世代代传喷鼻香火。啊” ——至此,歌曲才算彻底结束。现在看起来,这几句话对后来的大陆而言,险些可以说是一语成谶啊!
但当我在闽南地区大片贴着瓷砖的水泥房的乡间徘徊,探求和创造那些遗留下来的古厝时,那句“他们挖走了家乡的红砖,砌上了水泥墙”不禁就会涌如今耳边,想象着鹿港的红砖大概便是这个样子吧。又或者记得某一年(08年奥运前)忽然听史建和我说赶紧去看看鲜鱼口,说再不去就拆没了时,我赶到时看到的大片废墟里一块块斑驳的木板,\公众门上的一块斑驳的木板刻着这么几句话,子子孙孙永葆用,世世代代传喷鼻香火。\"大众这句歌词就在耳边几次再三重复地响起。三十年前不断哼唱的歌竟然预先唱出了我们面前的现实:水泥房与老红砖还有被拆毁的门板!
台北不是我的家,我的家乡没有霓虹灯,鹿港的清晨,鹿港的薄暮\公众,家乡有来自自然真实的光芒变革,从清晨到薄暮,没有霓虹灯。如此这般的亲切美好却好景不在,由于家乡变得更加“文明”了,拆掉了老屋子的旧红砖,换成了和城里人一样的水泥屋子,却失落去了过去岁月中,每个清晨和薄暮都不变的古老景象。以是说,这是一个“归不到的家园,鹿港的小镇,当年离家的年轻人”。离家的人再也找不到他原来的家乡了。至于先人刻在门板上的“子子孙孙永葆用,世世代代传喷鼻香火”的希望。
我们这一代的发展经历堪称戏剧性,阅读真实天下比书本更须要想象力,荒诞如梦幻泡影。好在有《鹿港小镇》在当年我们这些“离家的年轻人”头脑里反复“预演”,可以时时蹦出来,提醒着碰着现实而手足无措的我们。“台北不是我梦想的黄金天国,都邑里没有当初我的梦想”。城市如此,故乡呢?“在梦里我再度回到鹿港小镇,庙里膜拜的人们依然虔诚”——回去连续卖喷鼻香火么?可是“世世代代传喷鼻香火”还能连续多久?——真是不知道这是回不去的无奈,亦或是回不去的缘故原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