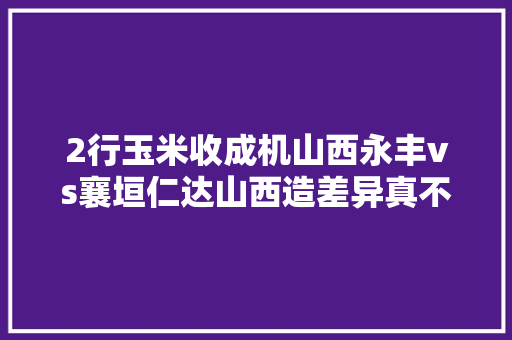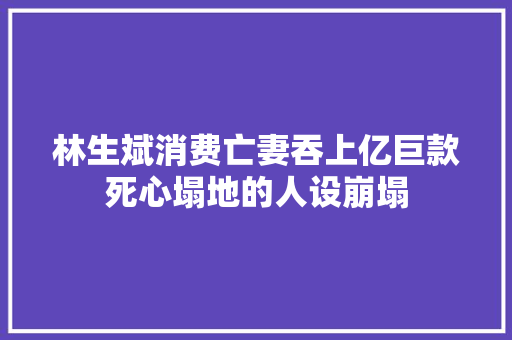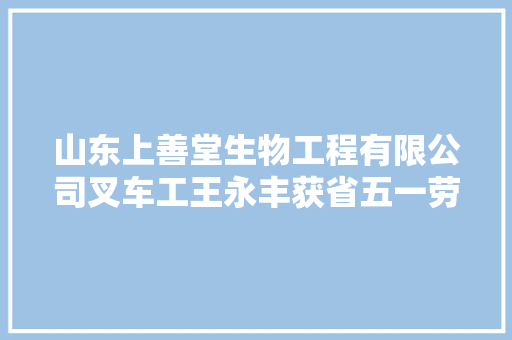2008年1月,客家音乐人林生祥和御用词人钟永丰召开音乐制作会,永丰说要不我们来做一个关于“南方”和“女人”的主题?
2008年2月,他们敲定了“野生”这个名字,林生祥以为这个意象代表着专辑的脉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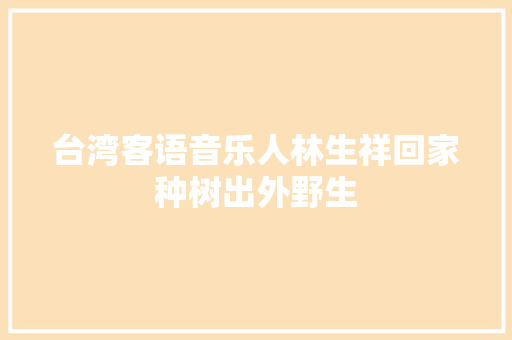
2008年2月尾,创作开始启动,林生祥说,“我们每个月创作两首歌,不要多,也不要少。”
2008年6月,专辑创作全部完成。
2008年7月,林生祥和吉他手大竹研开始录歌。
2009年4月,《野生》专辑在全天下发行。
2009年6月尾,林生祥和大竹研带着“胆大大”的《野生》来到这边南方,巡回演出、讲弹,他说“如果心情一贯流浪,那该怎么办?”
“我在专辑里面讲到女人,讲到我的太太,我的姑姑,讲她们关于心情的流浪。客家女人啊,从一早熟起心情就开始流浪,在家里也流浪,到城市里事情也流浪,这种流浪要随着她们一辈子,就像野生,零零落落地。那怎么办?我把我填好词的歌唱给她们听,我姑姑一贯哭一贯哭,那么我以为啊这个创作最少是深入民气的,有代价的。那样就够了。毕竟关于这个主角的该当不但我姑姑,心情流浪的还有很多人很多人。那他们怎么办?如果我能够用音乐让他们看到自己心情的流浪,纵然还不能拯救,也是好的。”
唱起山歌反叛库
时至今日,林生祥已经不太想回顾当初唱山歌反叛库的日子,“当时《我等就来唱山歌》是1999年,《菊花地夜行军》是2000年,实在才过去了九年旁边,在我看来彷佛已经由去二十多年。”
美浓,原名弥浓,三面环山,南面有一条大河,出生在这里的林生祥是一个看起来斯文的瘦子,戴着眼镜,说话是懦软的台湾腔,若不是知道他之前的统统,谁也不会把社会运动勇士和他联系起来。1993年4月16日,当时的林生祥还在读大二,玩着自己的校园乐队,而他美浓的父老乡亲们已经坐了一夜的巴士,来到台北立法院,用唱山歌开始了轰动的反叛库运动。
实际上林生祥的家就在水库选址最近的地方,唱山歌的人里也有他的母亲,还有之后成为他互助拍档的钟秀梅。
一年后,林生祥回到老家,认识了曾经带着大家一起唱山歌的钟秀梅,也认识了钟秀梅的哥哥,便是后来成为他御用词人的钟永丰。包括钟家兄妹在内,谁都不相信在台北读了大学的林生祥会真正返乡。“美浓的人都习气了年轻人在表面博取功名,而我是真正以为乡下生活的品质比城市要好,我回家收成到的比我能给的要多得多。”
那时的林生祥是一个表面温婉内心激进的音乐手艺人,“我当时希望能将音乐和美学融入反叛库运动之中。”交工乐队因此而生,“交工”即是屯子互帮互助的劳动机制。对付当时的交工乐队,林生祥利用了很多客祖传统乐器,譬如月琴、鼓,客家山歌给予他强大的影响,“人要懂得从自己的传统中得到力量。”1997年,林生祥正式成为一名职业音乐人。
1998年,钟永丰给了林生祥第一首词,《夜行巴士——记一位老农的心情》(《我等就来唱山歌》专辑),1999年,“烟楼录音室”成立,两个月的韶光,《我等就来唱山歌》专辑录制完成,这是一张完备为社会运动做事的专辑,摇滚元素和民俗节奏并存,乃至还用上了西北民歌的唢呐,“水库若建得,屎也吃得”便是林生祥自己写下的歌词,每次唱到这里,所有的乡亲都会心一笑。
十年后,林生祥把那统统归结为由于年轻而燃烧出的激情,“实在那样并不能影响到更多的人,能量完备没有办法扩散出去。”
抓到成熟音乐的尾巴
在上世纪90年代台湾民众音乐的发展史上,林生祥的交工乐队被许多乐评人认为是“标的台湾新音乐创作时期里程碑的音乐军队”。《我等就来唱山歌》、《菊花地夜行军》掀起了台湾民众音乐的风潮,然而第三张专辑还未出,交工乐队便因方向不同而终结,这也发布着一个时期的结束。
用马世芳的话来说,乐迷们还没有喘息过来,林生祥很快便制作出“后交工时期”的《临暗》,以及后来加倍大气的《种树》,和之前比较,2007年轰动一时的《种树》没有了之前那么明火实枪的战斗感,虽然反响的生态问题愈发根深蒂固,但林生祥开始了学会做减法,开始是减掉了当时在独立音乐圈能够鹤立鸡群的打击乐器,后来把月琴等民俗乐器完备摒弃,只和大竹研用两把木吉他在台上弹拨。音乐体例越来越简约,他们的音乐却越来越成熟和大气,到了2008年初来到广东南岭《种树》时,他终于承认自己的音乐抓到了一点成熟音乐的尾巴。
“我和永丰繁复谈论,我们希望用大略精髓精辟的篇幅换来最广阔的音乐空间。《种树》是成熟的开始,而到了今年的《野生》,无论从节奏、音乐,还是视觉呈现,我以为这是目前我最成功的一张专辑。”林生祥试图用一种简约的办法实现丰富的细节和表达力,钟永丰也是一样,《野生》的五言,《转妹家》的四言,以及《木棉花》的三言里,我们都可以感想熏染到来自诗经、汉唐乐府和客祖传统音乐相结合的新的音乐力量。
现在,从事职业音乐创作12年的林生祥依旧生活在他喜好的美浓小镇,定期,他都会去母亲的猪舍帮忙干农活,闲时便陪女儿或者打乒乓球,“乡下多好,不用考虑停车位,不用堵车,开车30分钟便可以去高雄看场挺不错的电影。”
对
话
措辞不能凌驾于音乐之上
东莞时报:当初《野生》选择女性做主题会不会担心男性视角的问题?
林生祥:记得那个时候永丰见告我的时候,我也吓了一跳,我说永丰,从生理上讲,我们都是男人,会不会有问题。但后来我想通了,实在男性可以拥有女性的不雅观点,女性也可以拥有男性的不雅观点,我不雅观察到的自己有一方面靠近女性的特质,我的家族成员也有女性靠近男性的,于是我以为这个角度没有问题,就看怎么写。
东莞时报:这个角度?
林生祥:便是说,对我来讲,这次的题材比较生活性,我没有办法替女性说哀求什么,大概只能是为一些征象找答案。里面包括了生命进程里和女性发生的跟女性干系的故事。之前说过的我的姑姑,我和我太太,还有我的姑婆,还有永丰的妹妹、老朋友秀梅,都是这次的主角。
东莞时报:个中《转妹家》很特殊,四言的诗经体,其余去世亡的议题彷佛很少见。
林生祥:《转妹家》意思便是回外家,“看到暗暗,毋好行兼看到有光,佛祖来揽”,当时看到歌词很震荡,怎么会有人在离世前是想回外家,那她到底有什么样的故事?于是我在作曲的时候就很存心去体会个中的感情。去世亡的议题在汉人音乐中实在很敏感,对付我来说是很陌生的,以是这也是我决定去考试测验的缘故原由,我、须要很大的能量跟歌词对话。
东莞时报:“交工乐队”终结往后,你音乐的演绎办法彷佛变得越来越轻了,这次的《野生》尤甚,但反响的问题实在挺尖锐的。
林生祥:当时以为音乐参与社会可以做些什么。后来逐渐创造,真正参与运动的人的影响没有办法扩散出去,让更多人来理解。我就思考,如果我们真的要改变什么,我们到底该当怎么做。
而个中,期望最大的改变,实在是根植于普罗大众的生活代价不雅观,这种改变一旦形成了,到某个时候,她们就会做出一个社会性的大改变。于是现在我想事情,就不会局限于两年或者一年的成果,而是今后看十年,乃至二十年来思考这件事情。譬如种树,当时我就以为种树对付生活的代价生命的代价是一件主要的事情,以是我就做了种树干系系列的作品,这次谈到的女性的主题对付我来说也是一件主要的事情。今后十年或者二十年,我们可能改变统统。
或者换种说法是,我以为我这一代没办法办理的事情,我要关注下一代。这是一种局限感,也是一种策略。
东莞时报:实在对付乐器的选择,你们也越来越大略了。
林生祥:现在我和大竹研便是两把木吉他和一把口琴。交工终结往后,我实在感想熏染到了自己在音乐上的不敷,节奏感很缺少。我们的民族没有强壮的节奏文化和舞蹈文化,只有旋律文化。于是在2006年我跟随来自日本的大竹研和安然隆学习节奏,我要办理一些身体内部的局限,我要先启动自己的能力。
东莞时报:那现在节奏感满意了吗?
林生祥:实在这张做完,我就以为韶光差不多了,也到了我是时候捡起传统乐器的时候了。今年下半年,我会重新启动一个月琴的改造操持,两条弦变成三条弦,会有一个新的音乐纪元也说不定。
东莞时报:还是会坚持用客家语演唱吗?
林生祥:不是坚持不坚持的问题,只是说有没有办法表达准确,有没有办法自然地表达。就像我拒领金曲奖,为什么奖项划分要用措辞呢?措辞不应该凌驾于音乐之上,它不是划分媒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