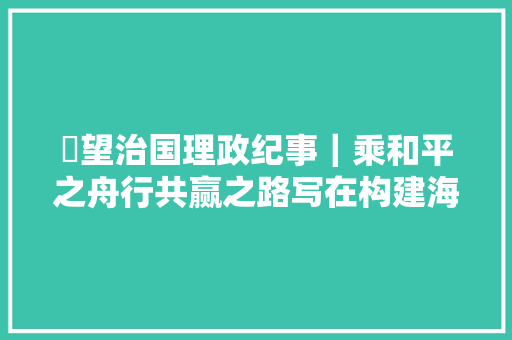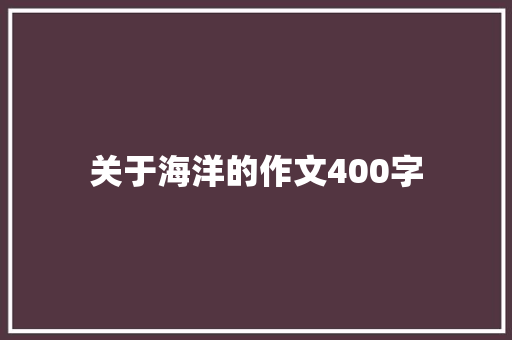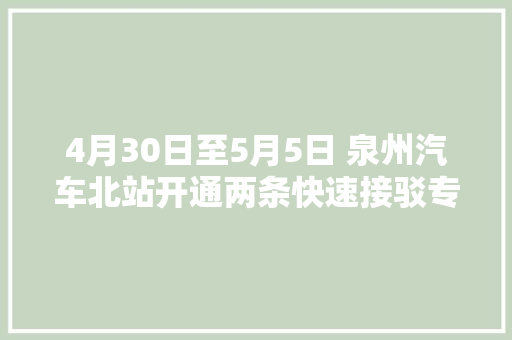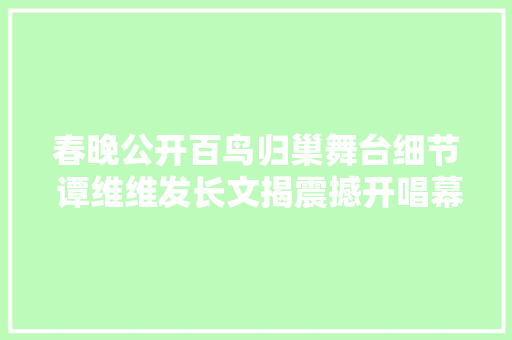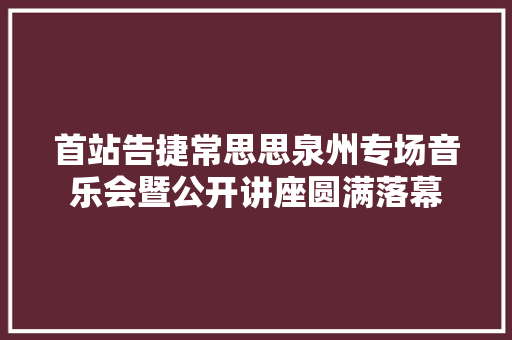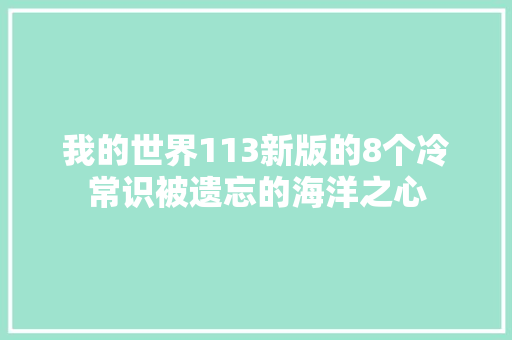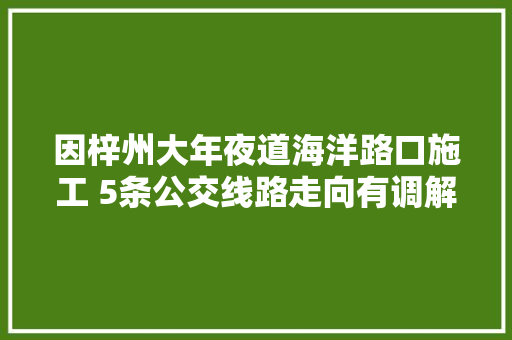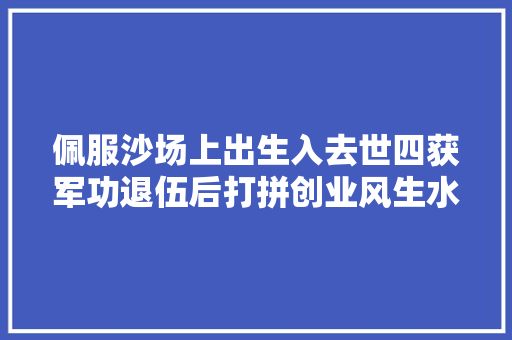从空中鸟瞰泉州市区,泉州城西路像一张“弓”,西街的西段则如搭弓待射的箭。这里是泉州历史文化名城的核心区,周边布满文物和遗产建筑。 (图片来源:《泉州》)
2022年7月13日,清晨的蟳埔村落黄氏宗祠前,村落民正在撬海蛎。 蟳埔村落位于泉州晋江入海口处。这里出产的海蛎极其有名,新修的祠堂仍旧采取了蚝壳厝元素。祠堂上“紫云衍派”的门楣,闽南人一看便知指的是捐地修开元寺的黄守恭后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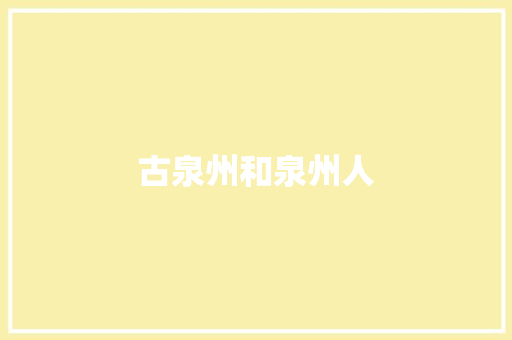
2022年7月,泉州申遗成功一周年到来之际,参加国学夏令营的中学生正在排队进入泉州天后宫遗产点参不雅观。
泉州天后宫内,喷鼻香客祭拜的风尚依然延续下来。天后宫是表示天下海洋贸易中央管理保障的代表性遗产要素,表示出民间崇奉与国家意志相结合对海洋贸易发展的共同推动浸染。泉州天后宫的建筑规格高于湄洲祖庙。
1974年,在泉州湾后渚港出土了一艘宋代建造的远洋货船。考古人员从船上创造了喷鼻香料药物、木货牌(签)、铜钱、陶瓷器、竹木藤器、果核(壳)、贝壳、动物骨骼等14类文物。这是我国迄今为止创造由外洋返航并已出土的唯一一艘古代远洋海船。 (图片来源: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
“船”在泉州历史文化中霸占主要地位。2008年7月,在泉州石狮祥芝镇斗美宫展出一艘“迷你”王船。“送王船”是闽南地区一种祈求安然、赶走瘟疫的仪式,与福船造型险些千篇一律。完成仪式后,王船会被送入大海或在海边点火。“送王船”仪式随着闽南人的脚步传到东南亚和日本长崎,2020年景为天下非物质文化遗产。
日本长崎的福建会馆始建于1868年。会馆内的天后堂,也供奉着妈祖。
这是泉州开元寺大雄宝殿后侧的印度教石柱。明末泉州湾经历了一次大地震,大雄宝殿重修时采取了一些当时已经倾颓的印度教寺石构件。
中国拥有悠久的海洋文明与文化。
2021年7月,“泉州:宋元天下海洋商贸中央”列入《天下遗产名录》,作为亚洲海洋贸易网络东端引擎型港口的精彩范例,展现了公元10至14世纪亚洲海洋贸易的高度繁荣景象。
成为天下遗产地后,人们从更宏不雅观的视角不雅观察这座“活着”的古城。这里不仅是有名的侨乡,而且是无数华人外洋拓展形成的“流动的社区”中央,是“海上丝绸之路”中的一个特色组成部分。
泉州是我的家乡。
我的曾祖父年轻时随着曾曾祖父去了印尼的泗水。祖父年轻时,也曾差点被送往泗水投奔伯父,学做生意,但是适逢台湾光复,祖父还是选择去台湾当老师,后来又分缘际会回到泉州连续做中学历史老师。几十年后,我跟祖父一样学了历史,在写博士论文时翻阅泉州南安石井郑氏资料,看到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在18岁时候便去喷鼻香山澳(即澳门)投奔舅舅黄程,便略有似曾相识之感——在少年时踏上一条跨海越洋的谋生之路,这大约是数百年来无数泉州人的必由之途。在泉州出身的这种生存办法,远比其他侨乡更加久远和稳定。
从泉州成为中国南部沿海要港起,泉州的历史就不再是单单发生在本地的历史。从明清开始,泉州人在外洋活动的人数与范围越来越多,这些游子与故乡的联系仍旧密切,未曾断绝。家族的成员,可能越洋再造家族;原来所具有的社会关系、社会资源也会延伸到外洋。因此,那些发生在外洋的人和事,亦是泉州历史的一部分。
到清朝中晚期,泉州人已经可分为住在原地和住在外洋两部分。外洋泉州人数量虽然相称可不雅观,形成的外洋社区不断流动,但他们的社会、经济生活却是与泉州本地连在一起的。近代泉州的公共生活实际上该当算上他们的一份。泉州的历史如果没有他们,就不是完全的。
“海者,闽人之田也”。泉州海洋传统的形成,取决于泉州人的生存模式和闽越族裔的历史秘闻。
泉州与海相伴生的往昔与主动拥抱海洋确当世,正是中国东南地区海洋文明的缩影。
福建省拥有3752公里的海岸线。每年春夏,西南季风从印度洋和南中国海吹来,秋冬时令东北季风则往南吹;北上的黑潮和南下的岸流能助沿着海岸线航行的船只一臂之力。于是处在东海与南海交界处的福建就成了一个绝好的海上运输中转地。早在东汉,来自中南半岛上交趾七郡的贡品,即从海道经由福州转运至北方。
福建北部绵延的武夷山脉不仅阻挡了冬季南下的寒风,给泉州留下“温陵”的雅号,也阻碍了从陆路北上中原腹地的脚步。向西向北,是绵延起伏的丘陵山地,向东向南则是广阔无垠的大海,只要有船,想去哪儿就可以去哪儿。泉州漫长而弯曲的海岸线上分布着“三湾十二港”。明代福建水手们利用的航海针路簿《顺风相送》既记载了从福建到东亚、东南亚各国的航道,也记载了菲律宾与日本之间、东南亚各国之间的航道。如果说在亚欧大陆上,机动性最强的族群是游牧民族,那么在大海上,机动性最强的族群便是海洋民族。
泉州最初的海洋传统来自于后世常被称作“疍民”的闽越族。《山海经·海内南经》说“闽在海中”。明弘治年间的《八闽通志》引用旧志记载:“闽之先居海岛有七种”。福建的土著族群,是“以船为车,以楫为马”的百越岛夷。闽越遗裔给福建留下了无法磨灭的海洋文明传统。他们是中国周边海疆最精良的水手,西晋《吴都赋》就有“篙工檝师选自闽、禺(番禺)”的辞句;他们是出色的造船工,两宋时有着水密隔舱和强抗风浪能力的福船超越了阿拉伯海船,还是日后郑和宝船的原型;他们也是卓越的冒险家,早在唐开元八年,泉州就有航海家林銮“试航至渤泥(即文莱),往来有利。沿海畲家人俱从之往,引来番舟”,至今留下了著名的“林銮渡”;他们后来还是海岸线的护卫者,明朝以沿海卫所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海防体系时,曾“招岛人、蛋户、贾竖、渔丁为兵”,让部分疍民上岸成为卫所驻军。泉州港在宋元的崛起与其后海洋传统的延续,闽越遗裔功不可没。
泉州拥有适宜海上活动的自然条件,同时又是一个不适于农业的地区,生活在这块地皮上的公民必须迈向海洋,才能生存发展。
两晋至唐宋“衣冠南渡”的农业移民则是泉州平原的紧张开拓者,他们带来前辈的农业技能,建筑了大量的水利工程,使这个曾经的南蛮烟瘴之地,能够为外洋贸易生产充足的商品。
今日泉州古城的核心区域,至汉代仍有一部分泡在水下。这里是晋江入海口,咸水与淡水交汇。南下的北方农业移民在泉州选择的第一个定居点是更加上游处的丰州九日山下。除了鳄鱼与毒蛇之外,贫瘠的地皮与不断侵袭的海潮是农业移民面临的最大寻衅。
泉州沿海平原保存下来为数浩瀚的明清族谱,这些族谱每每用“硗确”来形容本地土壤之瘠薄。仅从字首偏旁,人们也能感想熏染到这片仅有345平方公里的平原,坐拥福建省第四大河流,却无缘成为肥沃的三角洲。不仅如此,携带着盐卤的海潮还时时时涌入先民筚路蓝缕开垦的田地。一次天文大潮,就可能将费力劳作的成果子虚乌有。为了积蓄细流与雨水以灌溉冲刷斥卤的田地,由唐至宋,晋江沿海平原共建筑了125处埭田,与海争地。但是人口的增长速率,仍旧超过了泉州平原农业产出的承载能力。北宋元丰年间,泉州与福州并列福建人口最稠密的地区,南宋时仅泉州城内便号称有“生齿50万”,当地已经损失了粮食自给的能力,须要从域外调运。为了生活,农业移民学习了本地居民的滩涂养殖和近海捕捞,用海产来换取粟米,随后也被卷入了外洋贸易的生产链条。
与对外通商历史悠久的广州港比较,泉州港表面看上去彷佛并无任何上风。但是福建比之广东,却相对开拓得更早、更全面。全体北宋年间,福建登科的进士人数是广东的十多倍,这在一定程度上反响了经济发展水平。泉州及其腹地为了外洋贸易而生产多种商品,但对付广州港来说,有许多则需从外省调运才能得到,这无疑加大了广州港的贸易本钱。在泉州,为了适应海洋生存模式,栽种粮食的地皮改为栽种经济作物,比如荔枝、龙眼、茶叶、甘蔗和木棉;烧瓷的窑址遍布了海边与山区,宋元泉州窑址的密集程度堪比浙江龙泉和江西景德镇。出使真腊(即柬埔寨)的元朝青鸟使周达不雅观也在当时真腊都城吴哥见到了泉州出产的青瓷。同时,有利于水陆转运的桥梁也被大量建筑。有宋一代,福州共造桥18座,泉州却建造了115座,仅平原核心地带的晋江县就建了43座桥梁。
海洋生存模式造就了泉州的海洋传统。在外洋贸易不受国家限定的时候,海洋商业传统得以发展和深化。
公元1087年,北宋朝廷在泉州设立市舶司,泉州刺桐港步入了她的黄金时期。在一副绘于1375年的《加泰罗尼亚天下舆图》上,刺桐港被记录为“Zayton”,这是她名扬于天下航海史的名字。在这座城墙内面积乃至超越了首府福州的城市里,来自迢遥异邦的各国贩子居留在“番坊”“聚宝街”,或在摩尼教寺、基督教聂斯托利派的教堂和婆罗门教寺院乃至参加科举。他们在泉州为官做生意,与刺桐城分享顶峰的荣光。经考古创造,一位故里不知何方的阿拉伯人蒲氏,末了以“有宋泉州判院蒲公”的称号,被埋葬在文莱的墓地。更多的阿拉伯贩子后裔,当刺桐港衰落后仍定居在城郊村落庄,与本地人联姻繁衍。明代著名思想家李贽家族的墓道碑上记载的家系,证明了其家族与阿拉伯贩子后裔金氏、蒲氏、丁氏都存在着联姻关系。
刺桐港的黄金时期,加深了泉州地方社会与海洋生存模式的共生关系。地方社会从此习气于商业活动,习气于与异邦人交往领悟;百姓们也习气于生活中时时有远邦的方物或异闻。泉州晋江入海口处的蟳埔村落,除了出产泉州湾最好的海蛎,也同样以蚝壳厝而有名,只是他们所利用的大型牡蛎壳,并非娇小确当地品种,而是来自于迢遥的东非海岸,在数百年前充作压舱石随同福船一起返回泉州港。郑芝龙主持重修开元寺大殿时,用了印度教寺的石构件,摩尼教和印度教的神明则进入了本地崇奉体系,被当作地方神明崇拜。草庵的摩尼光佛和池店兴济亭的湿婆之妻都被百姓当成不雅观音菩萨奉祀。随着明初到访中国的锡兰王室青鸟使定居泉州,犬神毗舍爷也成了铺境庙白耇庙的随祀神,位居主神田都元帅之侧。
海洋传统造就了泉州地域社会的流动性,泉州的历史边界随着其社会成员的脚步而不断向外拓展,形成了遍布外洋的“流动的社区”
在刺桐港衰落后的几百年中,泉州人的足迹遍及中国海和东南亚海疆。来自外洋的财富又支撑了泉州的社会经济。因此宋元往后的泉州并未走向衰落,泉州的海洋传统也并未中断。
明成化八年(公元1472年),福建市舶司由泉州迁往福州,泉州失落去了合法口岸的地位。然而港口并不是泉州海洋传统的核心所在。中国现存最古老的清真寺——泉州清净寺始建于公元1009至1019年,这从一个侧面证明当时泉州已经存在具有一定规模的阿拉伯社群。海洋贸易是形成这些多元社会风貌的条件。“山不来就我,我便去就山”,海洋传统的核心是不畏风浪的流动性。泉州港衰落后,泉州人的海商集团发展起来。他们行走于海内外各处商埠。从长崎到阿瑜陀耶(即现在的泰国大城),都有他们的身影。当时著名的代表人物是郑芝龙,他能够利用多种措辞,生动于福建、澳门、台湾及日本等地。他的儿子郑成功7岁从日本回到泉州的家乡石井镇,后来创立的海陆五商行更是涉及全体中国周边的海疆。
泉州港失落去东方大港地位后五百年间,泉州人用一次次的海上冒险完成了海洋传统的再生。海洋生存模式带来的生活习气和知识体系早已融入了民间生活的方方面面。大海上危险重重,休咎未卜的出息令跨海谋生者每每迷信于神灵的庇佑。泉州人纵横四海的商业网络,也须要一套信用体系去坚持。于是“神灵”就成为了见证人,祭拜神灵就成为悠久的传统。从晚明到清长达一二百年的韶光里,泉州贩子在日本长崎与福州商帮、三江(浙江、江苏、江西)商帮一同轮值主持妈祖祭与掩护悟真寺华人义冢。直至现在,我身边碰着的泉州老太太,可能不识字,或许从未听说“伦敦”“纽约”这样的大城市,但她知道仰光在缅甸、泗水在印尼;虽然她从没学过英文,不知道英文“outside”一词如何读写,但她在玩闽南的四色牌时,如果出了错张,便会懊恼地脱口说“奥赛”。泉州的老一辈人在做早餐时,会很自然地将来自南洋的朱古力条加入鸡蛋燕麦粥中煮做早餐,而这实在是一道经菲律宾中转而来的墨西哥菜。
常常有人说,泉州是一座“活着”的古城,它没有凝固在历史的风尘中,而始终充满着鼓噪的烟火气。虽然昔日市舶司古海关早已变成了奉祀戏神田都元帅的水瑶池境庙,泉州人却把唱南音的“郎君社”搬到了南洋各埠;虽然港口早已不再贸易南岛喷鼻香料,泉州人却把南洋味道加入了牛排和沙茶面。内生于民间文化与生活办法之中的海洋文明,授予了泉州长久的开放与原谅,泉州人也能连续从大海上探求到新的出路,我想这正是这里顽强传承“草根”生命力的最大来源。
蒋 楠: 青年学者,华侨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明清华南社会经济史与华侨史。
(本版照片除署名外均由蒋楠拍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