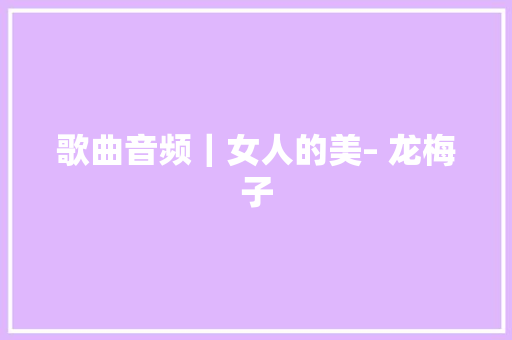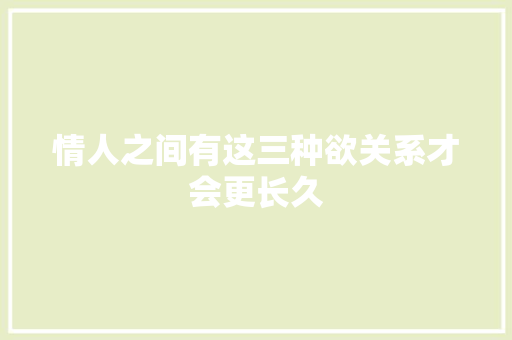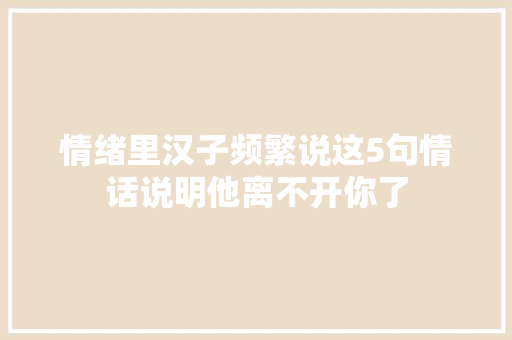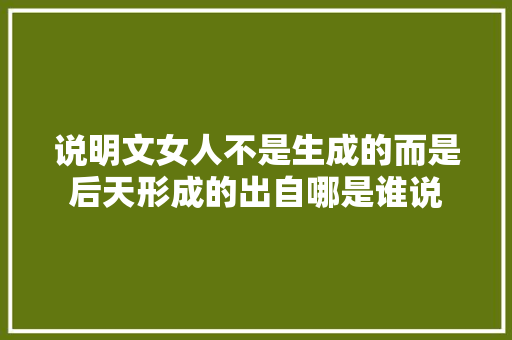01
本日想聊一档旧节目:《半边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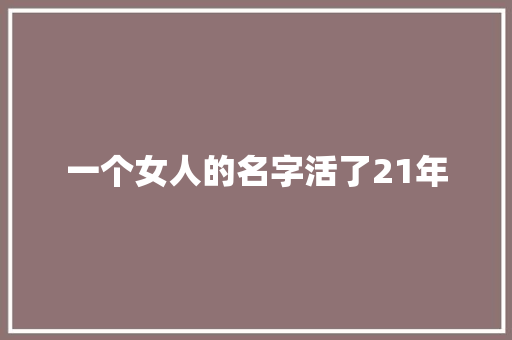
前两天看到主持人张越讲,如果她早碰到余秀华,第一韶光就会约请她去上《半边天》。一下子就把我的影象拉到这档停播的节目上。
事实上,《半边天》可能是少数几个停播了,却仍有很强生命力的节目。
人们一直剪辑重译这档节目,有数百万的播放量。
人们记住了里面的很多名字,尤其是刘小样。
虽然旧节目清晰度不高,但看着那些表述着痛楚的女性面庞,我们还是会忍不住堕泪。
这档开办于「1995 年天下妇女大会」背景下的节目,成了一个分外的标识符号。这也是我本日想要再评论辩论它的缘故原由。
它,和它所拍摄的女性生命力和穿透力如此之强,在本日仍旧会触动我们的心。
1)主持人张越和传统的央视女主持人很不一样,直不雅观上就不一样。她有光鲜的态度。至少我第一次听到一个央视女主持人敢这样说——我们的文化里,对女性是“受害者有罪论”。
2)当下我们评论辩论的绝大多数女性选题,单身女性、家暴、全职妈妈等等,都可以在那里找到源头。
3)它拍的高朋,不是明星,不是成功女性,不是美女。用某期节目里的一个词,是“怪胎”。张越前几天还在节目回顾起她——一个不结婚的女人。
《半边天》里有很多这样的“怪胎”——「不一样的女人」。
要离婚的女人、敢反抗的女人、不甘心的女人、不要做灰姑娘的女人、甘心痛楚也不要麻木的女人……
是一个个内心火焰熊熊燃烧的女人。
她们的内心,像住着一座座活火山。
本日,我们仍被这份活火山爆发的能量所震荡。
02
有个高朋你可能都没想到——韩红。
那是韩红第一次上中心电视台的节目,张越请她去的。那时的韩红,由于形状,被各种演出拒之门外。
张越问她,人家到底是什么情由?
韩红很无奈地说,“太胖了,没法要,太胖了。”
上这期节目也是有时。牵线人和韩红说,这个节目主持人和你长相相似。张越是听了韩红的两句歌决定让她上的,便是后来她流着泪在节目上唱下的:
“跑啊,解脱你的绳索,
找回渴望已久的自由。”
后来,韩红自己也承认,这期节目对她特殊主要。一些人认识了她,她开始有节目可上。
那期标题叫,《别为你的容貌发愁》。
03
《半边天》最打动我的是,它在一个没有太多人评论辩论“女性主义”的时期,给所有人带来了一份最朴素的女性主义视角。
我记得一个叫杜娟的成都女孩,她是个“逃婚”的人——
逃离了那个所有人都夸奖的婚姻。婚纱照拍了,婚房买了,婚房里的家具每一样都是她亲手挑选的。但在末了关头,她还是反悔了。
她实在按耐不住那些以为不对劲的声音。她受过教诲,是职业女性。丈夫却并不支持她的事情。她加班到很晚,丈夫暗指她“不把稳”,夜不归宿。
她要强,想干奇迹,丈夫对她的期待却是,“随便找一份事情就好,没事情的话就每天打打麻将,走走街,做美容”。
这样的生活不好吗?不好。杜娟复苏地见告自己。
她走了。在 28 岁开始北漂,拎着几个箱子,和别人合租,过着流落的日子。
别人问她,为什么一定要走?
她说:“我要走得远一点。我如果留在成都,终有一天我肯定会动摇,选择嫁给他。”
还有一个叫吴蔚的广西女孩,我尤其记住了她的一句话——“我比起黛安娜(英国王妃)来,彷佛还要明智很多。”
她出生屯子,拿了最艰险的开局。6 岁开始给百口人做饭,去离家 500 米的地方挑水。读书的机会,是靠内心始终不肯低头的一口气护住的。终极,她读了大学。
后来,她恋爱了,工具是公司老板的儿子。周围人都以为,这是吴蔚最好的归宿。但在见家永劫,吴蔚谢绝了。
有人说,这便是灰姑娘的故事啊。
吴蔚回,“我恰好就不想做灰姑娘。”
她知道,进入那段婚姻,必须要交付出自我。她不接管。
还有个不结婚的女人,我找不到她的名字,她便是那个被称为“怪胎”的女孩。
县城里 23 岁以上的女人都结婚了,烫着卷发,穿当时盛行的“一脚蹬”连裤袜,接送孩子。但她没有,她穿着白衬衫牛仔裤。
她活成了怪物。
张越提到一个细节:
《半边天》节目组的男性编导和她一起从小区楼底下走过去,所有人家的窗户都“啪啪啪”打开,盯着她,议论她。
如果你问我《半边天》到底是一档什么节目,有个答案:
一个被周围人称为“怪物”的女人,在这里能得到理解。
04
最让我感触的,是一个叫杨东凌的屯子女性,村落里人都喊她“杨三换”——由于她爱换衣服。
下地干农活的时候,她跟所有人一样,穿方便的短袖短裤;农活干完,杨东凌会急速洗个澡,换上干净的旗袍。
她回顾起自己年轻的时候,穿着蓝色旗袍,骑着赤色的木兰摩托在街上闲逛,两眼放光。
在屯子的生活无聊,她就写诗,随时随地写。
叠衣服的时候,她写:
柜门洞开着
棉的 单的 薄的 厚的 长的 短的
我把它们全都搬了出来
于是
粉色床罩上全是衣服们乱糟糟的思绪
是该整理了
我要尽快地让它们规复沉着
她说“衣服们乱糟糟的思绪”便是她的思绪。她没办法让它们规复沉着。
她有时候夜里做梦也在写诗,半夜醒来,想赶紧把梦里的句子记下来。丈夫就骂她:“又玩电脑去了。”
她就不写了,然后,“那个诗就压去世在梦里了。”
但她不想让自我被压去世在生活的梦里。
同样不想被“压去世”的,还有一个爱穿赤色衣服的女人,也是那个至今还在被谈论的女人:刘小样。
“刘小样”这三个字,涌如今高中女生的日记里,涌如今微博热搜里,涌如今无数谈论的主语里。
人们说:
“我住在刘小样的身体里,天下里。”
“刘小样无处不在,我便是个中一个。”
她带着哭腔说出的那句,“我宁肯痛楚,我不要麻木”,像一声惊雷,在无数人的内心爆炸,无论男性还是女性。
人们震荡于一个屯子妇女惊人的表达力和敏锐的感想熏染力,更震荡一个女性如此准确地表达了内心所受的限定。
“大家都认为农人,特殊是女人,她就做饭,她就洗衣服,她就看孩子,她就做家务,她就干地里的活儿,然后就去走走,她就做这些,她不须要有思想。”
“我不接管这个。”
她常常坐在四方的院落里,举头看飞机,仔细听着高速公路上汽车飞驰而过的声音,听火车经由时的汽笛声。
她给《半边天》写信。为了让自己的声音从平原上传出去,她踩十里地的自行车到县城邮局,寄出了这封信。
她爱穿赤色,她知道大概城里人会以为那样太艳丽、太俗气。但她的周围,全是土。红,是差异于土的颜色,是她的寄托。
她有一扇永不关上的窗户,在心里。“我让它一贯开着,一贯开到我老。”
05
如今再看《半边天》,很多女性的故事都让我深受触动。我心头始终有一份温热,那便是节目本身对女性的一份同情与关注。
我在节目里看过一个西双版纳的“杀夫案”。一个女人杀去世了丈夫,手段残暴,泼了汽油,点了火。丈夫由于烧伤并发症不治身亡。
在其他新闻谈论里,这是个残酷的女人,乃至是个该判去世刑的女人。但在《半边天》,我看到了故事的另一壁。
她叫罗珠,是个热爱生活的女人。她有两个小孩,她照顾得很好。她一贯在被丈夫家暴,手段是非人的。
丈夫会扒光她的衣服,绑在芒果树上打。来往的人都能看到。
她想过跑,可怎么跑得远呢?她还有孩子。
泼汽油那天,丈夫又上门,带着新交的女友,又要钱又打人。于是就有了那个悲剧。
要知道,这个事情发生在近 20 年前。我真的很感谢《半边天》这样的节目,把中心电视台的镜头,把数十分钟的韶光,给予了一个女性。
让她去讲述,她身上到底承载了多少伤痕。
还有个细节我也难以忘怀。2008 年,恰逢节点,改革开放 30 年,所有节目都在做献礼,《半边天》也不例外。
它做的专题叫《繁花》,讲述一群深圳打工女孩的故事。
为什么?
不是那些所谓更成功、更亮眼的女人,而是朴素、普通的她们。
张越在一篇文章里写下情由:
“她们建起了深圳的半座城,将自己的血汗钱寄回家中,哥哥娶了媳妇,弟弟有了学费,父母盖了新居,一个个村落落脱贫了,一个个州里繁荣了,但她们少有人关心。”
无数中国“看不见的女性”,《半边天》或许是最早关注到她们,最早为她们说句公道话的节目。
06
还有不到十来天,这档节目就播出整 29 周年了。
足以让一个女孩终年夜——我在它开播那一年出生,如今,我对自己的命运开始觉察自省,创造和那些女性的讲述,有如此多的共通之处。
我和我的差错们,都知晓“刘小样”的名字。我听到一个女孩说,她的身体里,也住着一个刘小样。
我们甘心痛楚,我们不要麻木。
我们要复苏着欢迎自己的命运。
就像那个写诗的女人在半夜醒来,一定要写下那首诗。“(要不然)那个诗就压去世在梦里了”。
一个醒来的女人,一定忠于她内心最老实的声音。“(要不然)那个女人就压去世在梦里了”。
只要一个女人醒来了,
她内心的火山,
就没有去世掉。
只要一个女人醒来了,
她心中的火焰
就必须燃烧。
撰稿:樛木
演习:兔子
责编:丁丁
部分资料来源:电视节目《半边天》、《非常静间隔:俏丽新天下韩红》、《非常静间隔:跨界人生张越》、《第一人称复数》、《重庆专访:对话著名主持人张越——每一个人心都波澜壮阔》;人物《自由之路,〈半边天〉往事》、《平原上的娜拉》;文献《繁花——打工妹三十年实录》、《由〈半边天〉节目形态构建的嬗变谈女性专访类主持人的特质》
我已不再沉睡,海浪将我拥起。
——韩仕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