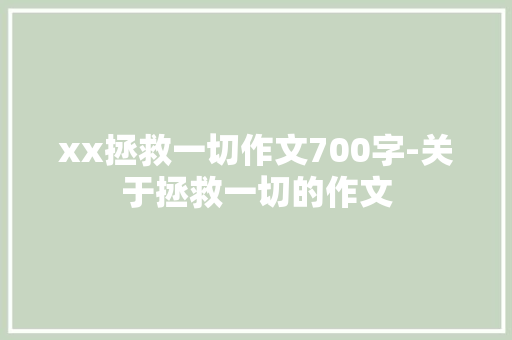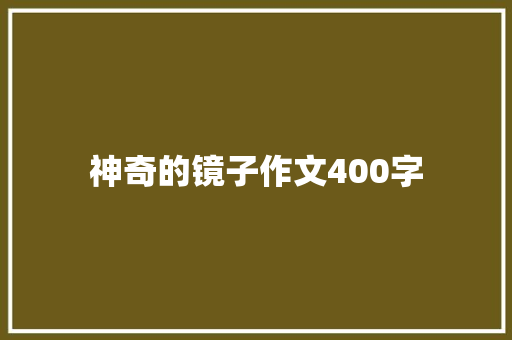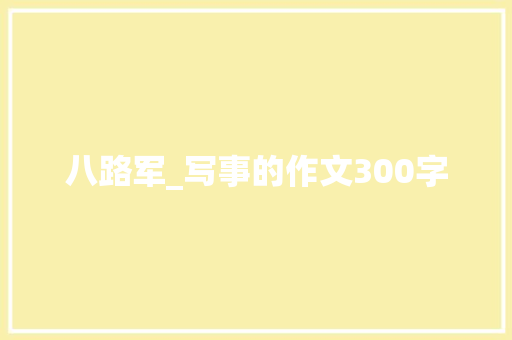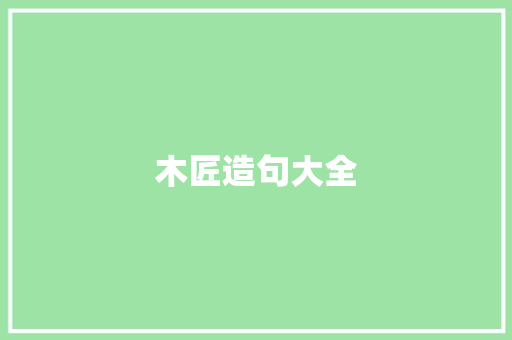民间博物馆让传统木作“活”起来
这个暑期,“博物馆热”持续升温,位于北京通州台湖镇东下营村落的文旺阁木作博物馆迎来了大批游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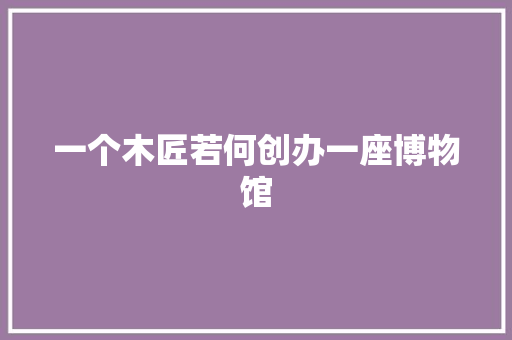
对付孩子们来说,这里“很好玩”:踮起脚就能触摸到一件件展品上的木纹,深吸一口气就能闻到扑鼻而来的木喷鼻香。如果他们刚好在博物馆里碰着王文旺,这位木匠馆长会绝不惜啬地从墙上摘下一件件响器——磨剪子磨刀的卦连、收垃圾的摇铃、拉洋车的铜脚铃、剃头匠的“唤头”,当这些老行当的吆喝工具再次奏响,孩子们便听到了已经失落传的民间绝响。
这间民间博物馆收藏着上万件木作老物件。在古色古喷鼻香的大门前,身着汉装、脚蹬布鞋的木匠馆长王文旺正用手机指挥员工,做好文博展品的新媒体展示。
离开老家河北衡水武邑县36年了,54岁的王文旺乡音未改。
跟随他穿行于博物馆,便走进了和木作息息相关的百态市井。满墙都是他亲自收藏来的老物件,抬眼可见传统民间的广告招牌幌子。在这里,可以抚摸逾百种中国古代榫卯构件,可以操练千行百业所用的木尴尬刁难象,乃至可以体验踏上马车、登上木船。
国家文物局统计数据显示,全国备案博物馆总数已从2012年的3866家增至2023年的6833家,非国有博物馆约占全国博物馆总数的三分之一。各具特色的博物馆连接了过去、现在和未来,也丰富了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作为一支不可或缺的社会力量,“小而美、精且专”的非国有博物馆通过民间力量搜集历史见证物、保护文化多样性,守护、传承、展示中华文明精良成果,在丰富公共文化做事供给、保存历史影象,以及优化我国博物馆体系等方面发挥了主要浸染。
王文旺在博物馆向不雅观众先容木作文物。均为新华逐日电讯谈昦玄摄
天子之六工,木匠列其一
“要在木板上雕龙刻凤,首先要把龙凤的造型画出来,按照轮廓,用刻刀把多余的部分剔除,才有立体感。左手握住雕刻凿把利用自若,右手持敲锤‘啪’地一打。活干闇练了,听响声就像在演奏音乐似的。”
做木工时的节奏感,王文旺至今影象犹新。他说:“手艺学成了,绝对是一辈子的事,你忘不了的,身体也会帮你记住。”
但曾经的王文旺并不甘心一辈子做木工,他以为“学手艺是糊口的无奈选择”。未曾料到,拿起大锯、截锯、手锯、推刨、锉刀、凿子、钉锤、墨斗、角尺,他就再也没放下过。
1970年,王文旺出生于衡水武邑一个屯子木工世家。数百年来,祖辈乡亲们多在营造行业做活。每个村落都有瓦匠、木匠,谁家盖房,就请乡亲们来搭把手,十几天就能建起一座新居子。
在中国,木工的历史可追溯至2000多年前。古代木匠事情范围很广,除了建筑,生产生活中家具、车船、棺材、木工艺品乃至军事上的弓箭、堡垒等,都离不开木匠。《礼记·曲礼下》记载:“天子之六工,曰土工、金工、石工、木工、兽工、草工”,木匠位列其一。
河北衡水,被称为“木匠之乡”,武邑县是硬木雕刻家具的主产地,迄今已有500多年历史。旧时北京城的营造行业,处处有武邑匠人的身影,宫廷造办处特设的雕刻家具作坊中,武邑艺人占八成以上。
在王文旺家里,小到农具、木匠工具、家具,大到拉车、房屋的横梁木架,无一不是祖辈凭借木工手艺亲手打造的。他的曾祖父、祖父都是普通木工,手艺代代相传,算不上博识,能搪塞屯子常见的木工活。祖上给外村落人干活,收点工费,补贴家用;给本村落人做工,不收工钱,主人家请吃顿饭就行。
到了父亲这一辈,农忙时务农活,农闲时做木工,走村落串巷去别人家里修桌椅、打家具。提着工具出门,带着一身木屑回家,挣来的钱刚好够五个孩子填饱肚子,再多的需求,便不能知足了。
作为家中最小的孩子,五六岁起,王文旺就拿着木雕凿子在边角料上做活,给自己做各式各样的玩具。终年夜一点了,有了力气,他会帮父亲“拉大锯”——在木料上画好墨线,用大锯将木料分割成多少木板。父亲和他一人站着,一人坐着,一上一下,一拉一送,拉锯要实,送锯要虚,节制着力度、方向和节奏。
推刨时开出的一卷卷刨花,散发着木喷鼻香,王文旺却安不下心来。在他看来,做木工辛劳、呆板,入门门槛低,社会地位不高。他打定主意,绝不子承父业。
然而,到了高一这一年,父亲多次对他说:“别上学了,学费挺贵的,做手艺吧,能养家糊口。”
做工、存钱、攒料、盖房,做家具、说媒、成家。父亲给王文旺方案好了人生。这是自古以来万万千万木工固定的人生轨迹,也是周围绝大多数乡亲们的现实生活。
但这不是王文旺的空想人生。他要出去闯荡,要去见世面。他偷偷报名参军,验兵通过了,又被父亲拦了下来。万般无奈,他只得辍学,练起了雕刻手艺。
王文旺在博物馆向不雅观众先容木作文物。
没有歪木头,只有歪木匠
迷茫之际,同为木工的老乡说带他去北京闯荡。一想到能看到在教材里见过的天安门,他便心动了。1988年,18岁的王文旺来到北京,一起上他暗下决心“有机会就做别的事,不能一辈子和木头做伴”。
老乡带他接的活是修复古旧家具。京郊小瓦窑村落的仓库里,古旧家具堆积如山,大多纹样精美、用料讲究,只见过大料粗工的王文旺看得晃神了。
师傅要验证他的水平,他信心满满地应下来,可到头来却连一张四方桌都搞不定。师傅说:“一个月30块钱的人为给不了你,你要么回去,要么在这儿做学徒工,没钱,只管饭。”
“没钱我也干。”王文旺说。
“没有歪木头,只有歪木匠。”要强的他此刻改变了主张,就要把木工学好。
修复古旧家具,和做新家具完备不同。审美上哀求修旧如旧,技艺上也极其繁芜,少则须要十几道,多则须要二三十道工序。选材、拆卸、修补雕刻残缺部件,都大有讲究。这些都对木工的技艺哀求很高。
单单为了练习刨花,他手上的水泡起了破、破了又起。待到双掌都磨出了厚厚的茧,手终于不疼了,技艺也终于练成了。经由近两个月的昼夜苦练,他总算能刨出薄如纸、长如卷的好木花。
每天耳濡目染各种古旧家具,一直地向老师傅求教,逐步地,木头在他眼里,不再只是木头,开始有了性情和灵气。“梨木炕柜杏木案,椿木风箱蛀不烂,槐木车辕松木椽,柏木棺材颐千年。”用什么样的木料做什么样的家什,贰心里越来越有数。
两年韶光过去了,一些手艺原来比王文旺好的同行,已经离开了这个行当,而从学徒工做起的王文旺,成了古旧家具及文物修复业内小有名气的木工,开始有顾客指定“这个活就让小王干”。
有心的他,把周围老师傅的手艺学透了,便想着向古人求教。一有韶光,他就去逛北京各大古迹,把所见的木建筑、木家具,印刻在脑海中,临摹在画纸上。
他将北海团城数米高的大佛龛,按比例缩小,复刻下佛龛里的雕刻和木艺,制成50厘米的木制小佛龛,很快便以280元高价卖出。“那可是1991年,很多人月薪不过60元。”首战成功,让他对这一行更有了信心。
1992年,他开始单独接活,翌年便碰着了改变命运的机会。一位收藏爱好者拿来15件家具,哀求他紧急修复。接下来,他每天就寝不敷4个小时,硬是在半个月做完了一个月也做不完的活。回顾起当年昼夜不歇的干劲,他说:“那时想不了那么多,只知作别人交给我的事就一定要做好。”
自此,他在古旧家具修复行业小有名气。短短几年间,小到不敷1尺高的板凳,大到4米多高的红木柜子,他修复的家具有万余件,每件他都力求做到最好。
曾有人调侃他“穷木匠,媳妇都娶不起”。但王文旺的木匠买卖却越做越好了,20世纪90年代,他成立了自己的古家具公司。
挣钱最多的一次,对方给了他100多万元公民币的活。“第一天就说先给我定金,让我立时出活。”就这样,王文旺随着人家到西单,第一次开办了一个账户,第一次瞥见汇款单。那2000美元的汇款,把他激动坏了,“手直抖动,汇款单都不知道放哪儿好”。
王文旺在博物馆向不雅观众先容木作文物。
何以为匠?
西席因材施教,裁缝相机行事,木匠则看料下锯。好木匠能看料做活,打造的家具十全十美,打造的建筑耸立千年。
木匠行里,随便做做和把工做好,有寰宇之别。好的做工,能让两块木板融为一体,浑然天成,“对着太阳光看,一点光都照不进去”。好的做工,能让一块木板被推得平展如布、光滑似镜。好的做工,能让榫卯紧实咬合,让一件家具、一处建筑耐久不衰,坚固耐用。
韶光,是考验木匠技能的尺子。“如果做不好,随便乱来,家具过一阵就用坏了,那木工的名声也坏了,就没人找你做活了。”王文旺说。
一贯在学习和思考的王文旺,不再知足于做个木工,而是想做一位匠人。
“比较木工,木匠的技艺和水平都更博识,从用具的材料、造型到构造、色彩和构图都要管窥蠡测,要将手艺和聪慧结合。”他说。
何以为匠?王文旺有自己的标杆。
“削竹木以为鹊,成而飞之”的故事家喻户晓。鼻祖鲁班发明了鲁班尺、鲁班锁,巧匠墨子更从木作中汲取大聪慧,提出了“兼爱”“非攻”等不雅观点,创立了以几何学、物理学、光学为突出造诣的一整套科学理论。
王文旺说:“在古时候,被人称为匠,那是相称了不得的。匠人是手艺人的最高境界,许多人一辈子也未曾达到,大国工匠那是想都不敢想的事。”
1999年,王文旺被北京市文物古建公司特聘为木工工长。在这里,他更有了用武之地,先后参与了丰台区药王庙、宛平城和故宫建筑的修复事情。在这些事情中,他又开始研讨和建筑有关的木作知识,每一处施工,他都力求做到最好。
有一次,他正拿着一块木料准备用作修复,一位监理事情职员走过来责怪他用料以次充好。他举起手中满是大大小小“虫洞”的木料,递到人面前,不卑不亢地说:“您再好好看看,这虫洞是我一个个做上去的。”那人顿时惊愕得说不出话来。
原来便是拿料填空的活,谁能想到,王文旺费时费力将整块木料做旧如旧,为这块补料增长了风雨、虫蚀的岁月痕迹。没人哀求他这样做,但他以为“这活就得这么干”。
在他看来,想成为好木匠,不仅是按客户哀求和行规事情,还要有高超的技艺、精益求精的态度,要把德行、坚持、诚信都融入自己的作品中去。
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中国自古爱崇工匠精神,《诗经》中所写的“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反响的便是古代工匠在雕琢器物时执着专注的事情态度。“巧夺天工”“匠心独运”“技近乎道”“斫轮老手”等针言,彰显著精益求精的中国工匠精神。
“木匠是民之本。你不要鄙视了木匠。”王文旺说。
他常常向人讲起唐代柳宗元《梓人传》中所写的木匠故事。梓人,便是木匠。这位木匠随身带着度量是非、方案周遭和校正曲直的工具,但没有磨砺和砍削的用具。柳宗元以为,他手头的工具看起来不足全面,就去问他会做什么?木匠答:“吾善度材,视栋宇之制,博识圆方短长之宜,吾指使而群工役焉。舍我,众莫能就一宇。”言外之意便是,作为一胜景利的木匠,他是帅才,而非小兵。
柳宗元亲眼见证了这位木匠在墙上绘制官署屋子的图样,建成的屋子没有一点偏差。“盈尺而曲尽其制,计其毫厘而构大厦。”他从木匠的分工、事情方法、绳墨规矩中领悟了将相的管理方法。
做一个好木匠,并非易事,除了要练妙手上的技艺,还要练成脑中的算力。
“木匠看尖尖,瓦匠看边边。”王文旺说,木匠是要精于打算的,用尺标志木匠的水平。“做家具若是尺寸不准,废物,还无法放样、画线和加工,一个好木匠能通过打算,让尖尖角角都到位。”
木匠还要精于看丹青图、善用榫卯。大师齐白石便是村落庄木匠出身。所谓“榫”,即凸出部分,“卯”为凹进部分。榫卯构造,即两个部件以凹凸连接的办法咬合在一起。制作的榫卯规格精密无缝,这才算是好木匠。
“我是学问不如人,但干活我有履历。”王文旺知道自己的短板在哪。他不知足于只有手艺,想在学问方面有所上进,想做个新时期的木匠。
于是,他托人引荐,到故宫求学,拜“故宫末了一位木匠”李永革为师,想随着师父学些更好的手艺。
高中辍学30年后,没有圆梦大学的王文旺终于找到了适宜自己的“木匠校园”——故宫。
李永革原任北京故宫修缮技艺部副主任,是官式古建筑营造技艺非遗传承人,故宫的建筑他险些都参与修缮过。他坚持用古法修缮故宫,比如在丈量柱子、梁架、进深等尺寸时,他不用更为方便的卷尺,而是利用“排杖竿”丈量法。李永革说:“差一点,榫卯就合不上。老祖宗的方法看似笨拙,但更实用。”
王文旺常常向师父请教问题,理解营造方面的细枝末节,每每有了新想法都先请师父示正,就像高校学生引导师提交科研论文。
“即便是在机器工艺发达的时期,社会发展仍旧须要木匠。一个新时期的好木匠,一定要用好新机器,又保留着古匠心。”王文旺说,在手工活上办理机器做不了的精工细活,在设计创造上表示木匠的巧思和创造力,这便是匠心肠点。
“我以为木匠一行也可以有研究生、博士生,由于这里面的学问,既须要有好的师父教,也须要自己肯花心思悟,没有三五年潜心研究,是学不明白的。”他说。
王文旺在博物馆向不雅观众先容木作文物。
让更多人理解木作里蕴藏的中国文化与聪慧
“以前盖屋子用木头,现在用钢筋水泥,以前做家具靠人工,现在用机器。在我十几岁的时候,各处是木工,现在木工的数量不敷以前的三分之一了。”从没有人为的学徒工,到收了一百多个徒弟的师父,王文旺在木匠行当里闯荡了近40年,见证了木工繁盛时期的悄然退去,也见证了属于木工艺术新时期的开启。
如今,在他的老家武邑,很多人做起了硬木雕刻和仿古家具,还有人开了小工坊,在当地形成新的木作家当。年轻人纷纭到工坊里体验有创意的木工制作。同时,木工也走进学校,成为磨炼学生思维、动手能力的教诲科目。木工艺术正以另一种办法传承下来,更好地做事于当代社会。
木作艺术贯穿着中国几千年来的发展。劳作在树木旁,居住在木房里。食在木桌上,寝在木床上,用木头造纸、雕版印刷。上到搭屋建房,下至走街串巷,都离不开木头和木艺。
作为木匠,王文旺懂得每一种木工里沉淀下来的聪慧,也懂得木作老物件里蕴藏的历史、文化,但他并不知足于此。他担心自己虽然懂得了中国文化的这一符号,但没能力守住它。
“人们都知道《鲁班经》是工匠之作的代表,但还有一本书叫《木匠》,内容更丰富,但由于没受到应有的重视便失落传了。”让王文旺心疼的是,有些古籍古物,一旦失落传就再也找不回来了。
多年前,他去朋友家,瞥见朋友的母亲正拿着一根弯弯的木棍烧火做饭。来不及说什么,他疾步上前,在木棍要被塞进灶膛的瞬间抢过来。仔细一看,那是条代价昂贵的黄花梨喷鼻香几腿!
这件事,让他意识到了遍及木作文化及传统木器认知的紧迫性。
于是,自1997年开始,他便致力于老物件的收藏、研究、整理与展示。他不收收藏家看好的金石字画,不收值钱的珍瓷美玉,只收老祖宗留下的实用型文物——和衣食住行、民俗历史息息相关的木作文物。
“我想通过修复和收藏,使一些濒临消亡的木作文物拥有更长的生命。”他说,“我尽自己的所能,能留住多少,就留住多少。”
从2005年起,王文旺带着自己收藏的老物件,先后在20多个城市巡展,让更多人理解木作里蕴藏的中国文化与聪慧。
古人用墨斗在波折的木头上画下直线,今人用红外线即可测绘。时期在提高,文化须要传承,博物馆是留住历史、传承文化的最好家园。随着巡展越来越成功,得到越来越多不雅观众的支持,“自己开个博物馆”的想法,在王文旺心中萌生。
“既然我知道了传承木作文化的意义,那就该轮到我做了。”关于开博物馆的决心,他这样说。
一个木工,如何能创办一间博物馆?
资金,用自己赚来的钱。展品,是自己的藏品。筹建,自己读书写方案。布展,自己请教专家辅导。
为网络木作文物,他问工友、找熟人、逛市场、去外地,费钱、费时、费力、费心,中断了自己赢利的买卖,不顾家人的反对,将一件件即将消散的木作老物件“请”到了一起,给它们找到了最好的归宿。
为给藏品做好文化溯源,王文旺“把图书馆搬回家”,当起了书虫,常常通宵达旦地查阅资料。有时,书上讲的内容,和他库房里收藏的物件恰好能对上,天一亮,他就把东西找出来,对照书本进行修复。
他动手妥善安置自己的200多名员工,把记录着97名外洋供应商的联结簿收进抽屉,全身心投入筹建中国木作博物馆的事情中。困难期间,“运营不下去就卖一点东西”。说这句话时,他显得有些无奈。
但提及接到博物馆申请获批的那个电话时,他显得有些激动:“你不知道我那时候的心情,我哭了整整一个下午。”
人和木头很像,什么样的木头做什么样的物件
2017年,北京文旺阁木作博物馆正式开馆。
从辍学的屯子木工,到没有人为的学徒,到开公司的贩子,再到受人敬仰的博物馆馆长,这一起走来的激动和痛楚、热闹和孤独、造诣和酸楚,五味杂陈只有他自己知道。
木作文化佳构展、传统民间广告招牌幌子展、传统百工百业展、传统建筑及家具展、传统出行工具展、度量衡展、不同地域古家具展……在北京文旺阁木作博物馆里,50多个主题的展览、上百个门类的藏品,品类之全令人惊叹。
“每次来到文旺阁木作博物馆,都有新的变革,不管是知识先容的展板,还是小型的专题展览,都是这座民间博物馆对"大众的贡献,创新使这座博物馆充满活力。”北京市文物局一级巡视员向德春说,博物馆创新,是一件知易行难的事,但这间民办博物馆一贯在努力做得更多、更好。
作为全国科普教诲基地,文旺阁木作博物馆每年欢迎几万逻辑学生研学,多次与都城博物馆、中国园林博物馆、中国港口博物馆等博物馆互助办展,并受邀参加喷鼻香港、澳门创科展览,先后被付与“北京市科普基地”“北京市中小学社会大教室资源单位”“北京市民终生学习示范基地”等名誉。王文旺研发了上百个劳动技能课程,部分录入中小学课外经典诵读。他还开拓了多种木作体验课程,比如一架桥梁模型,小学生看外不雅观,中学生看构造,大学生学习丈量打算等设计知识。
“作为劳模,王文旺不但传承着木艺技艺,也发扬了木工行业里蕴藏的中华精良传统文化,在平凡的岗位上造诣着不平凡。他身上争创一流、勇于创新的劳模精神,和执着专注、追求卓越的工匠精神,能够鼓舞民气。”北京市通州区总工会干系卖力人表示。
作为馆长,王文旺得到“通州十大工匠”名誉称号,2020年被评为北京市劳动模范,以此表彰他在中华传统木作文化保护领域作出的突出贡献。
“被收藏界忽略的民间文化,让王文旺捡起来了。”北京收藏家协会常务副会长、都城博物馆文物修复部原主任魏三钢说,王文旺的收藏较为独特,大多数人选择收藏高大上的硬木家具,他却选择收藏民间的柴木家具,“正是这些柴木家具,最能真实反响历朝历代公民真实的生活场景”。
在魏三钢看来,王文旺之以是能做好民间木作文物收藏,一是由于他是木匠出身,职业经历让他对民间家具比较理解;二是由于他有经济头脑,做生意的成功让他拥有了追求空想的经济根本;更主要的是,他有文化自觉,“不在于文化学历的高低,而在于是否热爱传统文化”。
在王文旺申请创建博物馆之初,北京收藏家协会给予了很多支持,组织专家对他的藏品进行了专题会论证,为藏品正名。魏三钢说:“王文旺的收藏故事,是收藏圈值得关注和借鉴的样本。在与他的互换中,我们将博物馆专家的学者之长和民间力量相结合,更好地挖掘、保护了中华精良传统文化。”
“生命是有终点的。在彻底做不了事情之前,我还要做些事情。”五十知定命。现年54岁的王文旺常感叹时期发展得太快,而自己精力不济、能力不敷,不然能做得更好。
关于未来,王文旺有两个欲望:一是在中国其他省区市开办博物馆,让更多人理解木作文化;二是让中国木作文物巡展外洋。
“我想好了要若何对外国人先容中国的木作,要从榫卯讲到古人聪慧,从鲁班尺讲到易经易学,从椅背上的云纹讲到龙文化,从木作的周遭讲到中国人授予器物的哲学。”王文旺不断描述着属于自己的中国木作文化梦。
“以绳墨自矫,而备世之急。”高中被迫辍学的他,经由多年耕读,如今发言间,对柳宗元的名篇《梓人传》、墨子的佳句、长安城的建造故事信手拈来。
带了一百多个徒弟,在故宫完成过修缮事情,培植了一座博物馆,让更多人认识了木作文化。很多人说王文旺是专家、是学者,但他认为自己所做之事,不过是将木作老物件和专家学者研究出来的文化成果,对接在一个个木工活上,让这些古旧的器物重新抖擞光彩。
“人和木头很像,什么样的木头做什么样的物件,什么样的人做什么样的事。”王文旺说,“我只是做了一个木匠该做的事,我只是一个木匠。”
把手艺留着,让影象藏着,使历史活着,将故事讲着。这是一位木匠馆长所做的文化传承。(谈昦玄)
来源:新华逐日电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