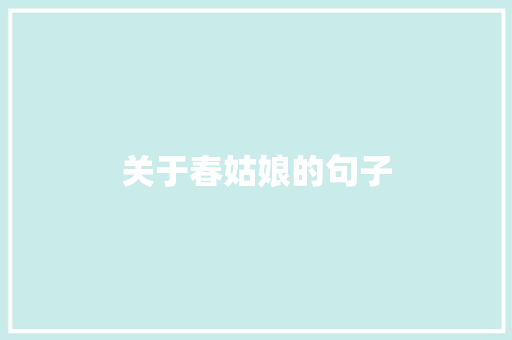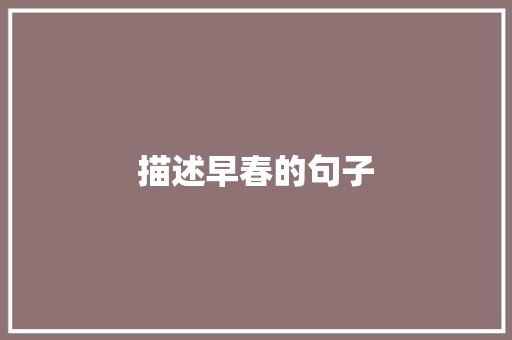最近学习《当代文学作品选》,读到戏剧部分,开始品读田汉的剧作《南归》。
田汉的真名田寿昌,湖南长沙人。剧作家、电影编剧、小说家、词作家、墨客、文学批评家、文学活动家,中国当代戏剧三位创始人之一。

《南归》是田汉早期的一出浪漫主义悲剧,剧中的人物和情节,多少带有些抱负色彩,作者利用浪漫的想象,童话般的描写春姑娘和流浪墨客辛师长西席、青年农人李正明之间的男女感情,表现他们对付现实人生的苦恼与美好憧憬的幻灭,悲叹空想、现实间的冲突,暴露社会的阴郁,剧作弥漫着感伤的气息,同时又交织有武断的反抗。真切地刻画了流浪墨客的孤独执着;春姑娘的热烈年夜胆;以及李正明的勤恳虔诚,人物情绪真实动人。
《南归》根据情节的发展以及人物行动穿插诗句与歌曲,将诗、剧、音乐相结流,使得这部独幕剧具有“抒怀剧”、“诗剧”的韵味。
读罢《南归》,我深深被《南归》营造的浪漫主义气息所传染,被流浪诗人为探求空想天下而四处流落的状态所震荡。流落者辛师长西席无所皈依的心灵、无处勾留的脚步、难以抛却的情怀,也正代表了过去的、现在的也是将来的一大批人的一个精神状态。
剧中表现的流浪和流落,是人类在探求精神家园。《南归》表意的中央是流落者无家可归的存在状态、悬浮无根的流落感和春姑娘对流落者的渴慕之情,在授予流落者深刻的历史内涵的同时,揭示了人类在探求精神家园是普遍存在的一种困境。
春姑娘对她母亲描述对流浪者的感情:
他来,我不知他打哪儿来;他去,我不知他上哪儿去。
“不知道从哪儿来也不知道上哪儿去”这不便是人类一贯在思考却一贯没有答案的问题吗:我从哪儿来,我要到哪儿去?
不管是坐着,或是站着,他的眼睛总是望着迢遥迢遥的地方。
那个远方是否便是我来的地方?是否也是我该当归去的地方?
我心里老在想,那迢遥的地方该是多么一个有趣的地方啊,多么充满着美的东西啊。
迢遥地方,是不是有趣,没有答案,但是流浪者没有选择,背着行囊拄着手杖,一起向远,一起流落,一起希望。由于唯有这样,才不负此生。
自古以来,人类就有一种流落的心态,一种出走的生理。至于如何流落,出走到哪里,没有详细的观点。只是想离开,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
纵不雅观古今,流落不是《南归》的专利;放眼中外,流浪却是人类共有的情怀。
在海内,从古代孔子的旅居游学,屈原的自我流放,杜甫的“行万里路”和郑和的多次西下,到当代人时时准备的逃离般的旅游 ——“天下那么大,我想去看看”,都是流落的心态、流浪的情结、寻根的渴望的使令下的一种行为。
而国外,最为范例的便是犹太人流浪的生存办法,而麦哲伦绕地球航行,人类和动物界一次次大规模的迁徙,都有找寻的身分在内。
流落者所说的很远很远的地方到底是什么呢?
很远很远的地方是一片净土,没有苦难,没有争斗,没有流落失落所更没有尔虞我诈。人类曾经从哪里出走,出走时有一份印记被镌刻在先人的影象里,并且被动地生生世世传承,人类不能也无法抹去那个印记。由于这印记太飘忽,太虚幻,没有方向,没有详细的处所,所往后来人都或多或少地都带有流浪情结——那是原始的召唤,是人类共同的感应。
“人生是个长的旅行:或是东,或是西,”
剧作家借助流浪墨客辛师长西席的口吻给这份流落找了个正当的媒介——人生便是旅行,至于是东还是西,是南还是北,都不主要。主要的是,人生要在路上,而且要一贯在路上。在路上就有找到原始的可能,在路上就有回到最初的希望,在路上就会免除负罪的折磨。以是,辛师长西席得知春姑娘被她母亲许给了李正明,便当仁不让地选择离开,连续他的流浪生涯。大概得不到春姑娘的爱情,辛师长西席有遗憾,但是是不是更多的是解脱呢?!
“我终于有个情由可以连续流浪了,了无顾虑,多好!
”而春姑娘又是这样一个执着的女子,他追随辛师长西席的足迹,“跟他到那迢遥迢遥的地方去。”
流落的人生“充满着诗,充满着泪”
《南归》“是田汉剧作中感伤身分最重的剧本”,评论界险些都认为这部剧作“反响了作家内心的苦闷, 寻不到出路的感伤、惆怅”。空想的家园不知在何处,代表希望和美好的“春”姑娘又与辛(心)无关,此地也已经无可留恋,去也无奈留也无奈,去留都是感伤。终极离开,是向南归去还是从南归来,都不主要了,以是这是一部悲剧。
“春归何处。寂寞无行路。若有人知春去处。唤取归来同住。
春无踪迹谁知。除非问取黄鹂。百蝶无人能解,因风飞过蔷薇”
黄庭坚的这首《清平乐.春归何处》读来总有一种难以言说的失落落、惆怅和期冀,词人是在问春、寻春、唤春还是寻根?“春无踪迹谁知?”由于不知,以是探寻,由于探寻,以是在路上,这便是流落者的宿命。《南归》的作者也把这份感情寄托在诗和歌中。
流浪者听到春姑娘许给了李证明后,决定离开,离开前对着春姑娘一贯保留的他的鞋,这样唱到:
......
我见了你,记起我旧日的游踪;
我见了你,触起我的心头的痛创。
我孤鸿似的鼓着残翼飞行,
想觅一个地方把我的伤痕将养。
但人间哪有那种地方,哪有那种地方?
我又要向迢遥无边的旅途流浪。
破鞋啊,我把你丢了又把你拾起,
宝贝似的向身上珍藏,
你可以伴着我的手杖和行囊,
慰我悲惨的旅程。
破鞋啊,何时我们同倒在路旁,
同被人家深深地埋葬?
鞋啊,我寂寞,我心伤。
流浪者亦歌亦诗,合着泪水倾诉自己的无奈和追求,同时也表现一种武断和断交:虽然翅膀已经残疾,虽然我只有手杖和行囊,但是我还是选择流落,流浪远方,直到“倒在路旁”、“被人埋葬”。
流浪者的脚步不能停歇,流浪者注定要在路上。虽然曾经的一份美好能让他暂时容身,但是离开还是一定。以是,听凭春姑娘如何追求,流浪者也不得不对春姑娘吐露真言:“春姑娘,我也不想离开你,可我是一个永久的流浪者,怎么能说得定呢?......春姑娘!
你说你不愿意离开我,难道我乐意离开你吗?不过谁能保得定没有不得不离开你的那一天呢?”
流浪者内心非常清晰自己的流落的心态:他不会永久地为一片云容身,也不会一贯恪守不变的生活的状态,他是一个永久的流浪者,以是他要离开,他要流落,他要流浪。而春姑娘追随的脚步,也揭示了流落的是人们内心普遍神往和渴求的状态。
写完,不知所云,内心被流落的感情包裹,被流浪的生存办法吸引。我是不是该当放下笔和世俗,一起流落,直到倒在路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