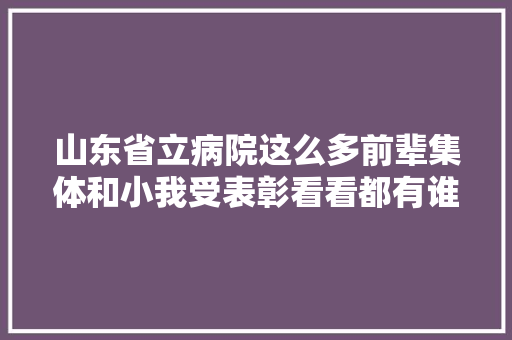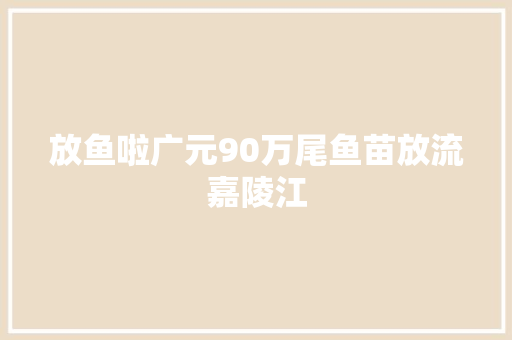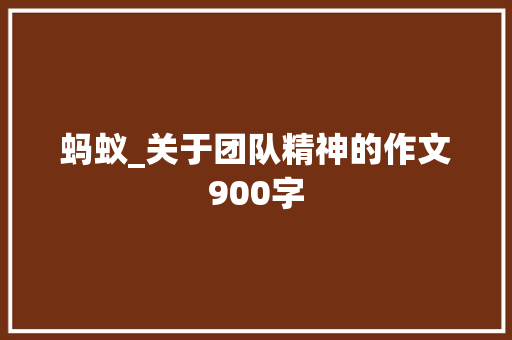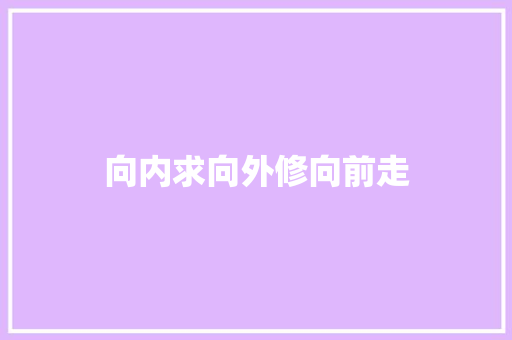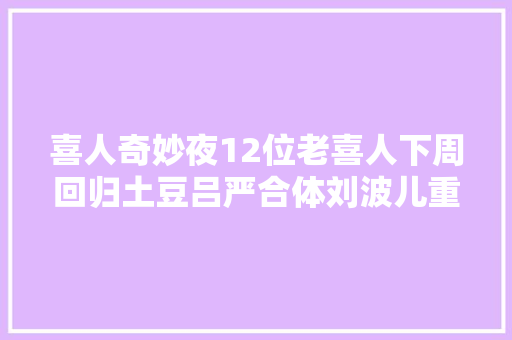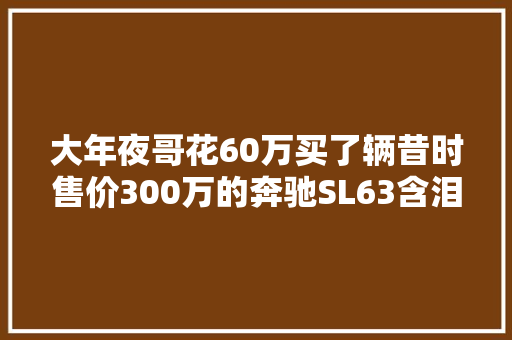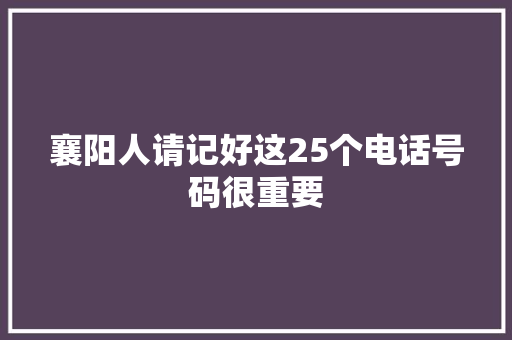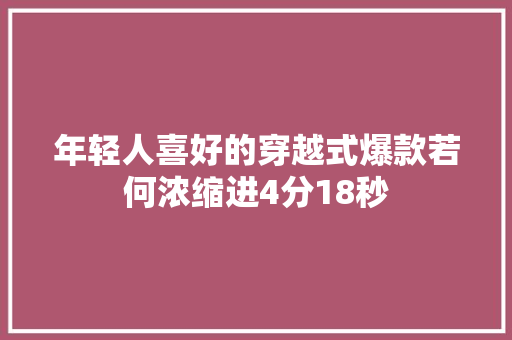水利部中国科学院水工程生态研究所生态技能工程中央团队成员在开展鱼类增殖放流活动。新华社 曹祎铭摄
从奔驰于青藏高原的雅鲁藏布江,到位于南水北调工程中线的丹江口水库……有江河湖泊的地方,险些都能瞥见这样一支团队:他们不善言辞、总是专一干事,为多地水生态环境保护注入科技力量,守护着祖国的大江大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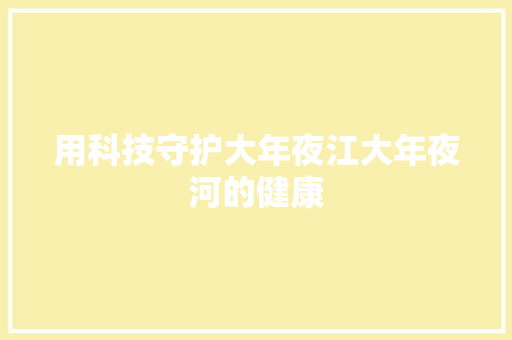
他们便是水利部中国科学院水工程生态研究所生态技能工程中央(以下简称工程中央)团队。今年“五一”前夕,该团队被付与“全国工人先锋号”名誉称号。
人工繁育长鳍光唇鱼
滔滔江水顺流而下,转化成的“绿色”电力,点亮万家灯火。不过,水电站在给人类带来清洁能源的同时,其培植运行可能会对河流生态环境造身分歧程度的影响,个中就包括生活在河流中的鱼类。
为了最大程度减轻水电站培植运行对水生生物的影响,水电站常日配套培植鱼类增殖放流站,依赖人工繁育、放归河流的办法,坚持流域生态平衡。
无论是我国第一座鱼类增殖放流站——乌江索风营鱼类增殖放流站,还是海内放流规模最大的鱼类增殖放流站——丹江口鱼类增殖放流站,背后都少不了工程中央团队的身影。鱼类繁育、增殖、放流,已成为这支团队的“看家本领”之一。
虽然已是业内顶尖团队,堪称“养鱼”好手,但在如何养好鱼这件事上,工程中央团队仍在不断钻营新打破。
2020年起,工程中央团队接管委托,在广西来宾市红水河珍稀鱼类增殖保护站开展长鳍光唇鱼的人工繁育技能研究。长鳍光唇鱼为红水河特有鱼类,其人工繁育的技能难点在于亲鱼(具有生殖能力的鱼)应激反应强烈。“这种鱼在被人为触碰或者受到惊吓后,极易去世亡。”来宾市红水河珍稀鱼类增殖保护站项目卖力人、工程中央团队成员之一张志明先容道。
在亲鱼的采集运输阶段,工程中央团队成员颇费了一番功夫。为了能把这种敏感的鱼安全带回保护站,团队成员长期蹲守在河边,理解、剖析可能影响其存活的各种成分。经由精心准备后,团队制作了分外网具对其进行捕捞,并定制了专用水箱,采取麻醉、充氧等办法进走运输,终极成功将其安然带回保护站。
不过,在后续的养殖阶段,工程中央团队又碰上了难题。保护站的“饭菜”并不合长鳍光唇鱼的胃口,来到保护站后,其永劫光不开口摄食人工合营饲料。为了摸清它们的“饮食习气”,团队成员又回到它们的“老家”——红水河。通过现场解剖,团队成员不雅观察其肠含物,他们创造长鳍光唇鱼在野外紧张以着生藻类和水草为食。
创造这个问题后,团队成员便开始自己动手,制作举动步伐设备造就硅藻,将硅藻与粉碎后的商品饲料稠浊后再进行投喂。这次,长鳍光唇鱼成功开口摄食。经由进一步研究,团队成员在不断降落硅藻比例后,终极使这种“挑食”的鱼类成功转食人工合营饲料。
2021年4月,经由一年造就,团队成员准备对长鳍光唇鱼亲鱼进行人工繁育。不过,事情职员在检讨其性腺发育情形后,使其涌现了应激反应,大量去世亡,第一次人工繁育未能顺利开展。
“我们吸取了教训,在亲鱼驯养造就过程中采纳拉网磨炼的办法,让它们更好地适应人工养殖环境。”张志明说。
2022年,工程中央团队开展了第二次人工繁育试验,得到了一定数量的鱼卵,虽未能孵化成功,但为后续事情奠定了根本。
今年4月,工程中央团队顺利开展4次长鳍光唇鱼人工繁育试验,得到4万余尾长鳍光唇鱼苗种。这是我国首次实现长鳍光唇鱼人工繁育。
像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十多年来,工程中央团队占领了长薄鳅、乌原鲤、巨魾、中国结鱼等十余种珍稀特有鱼类人工繁育技能瓶颈,累计放流鱼苗近4000万尾。
“复原”绿水青山
和鱼打交道,只是团队事情的一部分。他们另一主要职责是开展涉水工程水生态保护与修复。
回顾过往,让团队成员印象最深的,便是大渡河河口生态修复项目。
位于大渡河流域的安谷水电站地处旅游城市——四川省乐山市,那里有“天下文化遗产”乐山大佛。
“安谷水电站所处河段河网密布、洲岛发育丰富,大渡河、青衣江、峨眉河在此交汇后汇入岷江,这里鱼类资源丰富、生态系统敏感。”工程中央团队成员之一、安谷水电站项目卖力人、高等工程师王文君表示,早在该水电站方案培植初期,环境影响评价审核专家便对此处河网水生生境的保护与修复、珍稀鱼类的保护等事情提出了明确哀求。工程中央团队的事情便是针对这一工程可能对周遭生态环境造成的影响,设计出一套完全、可操作的水生态保护与修复方案。
接到任务后,工程中央团队成员首先对该河段水生生物、鱼类资源及主要水生生境进行了详细、深入的现场调查与监测,节制了此处水生生物群落的构造特色。随后,团队成员预测剖析了工程培植后河流生境指标的变革以及天然河段生态功能的受损情形,在此根本上针对性地提出了构建过鱼通道、增殖放流等方案。
“该方案能够有效规复河流生态系统的功能,得到了专家的同等认可。”王文君见告,大渡河河口主要水生栖息地的保护与修复事情从2007年开始,至今已超过15个寒暑。
在此期间,团队成员亲眼见证了大渡河两岸沟壑纵横、撑船渡河的村落镇演化为公路入户、宜居宜游的生态城镇,砂石袒露的施工现场经由人工修复后变为水流鸟栖、坡绿水清,生态河道与电站河道并行的生态美景。
踏遍江河湖泊
工程中央团队成员时常要到野外开展事情。青藏高原是他们野外调查常去的地区之一,面对高原缺氧等寻衅,团队成员已习以为常。
在青藏高原时,令许多团队成员印象深刻的,当数旱蚂蟥。
2020年7月,正值西藏林芝地区的雨季,工程中央团队冒雨在雅鲁藏布大峡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排龙乡附近进行野外稽核。在刚刚躲过一场山体滑坡后,团队成员蒋思进、方艳红溘然创造,他们身上有多处被“喝”人血的旱蚂蟥吸附。
“当时,旱蚂蟥已经吸足了鲜血,身体呈极度膨胀状态。”团队成员回顾道,他们在忍痛拍掉旱蚂蟥后,身上仍留有血痕和咬痕。据当地事情职员和村落民先容,旱蚂蟥具有一定毒性,如不及时处理可能会留下后遗症。于是,团队成员立即相互合营对伤口进行消毒处理,紧急购买排毒、解毒药物进行治疗。
直到现在,团队成员在谈起旱蚂蟥时,仍心有余悸。但在当时,他们战胜了恐怖,多次深入高山峡谷,终极圆满完成野外调查事情。
2021年11月,团队前往新疆塔里木河流域开展水生生态调查事情。冬季塔里木河地区景象恶劣,团队成员每天打仗冰冷的河水,双手几近冻伤。永劫光赶路更是让每个人都患上了腰肌劳损,个中就有当时已经56岁的工程中央研究员杨汉运。
如今,“接力棒”即将交到青年人手中。4年前加入团队的青年骨干——袁婷早在学生时期就对水生态学充满兴趣,毕业后,她在理解到水生态保护事情的艰辛后,依然选择加入。
“刚加入不久,团队老师就带我前往广西、贵州,为珠江和乌江渔业资源增殖放流奔忙。这让我明白,在祖国大好河山背后,是无数人的默默付出。”袁婷因此更加武断了她的选择。
“我们从未有过歇歇脚、松口气的想法,也从不居功自傲。我们团队已奔忙在水生态保护一线20多年,未来还将连续走下去。”工程中央主任陈锋表示,工程中央将连续专注于水生态保护奇迹,用科技力量守护祖国绿水青山。
作者:都 芃
来源: 科技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