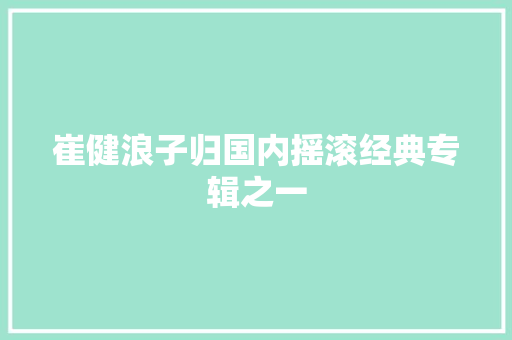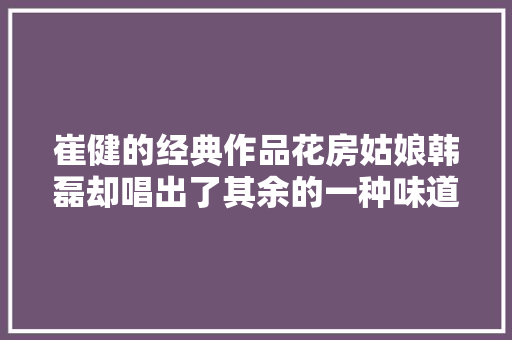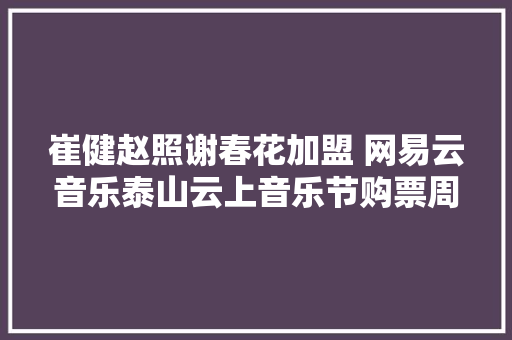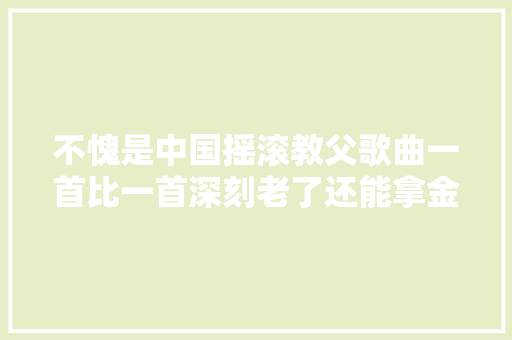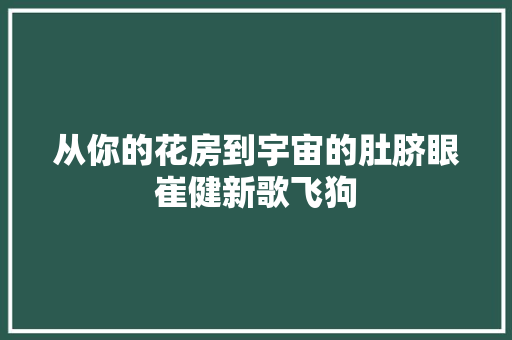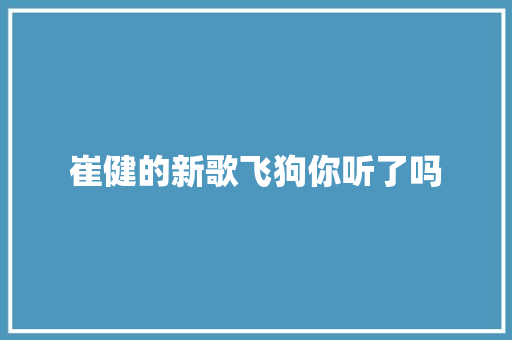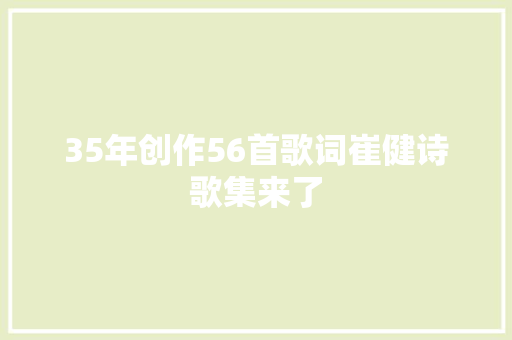我对摇滚的感情,基本始于这句歌词:“那烟盒中的云彩,那羽觞中的大海,统统装进我空空的肚量胸襟。”
为我年少时的胡作非为找到了完美的形容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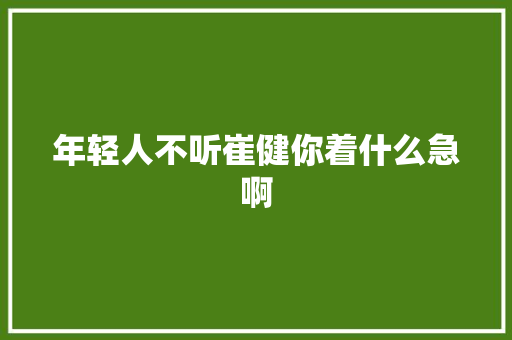
那时候听摇滚,听崔健,多少还有点逼格上的体面。现在弗成,听崔健在年轻人那儿连装逼的需求都知足不了。
办公室里的小朋友,对崔健的理解仅止于“很有地位的老歌手”,百科词条里多到吓人的“轰动”“标杆”“首创者”,对他们来说是种熟习的陌生,听得多了,觉不出什么厉害来。
摇滚教父的过气,在客不雅观事实上无可争议。
3月13号发的新歌,至今豆瓣评分人数不敷50。微博就甭提了,我连朋友圈都没看到几个转发的。
照例,人不多,吵的架倒是不少。
我看到有人在评价里一股脑用尽了感慨词组:“彻底过气了。时期结束了。不可惜。真的才华有限。”
还有一种另辟路子:“是不是现在也没人敢说崔健的新歌不好听?反正我以为不好听。”
愤怒的老炮键盘噼啪响,敲出一大串:“你大爷便是你大爷!
”
站在“崔健”这座中国摇滚的丰碑上无所事事,彷佛也只能用各种姿势找点优胜感。
02
认识到崔健有多糊这件事,是自认听过摇滚的老家伙必经的修行。
新歌开头一嗓子“数字天下大草原”,跟前阵子万青那句“星河下,电子荒原”挺像。
问题是这都2021年了,批评数字时期这事,晚了20年。
创作周期的长度,远超如今听众的兴趣周期。暌违六年写出来的歌词,在揭橥之前就已经由气了。
万青还能靠着文青情怀撑住,崔健弗成。万青是诗性的,文艺的,怆然里带着柔和——是更个人的。
这跟崔健赖以成名的先锋、愤怒不同——那是对全体时期的,石破天惊。
崔健生于1961年,亲眼见证过期期的崩塌与重塑,学乐器的初衷,据传是他父亲想让他进入文工团体从而不必下乡。
比起乐坛后生,崔健对更大的东西有更准确的感知,就像他的红布和头顶上的五角星。
他那份生于上世纪末的情怀,就适宜凝固在上世纪末,放在如今,老态龙钟,且没有必要。
愤怒什么?批驳什么?日子过得不是挺好的嘛。
崔健上过年轻人最爱看的B站晚会。镜头一扫,台下的不雅观众礼貌地打着拍子乖乖挥舞荧光棒,除了对前辈的尊重,看不出还有别的激情亲切。
老家伙很难接管崔健舞台下的不雅观众能如此镇静,他们当年恨不得吼劈了嗓子蹦瘸了腿,哪场演出安保不更加?
诸神时期的两块活化石,一个崔健,一个窦唯,都还在发歌,都听者寥寥。
活化石活在当年的身份里。崔健眼睛上那块红布,窦唯在红磡的那场演出,在并不漫长的华语乐坛历史中举足轻重,提起中国摇滚就绕不开。
然而一旦他们试图分开当年的身份,创造当下的作品,看着总有几分不合时宜。
是他们把握不住时期,把握不住听众了吗?
有可能。崔健的“数字大草原”会被嫌弃老套,窦唯的《后疫》淹没在一片最美逆行者里。
窦唯还可以归因于他羽化了、超脱了,上着综艺拍着电影的崔健,一贯在活动,从未被看重。
这个时期注定不会再像从前那样被一个人、一种风格所把握。崔健写的“数字天下大草原”,老一辈人避之不及,年轻人撒开蹄子跑得欢畅得很。
草原便是这样的,牛鬼蛇神并肩行,大鱼小鱼一起游,创作和得到的门槛都几近于无。
又或者是我们把握不住他们了。
周杰伦也是时期的标签,近几年的创作周期也一样长。但他发福多年,归来仍是少年,每次发歌都热闹非凡。
由于周杰伦好把握。这跟音乐水平无关,是音乐的内容和感情好把握。
歌唱最有共鸣的东西,爱情、亲情、少年之志,没有触及太多独特的、小众的人生履历。
打个比方,就像今年春节档势不可挡的《你好,李焕英》。人们谈论它的重点在于“冲动”“诚挚”,不在于剧本构思、导演手腕。
崔健当年红遍大江南北,也跟欣赏门槛没多大关系。空空如也的年代,听众最有共鸣的人生履历便是空空如也。
03
《蓝色骨头》听着有几分崔健自传的意思,里面有这样一句词:“我便是一个春天的花朵,恰好长在一个春天里。”
那个年代便是崔健的春天。
他是开荒的人。
带头揭开你我眼上蒙尘的红布,于是众人猛然创造,十丈软红里赤橙黄绿青蓝紫,要什么颜色有什么颜色。
当所有人都没颜色时候,崔健给你一点颜色,惊叹与爱都自然而然:我曹还能这样?
当所有人都有了各自的颜色,崔健一个人的颜色就没那么主要了。
这个时期不可能像从前那样被把握,也不须要有这么一个人来帮他们把握。
崔健导演的电影《蓝色骨头》,与他一首歌同名。
空空如也,在某种意义上创造出了无所不能。
而现在的我们,看起来什么都有了,一块红布和五彩斑斓随便选,我们可以去把握独特的、尖锐的东西,但是我们不能。
歌词会和谐,纹身会打码,演唱会要掌握影响,连点评其他歌手的音乐都会被舆论攻击。
这几种“不能”崔健都经历过。
印象最深刻的是他在《中国之星》里点评喷鼻香港歌手许志安,认为他唱的那首经典粤语歌在那个舞台上很同质化,且已经是20年前的旧作,希望能看到更多喷鼻香港的新鲜的表达。
节目组剪辑一通骚操作后,舆论果真风起云涌,都在骂崔健倚老卖老、不尊重粤语,还质问他“你不也只会翻唱那几首老歌?”
乐评人张晓舟气不过,专门找来完全的现场录音,撰稿给崔健正名,但上热搜的永久不会是一份澄清。
“看准那庞然大物的重心点,回来击穿它的肚脐眼。”这真是摇滚老炮才有的空想。
庞然大物太大了,谁也看不准它的肚脐眼。
04
走到本日,崔健当年亲手给听众揭开的那块红布,像是蒙在了他自己身上。
他必须先锋,必须独特,必须对所有人都很主要,必须在"大众年夜众面前与子弟扞格难入。
当年怀抱自由和背叛的摇滚精神,转眼成了另一种急需自由和背叛的标签。
被动的和主动的,从输出者到输入者,所有人互不相容,崔健只是他们识别代价不雅观身份的一份证据。
下图这位只是感叹了一下崔健新歌水花太小的网友,由于没有直言对教父的喜好,都要被追着问“你在瞎哔哔什么”。
人们格外关心崔健与许志安的“见地不合”,不会在乎他同时还在推举子弟谭维维。
华语乐坛的后生、未来,都不须要他来管。他只作为一个符号、一种崇奉存在,承担着逝去的时期的共鸣。
本日的时期共鸣不在他身上了。《一块红布》上一次引起广泛关注,还是由于有小偶像在节目上改编这首歌卖腐。
老家伙们咬牙切齿,小粉丝们喜大普奔。
被翻来覆去说烂了的是原子化、孤岛化、审美隔离,时势不再造英雄,金曲越来越少。
但实际上可能并不是曲弗成了,是大家对金的理解不一样了。
崔健上一张被多个滚圈人评为“听不下去”的专辑《光冻》,我一个朋友就非常喜好,尤其爱里面那首《金色清晨》。
在此前她并不懂崔健,不懂摇滚,以是才幸运地没有听见说它“听不下去”的主流的声音。
从前没人说话,嫌别人的声音太少,如今别人的声音太多,彷佛也万般不自由。
以是,没必要用崔健的江湖地位来衡量和评价他现在作品的热度。
由于“摇滚教父”这个凝固的标签,实在已经沦为了工具,晚会的工具,评论的工具。
对,不是崔健成了工具人,他还是人,是标签“摇滚教父”成了工具人。
这件事里面最尴尬的不是崔健、也不是活用标签工具的综艺或文章。而是揪着“标签”昔时夜旗的,感叹崔健老了,听众傻了的人。
按头别人听摇滚这件事,太TMD不摇滚了。
但是这对崔健来说大概并不悲情。
他早就在《从头再来》里唱过:“不愿离开,不愿存在。”
他确实不用离开、也无需存在于教父的神座上。
他还可以兴致勃勃地飞来飞去,到银河到宇宙,琢磨着去打别人的肚脐眼儿。
喜好《一块红布》的人也还是喜好《一块红布》,不听新歌便是了,本来他们中的大部分,以前也只听过他的《一块红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