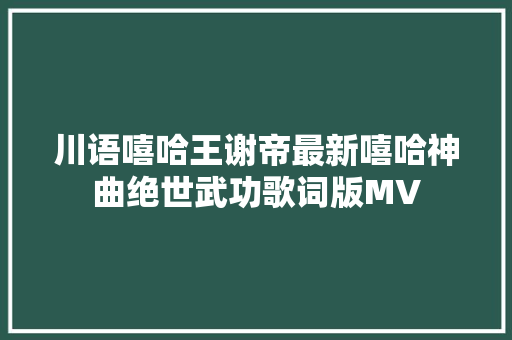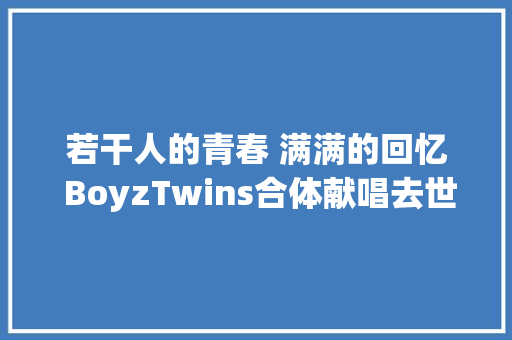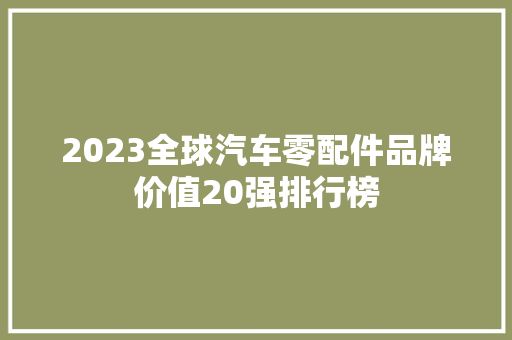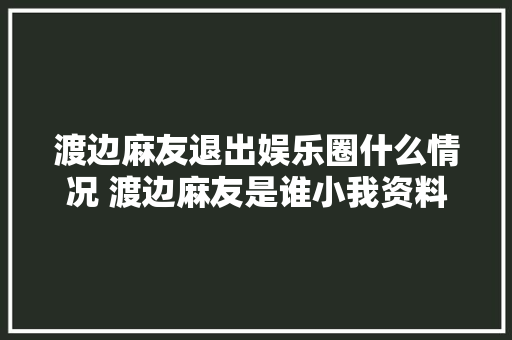2020年10月,日本女高中生Ado 演唱的《烦去世了》的MV在 Youtube 公开,随即在日本引发社会关注,如今不到半年,其播放量已打破1亿次。在海内,《烦去世了》虽然无法引起与番剧主题曲同等程度的关注,但歌曲直白的讯息也使日音爱好者中受到“996”压迫的社畜们对曲子的反抗性产生亲切共鸣。
《烦去世了(うっせぇわ)》 。视频:空灵雨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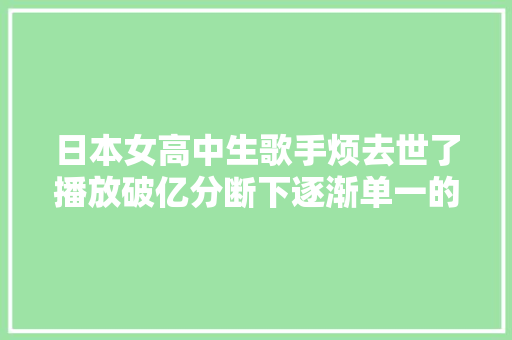
那么,这首不太文雅的“反抗”歌曲,为何能在均匀年事47岁、老龄化严重的日本打破原来的年轻受众,得到本日的成绩?背后存在的,实在是一个打破了日本人特有的“本音”和“建前”间的樊篱,讲述年轻一代与上一代人之间代沟和分断的故事。而这个故事所映现出的,也是被疫情加剧的,社交网络下当代天下的分断现状。
反抗曲《烦去世了》,折射出分断的两代日本人《烦去世了》由2002年出生的现役高中生歌手Ado演唱,社会人syudou作词作曲。前者刚于2021年3月17日宣告高中毕业,身份较为神秘。而syudou则和米津玄师一样,是属于Vocaloid界的新进鬼才音乐人,其2019年发布的Vocaloid曲《苦巧克力装饰》的MV播放次数也已打破1200万次,他本人也以歌手身份翻唱了《烦去世了》。
“烦去世了烦去世了烦去世了(うっせぇわうっせぇわうっせぇわ)”,伴随八度音程跳跃的上口曲调,以及当代许多日本人普遍拥有心情写照——副歌的这两个要素,很自然地使《烦去世了》在受到压抑的日本社会煎熬的年轻人中得到传唱。随着日本亚文化界的“唱见文化”的进一步传播和传统电视音乐节目对它的聚焦,《烦去世了》终极成功出圈,成为一个不雅观察日本当下社会的窗口。
歌曲第一段中的“从小便是头等生”、“刀子一样平常尖锐的思考回路”实在便是在致敬1983年日本The Checkers(方格子)乐团的出道曲《ギザギザハートの子守唄》。当下的日本年轻人自然不会知道这种致敬的存在。如果某位有所觉察的上一代日本人洋洋得意地见告他的子弟:“《烦去世了》实在是在致敬《ギザギザハートの子守唄》”,这位子弟可能表面上会毕恭毕敬地说:“啊?是这样啊,第一次知道呢。”内心却在吐槽:“烦去世了,那不是重点吧”。
《ギザギザハートの子守唄》。视频:点燃熏喷鼻香
自以为理解了《烦去世了》的上一代日本人迫不及待地将自己的创造和理解传授给下一代日本人,并以此得到精神上的知足。然而《烦去世了》所代言的新一代日本人对上一代人的“浅近理解”只会表面上点头示意坚持“建前”(表面功夫),内心却不会将自己的“本音”(至心话)——自己和这首曲子间的连带关系透露给上一代人。这便是这首曲子所歌唱的核心:世代间的代沟带来的分断。
尾崎丰是曾经一个时期的反抗的代名词。图片:推特
许多上一代日本人会将《烦去世了》与80年代日本歌手尾崎丰的歌曲联系在一起,他的许多作品歌唱了“抗议大人”的逆反生理。在那个时期,日本年轻人每每会通过骑上偷来的摩托“暴走”,或者打碎教室窗子的形式,向社会中的“大人”表达“逆反”。然而,上述暴力性抗议作为对“不满”的宣泄,至少还算某种形式的互换,这一代的年轻人却早就将之抛弃,关上了对话的大门。
《烦去世了》所描写的,实在是对“大人会来理解自己”的放弃,一种从未开诚布公的至心话。歌词“当然会把握最新的盛行动向,上班途中也会去理解经济的动向,以献身、纯情的精神进入公司事情”——表达的是年轻人对将这些“规矩”强加给自己的大人所组成的社会、以及“羽觞空了就要盛酒”等社交礼仪嗤之以鼻。因此,歌曲视频下可以见到许多诸如“上班路上听Ado,到了公司就以《烦去世了》的心态事情”、“如果能在上司面前这样唱该多爽”、“能毫无顾忌地去嗤笑他们太解气了”的赞许之音。这一代的日本年轻人,前一天还能在酒桌上与前辈谈笑风生,第二天就能递交辞呈——对立和反抗未正式发生就已然结束,没有互换,有的只是一种深埋心中的怨气。
与LGBTQ一样弱势的日本年轻人这种代沟和分断是如何产生的呢?紧张缘故原由大概这天本年轻人在社会中的处境。与中国不同,少子化数十年的当代日本社会中,年轻人占绝少数。统计显示,其1.3亿总人口中,10-19岁年事段的只有1100万,约占8%,这一比例明显低于其他国家,与日本的LGBTQ性少数群体占比持平。在这样的环境里,社会对年轻人和LGBTQ人士的歧视和忽略险些是等量的。
近年逐渐增多的日本性少数群体。图片:Yahoo
日本年轻人也早就对自身的少数和弱势现状有自觉。比如,在syudou所处的范例的“年轻人创作音乐给年轻人”的Vocaloid界,すりぃ的《Telecaster B-boy》(2019)和やてにをは的《Villain》(2020)等名曲会与LGBTQ的感性产生共鸣,绝非有时。而すりぃ和やてにをは这两位Vocaloid的P主(音乐制作人)也都给Ado的歌编过曲:2020年12月24日的《Readymade》便是すりぃ作曲,2021年2月14日的《ギラギラ》则是やてにをは作曲。
若以“47岁”这个均匀年事打算,出生于1973年的这代人正处于日本末了一个人口高峰。他们被称为“团块Junior世代”,人口规模约为 209万,而日本当下十几岁的学龄少年每届(年)也只有105万。规模相差足足一倍,两代人视野中的天下也大不一样。那么,对付人数上占绝大多数的“强者”前辈们“天经地义”的态度,弱势的日本年轻人会整体放弃“反抗”,而选择将心情寄托于这首《烦去世了》也实属正常。
从天下隔离的自我和向机器靠拢的人类然而,这种弱势地位并不应该成为谢绝与上一代人恳切互换的借口。某种程度上,《烦去世了》中过激的歌词和曲调带来的逆反“本音”,实在也是一种以为“烦去世了”就不由分辨地将自己与这个天下的他者隔离开来的中二态度。
新一代的年轻人会有这种态度并不奇怪。由于自我与天下、他者的分断与隔绝本身便是当现代界的一大课题。
随着科技进步,机器越来越靠近人类。个中霸占主要浸染的AI技能能得到高度发展,实在便是机器接管了“他者”的结果。例如,AI能下过顶级围棋棋手,也是通过与他者(别的AI)对战、网络信息和数据、不断反复对局磨练自我的结果。正是通过这种与他者的相互干涉,AI才实现了对人类的仿照和靠近,开始逐渐像人类一样节制多样思考和表现幅度。
与此相对,人类也在靠近机器:只要有了网络这位“老师”,险些就没有无法办理的问题;离开了手机和导航软件,人们可能会寸步难行,就连驾驶这一行为也将被机器取代。我们将影象、思考乃至空间认知能力“外包”给机器——仿佛只要有了网络,我们就不用去接管他者,就能坚持自己的天下不雅观,坚持只属于自己的“精确答案”。不用等新冠肺炎前来侵扰,《烦去世了》的火爆就已经展现涌当代人谢绝他者的“自我隔离”的现实。
《远间隔恋爱,见不着的时候也爱你。》直白的歌词。图片:prcm
开始被“一次情绪”盘踞的日本歌坛在另一方面,由于“烦去世了”就谢绝他者,并总是将这种情绪挂在嘴边,同样是一种不加润色的“一次情绪”。从平成末期,类似的歌唱“一次情绪”的歌曲就开始霸占日本歌坛。例如,男性音乐团体Sonar Pocket的《远间隔恋爱,见不着的时候也爱你。(遠恋だけど逢えない時間もアイシテル。)》(2011),副歌也是“想见你,见不着,好辛劳,好寂寞,想见你,想和你一起笑,想抱着你”;西野加奈的《Best Friend》(2010),歌词也是“感激有你,有你真好”、“我们是Best Friend,喜好你,最喜好你了”;而出场2020年红白歌合战的瑛人的《喷鼻香水》也唱道:“你是如此吸引我,我会再次爱上你。”
喜好、寂寞、辛劳——这些歌曲将情绪包装成歌词原封不动的唱出来,不存在任何误解或误读的空间。
而回顾更早的日本盛行乐,绝对不会涌现这些一次情绪:悲哀时是“看到你目光触及时钟就会想哭”(松田圣子《赤いスイートピー(赤色豌豆花)》),难过时是“似曾相识的雨衣,在薄暮的车站内心颤动”(竹内玛莉亚《车站》)。这些过去的歌曲中存在一种背景、一种歌词意象中解读的空间,与当代日本歌曲大相径庭。
是不是沉迷于“烦去世了”的当代人,情绪表现愈发纯挚直白,较过去发生了倒退?恐怕不然——人的实质并不是那么随意马虎就能改变。问题的关键大概是在媒体中。
喜好、想见你、寂寞——日本人从良久以前就将这些情绪寄托在歌里。天下最古老的长篇小说《源氏物语》中,主人公光源氏就将喜好、想见你、悲哀、落泪等感情编成歌反复吟唱。然而,这些歌中选取的语句常常会以挂词的形式演绎出两重、三重的含义,让读者展开想象的翅膀。
这些歌每每被写在遣唐使带到日本的唐纸上,这些纸乃至还留有暗香。纸上用羊毫写的字也是风格和形态互异,诱使读者对作者的意图和情绪不禁产生遐想。
低分辨率媒体带来的变革从手写的纸媒到活版印刷,从电话到电子邮件,再到推特、微博、微信——媒体作为装载情绪的容器“进化”到本日,从技能上看,其所能承载的信息量理应增加许多。
然而,只要十几个字、乃至几个表情就能传达讯息的当代社交媒体和在纸笔和字体高下功夫的纸质信件,哪一个信息量更丰富恐怕毋庸置疑——追求短平快的当代SNS的信息分辨率实在并不高。因此,在这个时期,发信者才不会利用具有多重意思的表现,而是选用不会带来误解的话语。
日本乐坛曾经的名曲每每将情绪寄于景物和行为描写当中,听者可以自由解读曲中所蕴含的意义,歌词在这一过程中自动转换为听者心中的情景,随之产生共鸣。那么,在这个低分辨率媒体霸占主导的时期,缺少背景和情由的一次情绪会以“烦去世了”的形式登顶“名曲”,仿佛也成为了一定。
《烦去世了》通过当代数媒技能领悟去世亡金属和动画风的乐曲,配上Vocaloid式的演唱,明明有如此多元的要素、如此丰富的信息量,内里却透着简化和单一。歌曲本要表达的“反抗”,就跟当下日本年轻人谢绝对话的态度一样,显得如此苍白无力、乃至风趣。就连歌词中敢于断言“我便是你们所说的天才”的毫无反省的态度,也只是身为弱势群体的当代日本年轻人无奈的矫揉造作。
“就这样将话语的枪口对准脑门”。图片:youtube
“我也不咋地”、“就这样将话语的枪口对准脑门”——《烦去世了》在仇视、谩骂这个天下和他者的同时,实在也是在骂自己。毕竟,一口一个“烦去世了”的人最“烦去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