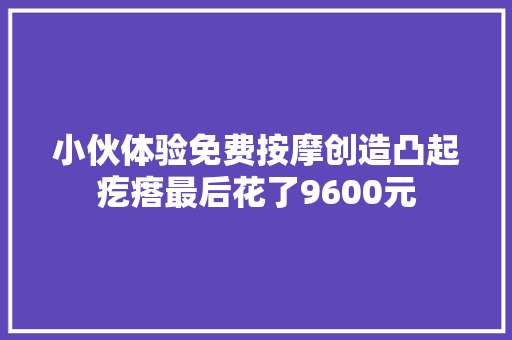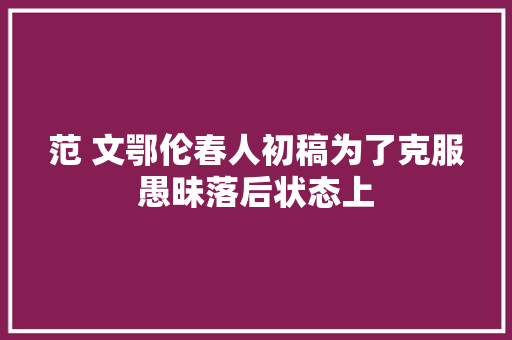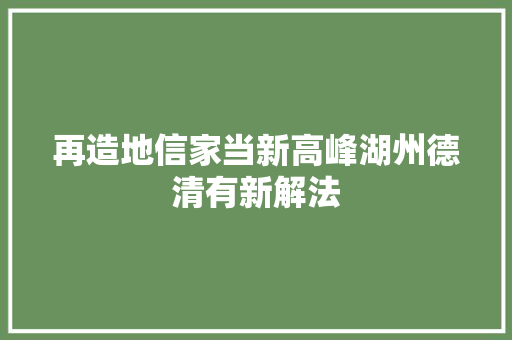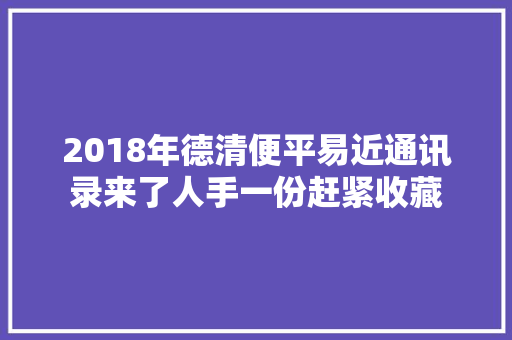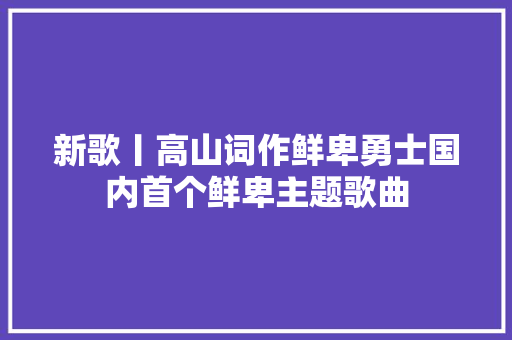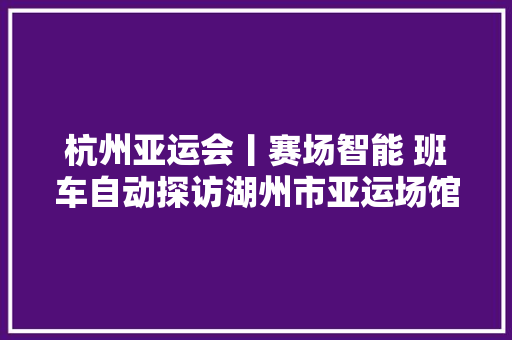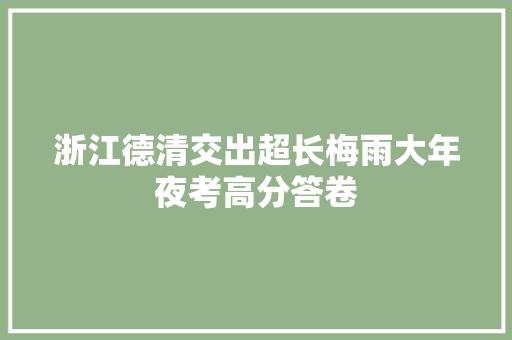顾德清能回答这个问题。这个来自齐齐哈尔的男人,少年时就抱负能有一支猎枪,生活在森林木屋里。后来,他来到内蒙古学习舞台美术,成了拍照师。年轻时,他曾经去过兴安岭的猎区,被鄂伦春民族的文化所吸引,念念不忘。改革开放后,1980年代开始,他带上胶片相机和胶卷,再次来到那里,来到鄂伦春和敖鲁古雅的鄂温克使鹿部落身边,拍摄下他们的衣饰、桦皮盒、驯鹿、佃猎生活……
猎民生活日记;顾德清/著;北京联合出版公司·乐府文化;2022-7

对付顾德清来说,这不仅仅是曾经梦想的实现,也是保存民族传统文化的急迫须要,“过去常能看到的鄂伦春族古老住屋‘仙仁柱’没有了,鄂伦春族人常穿的狍皮衣、‘其哈米(鞋)’也少了,有着古老花纹的桦皮盒不多见了,会跳 ‘萨满’的人也去世了!
”
顾得清开始了他一个人的民俗调查拍照。这可不是普通的拍照任务, 不是拿着先容信找几位族人摆拍几个生活场景那么大略,而是在某种程度上放弃一个“当代人”的生活,带上狍皮被,穿上皮袄套裤,剃一个秃顶,进入兴安岭的深处,与族人们同吃同住,无论冬夏。
最艰巨的时候要数进山打猎时,长途跋涉于原始森林中,动辄百里,骑马骑到屁股磨破,苦不堪言。住的是只有一层布墙的“撮罗子”,还常常露宿在雪地里、暴雨中。打到猎物时吃野兽肉、饮烈酒,和大家一起吃生鹿肝,打不到猎物时就只有吃列巴和大酱。
有一次打猎结束,他等了整整四天,才等到可以回到城里的汽车。又有一次,由于在森林中生活,衣服被刮成了布条,他差点被小镇旅店当成了逃犯。至于在雨雪中入眠,生病无法医治,也是家常便饭。
猎民姑娘 本文图均为 顾德清 摄
正是这样共同进退、共同生活,顾德清被猎民们真正收受接管,说他“包格道中!
”(汉人行),把他当作自己人,让他一呆便是两个月,一次又一次地,帮他备马鞍,帮他上马,让他跟随迁徙、打猎,给他做引导,乃至还引路千里,带他去看宝贵的岩画。
在顾德清的镜头中和笔下,有着最真实的猎民生活。他的笔墨,由于漫长的参与和全心的投入,有种简练而凛冽的力量。他记录下了他们每一个人的名字,以及他们朴实、坚毅、绝不矫饰、与世无争的性情:以为打猎前拍照不吉利,会打不到猎物,但也不因此责怪拍照的顾德清;哪怕没打到猎物,坐在篝火边安歇时,“脸上仍旧是那么坦然”;酒喝多了难免叫骂斗殴,到了第二天,大家又仿佛无事发生,相亲相爱,让顾德清忍不住感慨,“这真是我见过最淳厚的一群人”。
小猎手和驯鹿
他记录下莽莽的白桦林、山涧、月光下的雪野、清晨的雾、夏季沼泽里恼人的蚊虫、森林里清新的气味,以及在个中生活的动物:犴、乌鸡、飞龙、灰鼠、狐狸、驯鹿“珊瑚般俏丽的鹿茸”…… 千百年来,兴安岭的猎民们与这片森林和个中的生灵共生,没有林木就没有篝火,不打猎就没有食品,使鹿部落不养驯鹿,就无法生活。这是人类社会与自然所能有的,最为大略、朴实与和谐的关系。
这样的生活自然艰辛。大雪天跋涉数百里,却一个猎物也打不到。顾德清写道,又一次,好多天没有肉吃,为了改进炊事,玛丽亚-索只能杀去世一头她最宝贵的驯鹿。当然,在当代社会中,这样原始的关系更是薄弱的。哪怕在80年代,顾德清也已把稳到鄂温克人扎过帐篷的营地丢了不少水瓶之类的垃圾,而他们住在“原始佃猎住屋”里,穿着“当代衣着”,也让他有了一种“说不清”的觉得。
他还记录下经济活动对传统文化的改变:“白天看,这里的环境和我在1982年去乌苏门随猎的地方很相似,营地都是在河套的林子里,现在营地上已有不少猎物,差不多能装上一汽车。个中有些狍子没剥皮,这个征象在鄂伦春传统佃猎中不多见。鄂伦春一样平常是打到狍子急速剥皮、开腔,切成前腔、后腔驮回来。不剥皮,据我所知,可能是外贸部门专收整只孢子的缘故。看来,传统的佃猎习气也是随须要而改变的。”
十八站戴头饰的鄂伦春妇女
顾德清用了四年韶光,拍摄了两千两百多幅照片,记录了大量民族学、民俗学等资料。1991年,在他的建议下,鄂伦春民族博物馆成立,顾德清担当了首任馆长。他从来没有忘却过他的猎民伙伴们。20年后,他的儿子顾桃想要重访敖鲁古雅,他依然清楚地记得他们的名字,在纸上写下,让儿子去找他们。
顾德清在纸上写下的名字,在他的日记中都有出场。但是,当顾桃真的拿着名单前往敖鲁古雅时,却创造他们都不在了。“曾经带领他的果士克,也便是玛丽亚-索的半子。还有马克西姆,玛丽亚-索的哥哥,这四五个人都不在了。”
不过,他们虽然不在了,但活着的人,以及他们的后人,还记得顾德清,“顾德清的儿子”这个身份,依然为顾桃得到了进入猎民生活的“合法性”,顾桃依然记得当时在酋长的客厅里,大家挨个“盘考”:你是顾德清的儿子啊?
迁徙中的驯鹿
如果你看过顾桃拍摄的有关敖鲁古雅的记录片,会感想熏染到一种不同于《猎民边地日记》中勃勃活气的一种伤感。对付顾桃来说,他对猎民最初印象,来自父亲回家时,让自己帮忙冲洗胶卷。在那个亮着赤色小灯的暗房中,马、猎人、森林、狗、驯鹿穿行在森林里的样子逐步显现出来,特殊生动,为他带来了森林的气息。但是,20年的光阴使得敖鲁古雅原来依赖森林的生活办法发生了巨大变革,随着国家生态移民政策的开展,定居的鄂温克人告别了猎枪,大量鄂温克人下山入住敖鲁古雅乡,选择融入当代文明生活。五个猎民点中,后来只剩下已故的玛丽亚-索他们还保留着最传统的喂养驯鹿的办法。许多人不能适应,顾桃说,“(那时)我感到酒精的气息弥漫在山林里。”
猎民姑娘罗在雪堆中安歇
最近老酋长玛丽亚-索去世,顾桃回到敖鲁古雅,参加了她的告别会。他想起她说过的话,“玉轮戴头巾了,最冷的时候到了,你们赶紧出去多找点去世掉的树来取暖和”。那时是三九天,她说的玉轮戴头巾,指的是玉轮周围的光晕,顾桃说,她是部落一种精神上的存在,而且不仅仅是精神领袖,也节制着森林的聪慧。
不过,这次回访,顾桃也感想熏染到了年轻一代的发展。顾桃2010年拍摄了一部记录片《雨果的假期》,雨果是来自敖鲁古雅的鄂温克小伙子,曾经漂在北京、成都的主人公,曾经在北京、成都等地方打过工,三年前,他回到了敖鲁古雅。“在表面他们没有自由,回到家里,找到了自己该当做的事,就踏实了。”雨果帮妈妈柳霞连续养着驯鹿,也把抖音、滑板和山地自行车,带到了这片森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