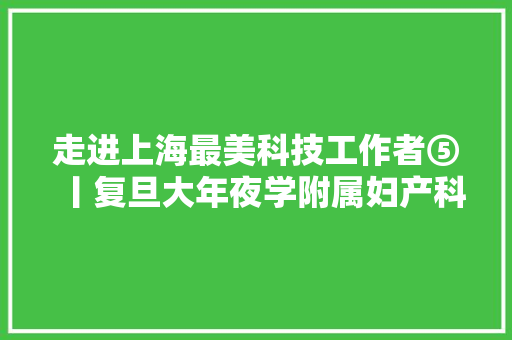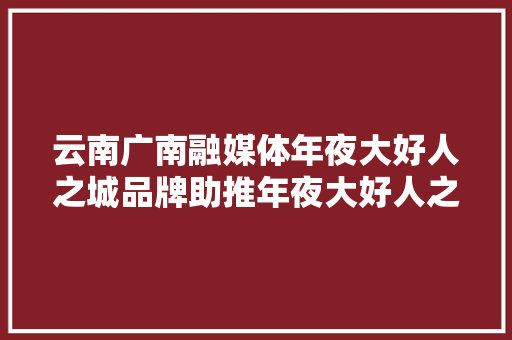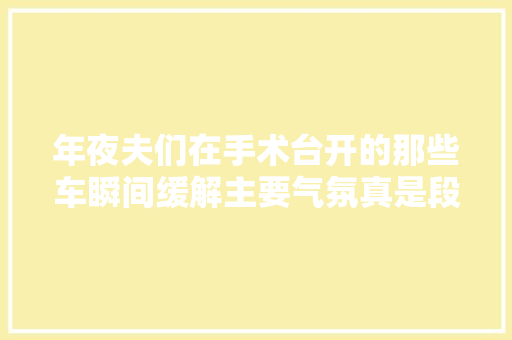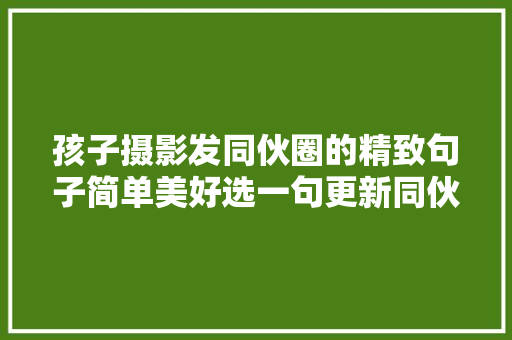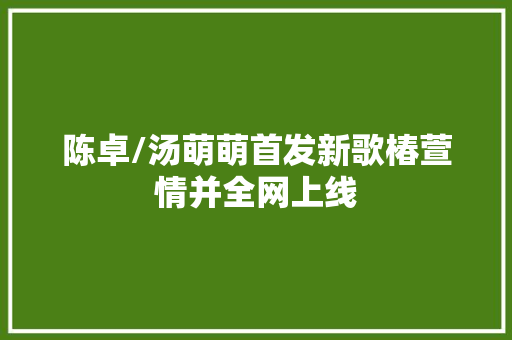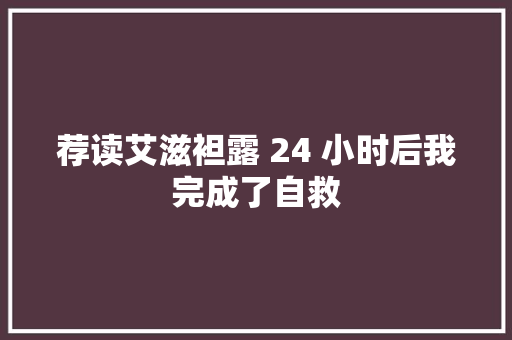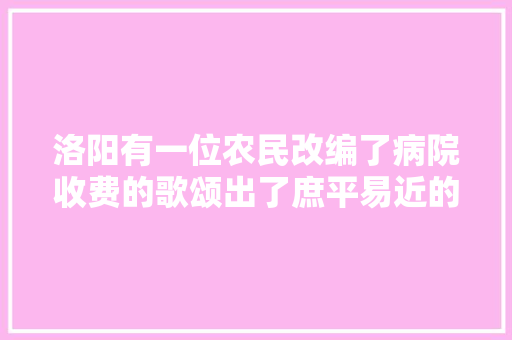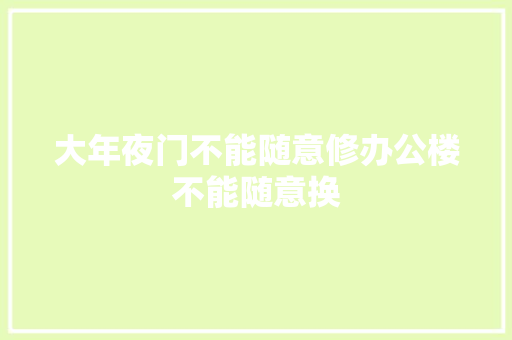我叫菲利普,是上海一家医院的整形科年夜夫。
从演习算起,我已经在医院摸爬滚打了将近 10 年,轮转了所有外科科室,也见过了人情冷暖和世间百态。欠费跑路的病人、蛮横无理的家属、牵丝扳藤的医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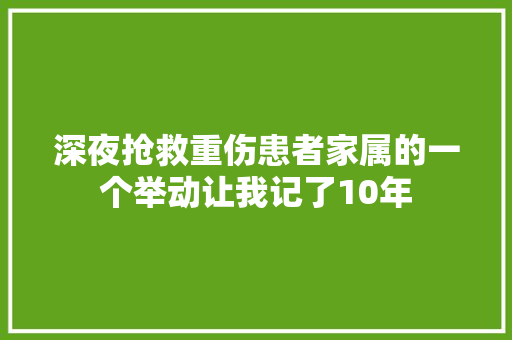
就像人们说的,医院是最能暴露人性的地方。
无名氏
10年前,我正是本科末了一年,刚进医院演习,轮转的第一个科室是神经外科。
那天是我值班,和另一个年夜夫凯哥一起守在急诊。除了有几个大略的头部外伤患者,统统都风平浪静。 吃过晚饭,趁着病人少,凯哥让我赶紧回办公室,利用空闲看看书,准备年底的研究生考试。可书还没看多久,手机溘然嗡嗡地震动起来。
“快过来!
来了个颅脑外伤!
”电话那头是凯哥发急的声音。
我心里一惊,任何一个外科年夜夫都知道颅脑外伤的严重性。我赶忙跑去急诊,凯哥正坐在诊室里看 CT 电影,一脸凝重。
电影是下面的县医院拍的,左侧硬膜外血肿,大概有十几毫升,右侧大脑有小范围的脑出血。单从 CT 结果来看,情形并不严重。
可看到患者后,我才创造,问题并不像电影上显示的那么大略。
患者是一个年轻男性,看上去 20 岁旁边,秃顶。除了一块淤青,他的头皮上并没有明显伤口,却已经陷入晕厥。我检讨了一下神经反射,也涌现了非常。
凯哥说,CT 是 2 个小时以前拍的,血肿肯定还在增大。他已经安排了复查 CT,今晚八成是要手术了。
听到凯哥这样说,我赶忙去帮患者办住院手续,可在候诊区喊了几次“抢救室三床家属来一下”,都没有人应答。这时我才想起,他的床头牌上,写的是“无名氏”。
随着患者一起来的警察说,他是骑摩托车出的车祸,事发地点在县城外不远处的公路上,很可能是车辆失落控背面部撞到路边的护栏,当场晕厥。目前他的身上没有任何身份信息,摩托车也没有牌照。
为了尽快手术,我只能联系医院的干系卖力人,帮他办了急诊绿色通道的手续,优先抢救。也便是说,先救命,再收费。
这时,CT 的检讨结果也出来了。我一起小跑去 CT 室,直到拿到电影,才终于明白了为什么血肿不大,患者的症状却那么明显——
虽然硬膜外血肿没有恶化,但脑出血很严重,患者的脑室已经里充满了血液,而且明显发生了扩展。这样下去,很快就会危及生命。
手术刻不容缓。
我又狂奔回诊室,把情形见告凯哥,然后立时关照病房和手术室。很快,手术室的麻醉师和护士们就准备好了,上级年夜夫海涛哥也在赶来的路上。
术前洗手的时候,我还在光彩:“这家伙是个秃顶,省得咱们备皮(剔除毛发并进行清洁)了。”
消毒、铺手术巾、穿手术衣,统统准备就绪。凯哥先在太阳穴位置做了皮肤切口,我和他合营着切开、止血,很快就暴露了颅骨。
这时,海涛哥也来到了手术室,准备正式手术。我们拿掉了一块大约 9 厘米长,6 厘米宽的颅骨,这样就相称于在脑壳上开了一扇窗,预防水肿挤压脑干,然后在侧脑室插入一根管子,把血液放出来,减轻脑室内的压力。
手术做得好好的,海涛哥溘然举头看了我一眼,问:“头部消毒的时候,有没有创造什么分外情形?”
我一头雾水,担心是自己消毒不合规范,当心翼翼地说:“没什么,便是他可能是刚剃的头,脱衣服的时候创造脖子上、锁骨上都是碎头发。“
“问题就出在这儿。”海涛哥的表情依旧专注,但还是可以从语气里听出一丝不满。
“这头肯定是下面的县医院剃的。都备好皮准备做手术了,创造没有家属,害怕没人具名担任务,又怕没人交钱,就把包袱甩到咱们医院。他们都这样搞了多少次了!
”
听了海涛哥的话,我才恍然大悟,怪不得县医院明明拍了 CT,却又把病人送到这里。
之前我还在学校的时候,就听老师们提过医闹。
前不久,楼上的普外科就经历了一场医闹,起因是一个患者结肠癌手术后,吻合口分裂造成肠瘘。这本来属于常见并发症,术前发言里,也讲过这种可能性,但家属张口就要 20 万,每天赖在病房里,搞得全科焦头烂额。
这个人现在身份不明,如果手术涌现问题,或者术后规复不好,家属又溘然找上门来,那我们可真是百口莫辩了。但患者情形危急,想不了那么多,先把人救过来再说。
做完手术,已经是凌晨,幸运的是,手术很成功。把患者送进 ICU 后,我心里默默祈祷这个家伙能尽快醒过来,哪怕是只有痛觉,能够哼唧几声也是好的。
一句感激都没有
第二天下午查房的时候,患者的状况还不错,呼吸和心率都很平稳,捏他手上的皮肤时,也有了躲避动作。
在 ICU 里又住了 2 天,他逐渐清醒。虽然有些迷迷糊糊,说话词不达意,但已经能和别人互换了,还会在半梦半醒中夸护士长得好看。 主任看过后,哀求隔天把他转出 ICU,给其他重症患者腾床位。我们看着 ICU 里空着的两个床位,心里都明白,还是钱的问题。
目前,他的治疗用度已经超过了一万,而这些钱都是医院垫付的,终极还是会摊到每一个年夜夫、护士头上。
就在这天,警察找到了他的家属:
一个看上去六十多岁的屯子老头儿,黑黑瘦瘦的,脸上沟壑纵横,身上穿着当时已经很不常见的蓝色中山装,脚上是险些完备褪色的绿色解放胶鞋。
他的裤子上还沾着泥点,裤脚挽起到小腿,像是刚在地里干完活的样子。
问了警察才知道,这个老头儿是患者的父亲,今年 56 岁,38 岁那年才有了一个独苗。孩子的母亲有慢性肾病,50 岁那年去世了,家里为了治病,一贯找亲戚、邻居借钱。这次来医院,也是和周围人借了一圈,才凑了不到一千块钱。
看到家属这副样子,大家都默默叹了口气——还钱?还是别抱什么希望了。
到了下午,患者的颅内压又升高了,而且术后谵妄(行为躁动、胡言乱语)比较严重,转出 ICU 的事情只能暂缓。我带着他父亲进去探视,这个诚笃巴交的农人看着插满管子的儿子,眼里一直淌泪,僵在那里,有些不知所措。
我又把他带到年夜夫办公室,向他先容病情,完成一大堆的发言和具名。而这个男人只是僵坐在凳子上,双手牢牢扣住膝盖,像一个在接管批评的学生。
我每说一句话,他就点点头,让他具名,就木然地拿起笔,一句多余的话都没有。一个小时的韶光里,他始终没有看过我一眼。
他离开办公室后,我不太高兴:“这个老头儿,我们救了他儿子的命,还垫了医药费,他竟然连句客气的话都没有!
”
凯哥听到了我的不满,过来悄悄跟我说:“这算什么,咱们便是靠治病救人养家糊口的,不要什么事都想着让人谢,不告你就不错了。”
听完这话,我心里更憋屈了。患者本来都准备转回普通病房了,现在颅内压又溘然升高,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万一家属硬要说我们手术没做好,就麻烦了。
由于患者住在 ICU,他父亲不能像其他家属那样睡在床位隔壁的折叠床上,又舍不得住宾馆,干脆直接睡在了消防通道里。保安巡逻的时候常常把他的“床铺”——两层纸板给扔掉。
我见告他,医院后面的小巷子里有日租房,一个床位一天也就二十多块钱,很多家属都住在那里。一听说二十多块钱,他本来呆滞的双眼看了我一下,摇了摇头,又把手里破旧的提包攥紧了一点。
末了,我们和保洁员商量,让他晚上住在放扫帚的仓库里,又找了些纸板当床铺。由于是夏天,温度也不低,夜里他就和衣而睡,算是办理了住宿问题。
不过,他依旧很木讷,一句感激都没有。
出院
这几天,患者的情形时好时坏,不过总体上规复得不错,转入普通病房该当只是韶光问题了。
他父亲除了每天上午的查房和下午三点的探视韶光外,都处于消逝状态。据保洁姨妈说,他一样平常在消防通道的楼梯上坐着发呆,或者去花园转转。
住进仓库的第三天,这个常常消逝的人溘然涌如今护士站阁下,搓动手张望。起初,我忙着干活,没把稳到他,直到保洁姨妈嫌他站在那儿影响拖地,喊了句:
“真碍事,晚上占着我们小仓库,白天又站在这儿碍我的事。”
姨妈说话的声音特殊大,周围的人纷纭看过去。他的脸瞬间涨得通红。 护士长把他叫到一边,问他有什么事情。他憋了半天,冒出一句:“主任上午查完房说,我儿子能从里面出来了,多亏了你们,保住了我儿的命。”
护士长连忙说,没什么,都是该当的。
直到这时,这个男人紧张的感情才终于放松了些。他跟护士长说,如果往后有须要,就去消防通道找他,医院里有什么打杂跑腿的事情,他乐意帮忙。
说完这话,他的脸又憋得通红,扭头去跟保洁姨妈赔笑脸,然后不由分辨地提起姨妈的脏水桶就往水房跑。 正在气头上的姨妈溘然噗嗤一声笑了出来。
那个黑瘦的男人提着水桶晃晃荡悠地走过来,和保洁姨妈一起打扫卫生。 活动几下,他显然是出汗了, 脱掉那件有些破旧的中山装,搭在阁下的扶手上。
来到医院这么多天,他脸上第一次浮现出自然的笑颜。
晚查房过后,我和护士一起把患者从 ICU 推出来,转入普通病房。老头儿早已经守在 ICU 门口,父子俩一见面,一句话没说,都哭了起来。 ICU 的护士说,患者刚醒的时候,总是问摩托车在哪里。原来,他失事时开的摩托,是向朋友借的,他家经济困难,怕摔坏了赔不起。
听到这个,我苦笑一声,心说这几天住院的用度,够买好几辆摩托车了。
回到普通病房往后,患者的状况逐渐好转,毕竟是 18 岁的壮小伙,规复起来很快。附近月尾,他已经能自己在病房里走来走去。也便是说,间隔出院不远了。
这段韶光,他的父亲也从仓库搬到了病房,白天没事的时候,就在走廊里站着,或者守在护士站阁下,看有谁须要帮忙。护士捧着瓶瓶罐罐的注射液,他就过来搭把手;保洁姨妈腰不好,他就主动去打水;饮水机须要改换水桶了,他就一个人扛起来一桶四十多斤的纯净水,胳膊上的青筋清晰可见。
日子一每天过去,正巧,我在神经外科的末了一天,患者可以出院了。
这时我们才知道,过段韶光他还要参加高考。这是他第二次参加高考,之前一年,他都在县城的高中读复读班。
失事那天晚上,有手机的同村落同学和家里打电话,说他家里的土胚房歪了。他一听,急忙借了县城同学的摩托车连夜赶回去,想看看父亲有没有失事,未曾想就在路上出了意外。
考虑到他们家的情形,这次治病我们就先垫付了用度,并且叮嘱他们带好单据,回去办新农合报销,报销的钱再还给我们。至于自费部分的钱,就由医院来出了。
出院这天,医院宣扬科还来拍了一张合影,说是医务职员公益救助困难患者,院报得宣扬一下。
我站在办公室门口,目送这爷俩离开病房。 老头儿转头朝我们看了看,彷佛眼里有泪水,由于他用袖子擦了一把。
我那时学生气重,找海涛哥抱怨:
“这人真是的,咱们救了他儿子,还没要钱,查房的时候从没听他跟我们说过感激。过去看电视剧里面,假如年夜夫仁至义尽到这份儿上,还不得戴德戴德的。”
一把花生米
之后,我也很快离开了神经外科,轮转到泌尿外科和普外科演习。
每天忙得像陀螺一样,又打仗了很多新的病人和家属,那个老头儿的形象逐渐从我脑海中淡去,只剩下一个模糊的影子。 直到十月的一天,我在食堂遇见凯哥,他把我拉到了神经外科病房。 办公室里放着一个很大的蛇皮袋,里面是装得满满的花生米。
护士长正在用小袋子分装,瞥见我来了,她赶紧递给我一袋:“快快快,赶紧拿着。 这一大袋子得有七八十斤吧,那人竟然一起扛过来,还真厉害。 ”
她说的是那人,是颅脑外伤患者的父亲,那个黑瘦的老头儿。
主任本来已经做好了他不还钱的生理准备,没想到的是,几个月后,他不仅把报销的钱带回来了,还拼拼凑凑了三千块钱,说是自费部分的,也还给我们,剩下的他再想办法。
听说,老头儿本日笑着见告大家,他儿子考上了大学,今后便是干部身份,不用再像他一样面朝黄土背朝天了。那一袋子花生便是他送给年夜夫和护士的谢礼。今年收的新花生,刚晒干的。
护士长推脱不掉,只得留下那袋花生,但大家商量之后,决定让他把三千块钱带回去。自费部分就不用再还了,就当是医院声援他们的。
周末,我把花生带回了家,足有一斤多。父亲之前一贯在老家务农,也种过花生。晚上炸花生之前,他挑挑拣拣,创造没有一颗不饱满,没有一颗虫蛀,没有一颗发霉,笑着说了一句:
“不孬,挑过的。”
听着父亲的话,我仿佛看到,一个晴朗的初秋夜晚,黑瘦的老农坐在院子里,就着泛黄的灯光,细心心细地,一颗一颗挑拣着花生米。
从医十年, 我时常想起这一幕
正是这个
不善言辞却又一片赤忱的老头儿
让我能够在纷繁繁芜的医院里
也时候保持着
对善良的笃信和期待
(作者:菲利普年夜夫。本文经由日本北海道大学神经科学硕士 庄时利和 审核。原文略有删节)
(来源:丁喷鼻香年夜夫微信公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