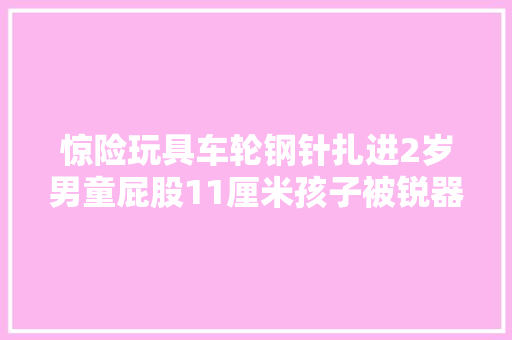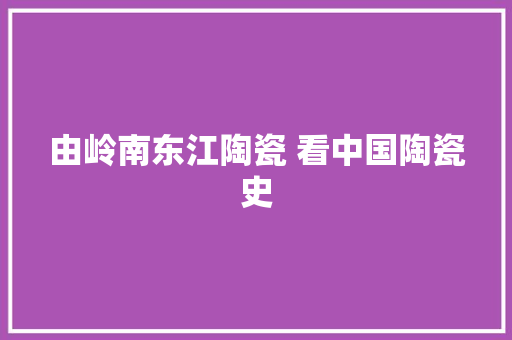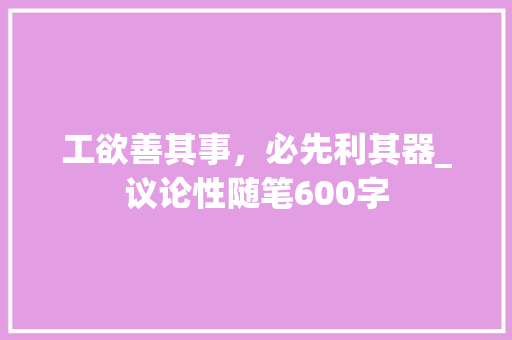世事无常,我们会受伤,为人所用的器物也是一样。冲破了,破败丑陋,难免被丢弃的命运。可在嘉善有这样一个手艺人,一手金缮技艺,化腐烂为神奇,将残缺变为极致的美,让破败的老物件重新焕发生机,他便是嘉善90后金缮手艺人朱墨皓。
修复,守住每一件器物的肃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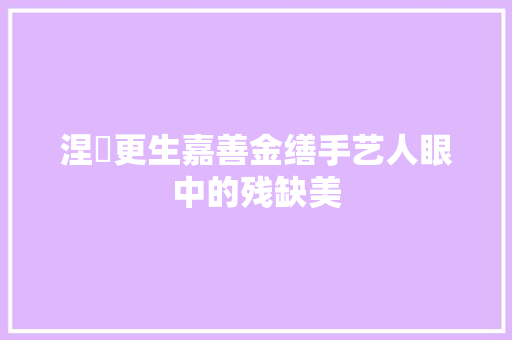
走进朱墨皓位于嘉善县城的事情室,不敷10平米的空间里,事情台、陈设柜、工具箱,还有各色缺东少西的陶瓷、木雕等大小不一的老物件。事情中的朱墨皓,常常在这里一呆便是一天。
因大学主修古陶瓷修复,求学期间,朱墨皓曾经随着老师去过不少文物修复现场,参加文物修复事情。这个94年的帅气小伙谈起器物修复来,眼中满是神采。“过去的器物重实用性,一样平常坏了也就丢了,真正花心思去修复的不多。” 朱墨皓说,专业知识教会他,修复不是创作,而是修旧如旧,还原器物本来的真实,而又不毁坏器物本身,不做过多的润色。
朱墨皓求学期间修复的作品(修复前)
朱墨皓求学期间修复的作品(修复后)
金缮,让朱墨皓对器物修复有了全新的认识。金缮是什么?这是一种以天然生漆为紧张修复材料的修复技艺。大学期间,金缮技艺作为课程内容进入了朱墨皓的视线。“不同于传统陶瓷修复中的锔瓷,金缮无需钻洞钉补,不会危害原器物。” 朱墨皓说,当代的文物修复中有三大原则,可识别性、可逆性、最小干预原则,金缮恰好是这三大原则的完美诠释。
更令人惊喜的是,经由手艺人的巧手,缝隙被绚丽的真金粉饰,与原器物不同的材质相辅相成,形成了另一种独到的美感,残缺的美。无形中,手艺人对器物的理解也被倾注在了修复中,不止金色,银、铜、漆艺皆可为装饰手段,可修复的器物材质浩瀚,除了陶瓷、紫砂制品,也可用于竹器,象牙,小件木器,玉器等等器物的修复。在修复中创作,这让朱墨皓更对金缮一技不克不及自休。
绽放,化残为美再现器物之魂
在朱墨皓的事情室里,惊喜随处可见。残酷的金色爬上了器物周身,有些状似流水细纹,有些似墨迹斑斑点点,因碎裂的随机而幻化出千奇百怪的形态。这些被抚平的“伤口”,让原来已毫无生气的器物找回了灵魂,也换了种“活法”。这大抵便是金缮的意义所在。
为器物授予新生的过程并不随意马虎。在朱墨皓看来,金缮脱胎于漆艺,漆才是金缮的灵魂所在。修补中,用大漆作为粘合剂,将碎片粘合,以漆为底打磨得当,再用金粉、金箔修缮,从而使老旧而破碎的器物重新焕彩。
上漆,光这一道工序就已繁琐无比。漆不能只上一遍,视器物损毁情形,酌情增减,上一层,干一层,循环往来来往,直到达到满意的厚度为止。干燥须要交给韶光,而环境影响不容忽略,温度必须保持在25度,湿度掌握在80%。
金缮修复时,手艺人也会受伤。大漆源自天然树脂,极易引起皮肤过敏,行内话叫被漆“咬了”。大学期间有一次为了修复一个木漆盒,朱墨皓过敏,整张脸肿到眼睛都睁不开,挂了好多天盐水才消肿。这两天,他修复上一件器物时过敏,手上留下的疹子还未完备消退。可是他对金缮的热爱依旧有增无减。
这个月,朱墨皓操持要参加一个学习班,再去深入学习专业髤漆工艺,利用到金缮中。“金缮起于日本,却与中国漆艺渊源颇深。” 朱墨皓说,漆艺,古称“髹饰”,它既为金缮之胎,亦可弃金饰并施以髹饰的工艺。漆的利用在中国的历史十分悠久,在杭州萧山跨湖桥遗址出土了一件漆弓,证明了早在8000年前,杭州萧山跨湖桥的先民已经对漆的性能有所理解并开始利用。
而在家乡嘉善,也曾呈现了一批雕漆工艺大家,如元代的杨茂、张成等人堪为个中俊彦,许多作品传播至外洋。朱墨皓希望,能将家乡的传统工艺传承延续,结合金缮推陈出新,将这种别样的美学艺术,更多地为人所知。眼下,他也正积极方案,打算开办几期培训班,找寻志同道合的人,一同研习金缮技艺。
注:文中部分图片由受访者供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