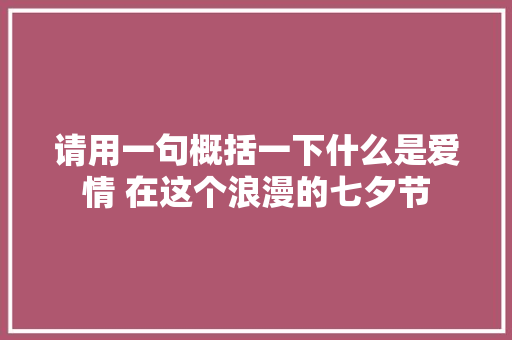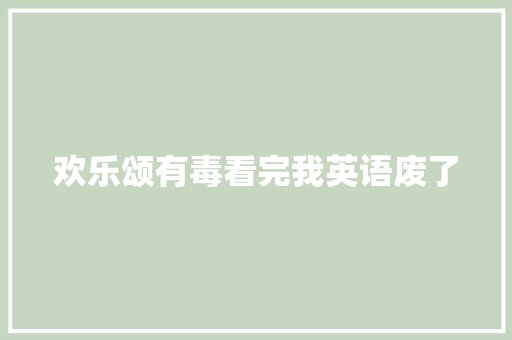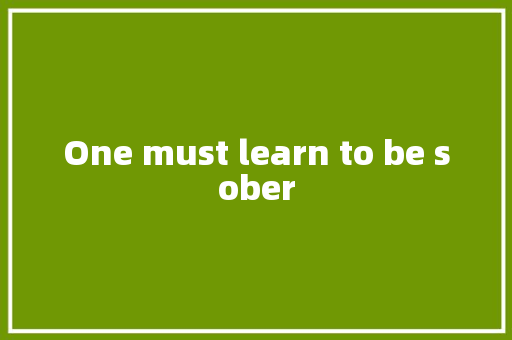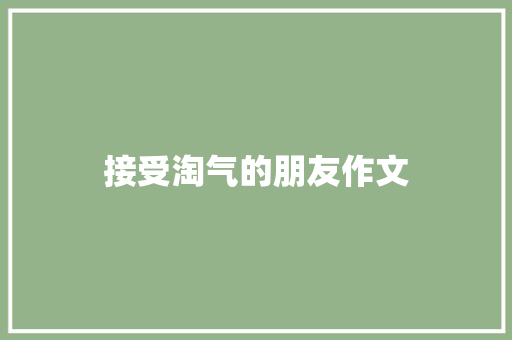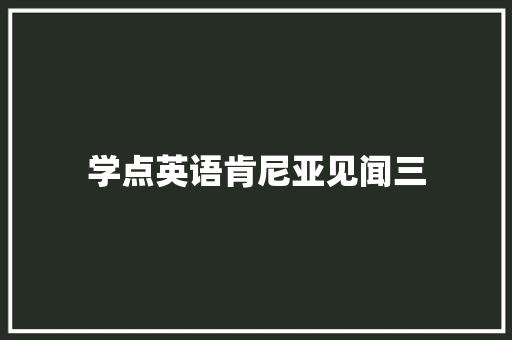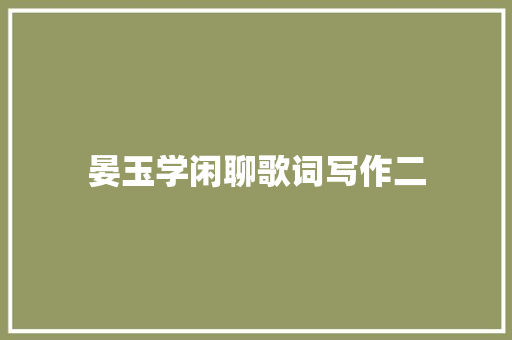《人类措辞的故事》,[荷]加斯顿·多伦著,闾佳 译,读客 | 文汇出版社 2021年6月版
下文中的A是一位英语母语人士,他有着大语种的“优胜性”,B是这本书的作者加斯顿·多伦,他则几次再三“否定”这种优胜性。他来自荷兰,英语是他的第二外语,他在这本书里一共盘点了包括英语在内的20种措辞。他们评论辩论了英语的措辞特质和它的未来,尤其是英语与其他措辞的比拟,还有汉语的天下地位,懂不懂英语在未来可能也不再那么主要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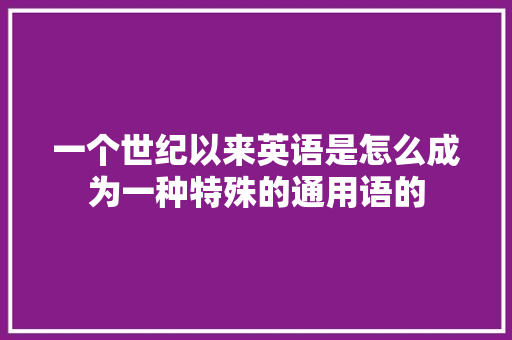
英语成为一种分外的通用语与它的特质有关吗?
A:我们在谈论波斯语时,你阐明了它是若何在一片广阔的地区茂盛了几百年的。而我的母语英语是凭着什么样的特质,霸占了本日这样的主导地位呢?
B:你怎么会以为这个问题事关措辞的特质呢?
A:当然是由于它成功啊。如果它没有一些出类拔萃的特质,就不可能这么成功,对吧?
B:成吉思汗、黑去世病和《天下新闻报》在他们所在的时期都极其成功。油井让阿拉伯海湾从天下财富里分到了弘大的份额。如果条件得当,很多东西都能发达发展。英语等了好几百年,靠着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才迅速蔓延开来。迟至15世纪末,只有300万旁边的人口说英语——而且全都集中在英格兰,其他地方险些没人利用它。当时没有人以为英语有什么内在的特质,能让它注定成为环球通用措辞。这个国家和它的措辞都相称边缘化。直到17世纪初,英格兰和英语才逐渐展现出政治和经济上的潜力。
A:你说的是前往印度的英国贩子吗?我是说,他们为大英帝国奠定了根本,并将英语传播到全天下,是这样吗?
B: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如此。大英帝国幅员辽阔,是有史以来最大的帝国,它将英语的“根”和“芽”传播到了天下各地。但在大英帝国存在的大部分期间,最靠近天下通用措辞地位的是法语。英语直到第一次天下大战之后——也便是说,是在所谓的“英国世纪”正要结束的时候——才开始寻衅法语的地位。实在,要等到第二次天下大战打完、美国世纪开始,英语才逐渐显得像是一种天下通用措辞。它毋庸置疑的霸主地位来得更加晚,要等到冷战结束后,俄语不再是竞争对手,英语才登上宝座。
A:俄语?竞争对手?你一定是在开玩笑。
B:我没有。诚然,在成本主义阵营,俄语处在边缘地位,但在苏联的势力范围内,利用俄语的范围要广得多——20世纪70年代仍有很多人利用俄语。中国险些也不重视英语。就连在拉丁美洲这个“美国的后院”,英语在那时也没什么存在感。当然,我并不是说英国在英语的扩展过程里没有发挥任何浸染——它发挥过,尤其是在北美洲和英联邦国家。但在其他地方,英语是美国通过跨国公司、消费品、电视节目、电影和音乐传播出去的。英语的传播办法和其他通用措辞大致相同,它跟随权力、金钱以及生活中的各类美好事物而渗透。靠着当代科技的发展,一种措辞如今能够在世界大部分地区都得到强大的存在感。
Par avion(法语:航空邮递):19世纪,邮政做事推广至环球,此时法语仍是首选措辞
A:1/4的人会说英语。
B:是的,大概。这算下来差不多是15亿人:3.75亿人以它为母语,还有超过10亿人把它作为第二措辞。这些数字听起来很真实,如果我们把那些英语说得很烂、让人难以理解,或是由于紧张而不愿意说英语的人都包括在内的话。
A:我仍旧认为英语的崛起肯定是由于它的某些特质,尤其是它大略的语法。你自己就说过,由于语法大略,以是波斯语成了全体波斯帝国建筑工人的通用措辞。
B:不完备是。我说的是,由于波斯语成了建筑工人的通用语,结果,波斯语的语法被大大简化了。它失落去了大部分的“繁芜形态”——大略地说,也便是它的词尾和单词的性别。回到维京人在英格兰定居并与当地女性结婚的案例,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英语身上,这些措辞殽杂的家庭就跟措辞殽杂的波斯建筑工地一样,带来了一种简化的措辞。英语很少有词尾,也没有性别,这叫它变得更随意马虎节制。
A:以是它才成为一种天下性措辞啊,正如我所言。
B:你的结论下得太早了。英语的简化发生在1000年前,而从那时起,除了最初保留的繁芜细节之外,它又发展出了大量新的繁芜细节。作为非英语母语利用者,我可以向你担保,英语语法比你想象的更古怪,更难懂,尤其是动词时态。比方说,现在进行时和一样平常现在时(如she’s deciding和she decides)的差异。接下来还有was going to do、would do、have been meaning to do、was going to have it done和would have been going to do等无穷无尽的奇妙之处。
A:我们真的会说“would have been going to do”(这是现在进行时的虚拟语气)吗?我有点说不准呢!
B:如果你都说不准,我又怎么说得准?类似的奇妙细节还有很多。强变革动词,不只会改变元音,有时还会改变辅音。冠词(定冠词、不定冠词,乃至完备没有冠词),也比乍看上去繁芜得多。介词的利用也很麻烦,比如“looking at someone”(看着某人)和“looking on someone”(指望某人)或者“looking to someone for”(寻求某人的帮助)。此外,还有那令人望而生畏的、广阔的动词短语领域,比如“getting by on something”(靠某事度日)、“getting along with someone”(与某人相处)和“getting on for so manyo’clock”(靠近、差不多几点了)。
A:但这些介词不是语法词尾吧?
B:它们是英语词汇的一部分,但这是其余一回事。而且介词非常多,我赞许这是英语的光荣!
当然,有些例子处在语法和词汇交汇的灰色地带。但英语词汇量弘大本身便是个问题。我敢肯定,在你内心深处,你认为这是个最值得骄傲的地方,但对我们非母语利用者来说,这太胆怯了。国际通用措辞该当是高效的,而不是奢侈夸年夜的。经济,不摧残浪费蹂躏;节俭,不挥霍;俭省,不铺张;够用,不……
A:好了,你说到点子上了。词汇太多了,我知道你说的是这个意思。但也可以从这个角度看:我们的词汇稠浊了日耳曼语和罗曼语,比如get和obtain(都有“得到”之意),或是street和avenue(都有“街道”的意思)。这让它成为空想的通用语,不只德国人和斯堪的纳维亚人随意马虎学,法国人和西班牙人也随意马虎学。
B:你真的找说西班牙语的人问过他们是否认为英语随意马虎吗?我有个强烈的预感:他们不会以为英语随意马虎。他们会创造,短语动词和介词无法理解,他们的舌头无法顺利发出所有英语元音的声音……倒不是说英语并不适宜作为天下性措辞。我的意见是,它并不特殊得当。它有些优点,比如没有词尾和性别,但也有很多缺陷:发音难、拼写混乱、词汇过多、语法相称古怪。
A:但它的优点呢?它用场广泛,适应性强。它很随意马虎创造新单词,并从其他措辞中接管单词,还有它出名的平等主义、刀切斧砍——不像法语,还有“你—您”之类的差异。
B:很遗憾地说,这是一堆毫无根据的老套说法,是对措辞学知之甚少的人散布的。所有措辞在有须要的时候都会创造新词。英语可以自由地从其他措辞里借用是没错,可这也没什么好坏之分——借用只是扩展词汇的一种路子罢了。其他还有什么地方,英语能说得上灵巧呢?身为局外人,我常常碰到一些合理的词序却遭到语法禁用的情形。比如,在许多措辞里,“Her I like best to kiss”这样的语序都能很好地指明一个人最想亲吻谁,可在英语里你这么说,就会显得像是《星球大战》里的尤达大师(Master Yoda,总是说倒装句)。
至于平等主义——没错,英语没有语法上的人称差异,大多数欧洲措辞都有,只是程度较轻;一些东亚措辞就很麻烦了。但英语本身也并不直接,无关民主。在现实生活里,用英语互换须要措辞礼仪知识。在很多措辞里,你可以直接问别人想要什么,可在英语里,你必须问“they would like”或“would prefer”,你能“替他们做些什么”“你能否帮助他们”,或者诸如此类令人费解的繁芜公式。如果我在点一品脱啤酒时直接说“我想来杯啤酒”(I want abeer),其粗鲁程度可能不亚于对着法国做事员说“tu”。这还不包括大量的“请”和“感激”,大量的人际互换都须要它们来润滑。我不是说这是坏事——实际上,这挺适宜我的——只不过,它也并不随意马虎。
A:至少,英语不是汉语那样的音调措辞吧,这肯定算是个上风!
B:在这一点上我赞许你的意见。音调太难于把握了,以是,对一种环球性措辞来说,没有音调是件好事。但英语发音的难点在其他方面。我花了好多年才能在说和听这两方面都能分辨清楚had和head、poor和pour、coughs和cuffs,或是leaf和leave之间的差异。
A:你便是故意要跟我抬杠,对不对?
B:不……真不是。我学越南语的时候就必须学习音调,我创造它很难,但还是能学会。英语发音里的奇妙之处同样如此,即便是到了现在,在表示强调的时候,我有时仍会把leave缺点地读成/leaf/,把any读成/annie/,不一而足。我可足足练习了40年啊!
真的,有很多人把英语作为第二措辞来学习,并不虞味着它很随意马虎!
这是项艰巨的事情,而且永无止境。
A:啊呀,我还以为我们已经为天下带来了空想的通用语呢。难道我们这些说英语的人完备受到了误导吗?
B:没必要对自己太苛刻。你对英语的觉得,属于另一种更宽泛的模式。一种措辞(或者说,任何一种措辞)得到广泛的主导性地位往后,不知不觉中,人们便开始奉承它:它有多么伟大、多么丰富、多么具有音乐性,诸如此类。
实际上,所有的紧张措辞,都有着贫贱的出身:阿拉伯语来自沙漠部落,波斯语和梵语来自草原上的马背民族,法语来自罗马士兵和被击败的高卢——然而,过了几百年,这些措辞就变成了历朝历代措辞造诣的顶峰。在利用者眼里,阿拉伯语和泰米尔语是神圣的,拉丁语和希腊语是唯一适宜文学的措辞,俄语是无产阶级浴火重生的措辞,法语是唯一符合逻辑的措辞。
现在轮到英语了,人们说英语大略、易唱、直接、清晰、灵巧,外加其他很多优点。它很可能比俄语随意马虎,比德语更适宜用来唱歌,比爪哇语更直接。但英语跟天下语和大多数克里奥尔语比起来就没那么随意马虎,用来唱歌不快意大利语,跟……(我不知道!
)比起来也没那么直接。直接与否,根本不是措辞特色。荷兰人直白得惊人,而同样利用荷兰语的佛兰德斯人就没那么直接了。
不才一代人那里,
英语还能保持现在的地位吗?
A:天下经济重心正从美国转向亚洲。那么,一旦这种情形发生,英语还将是天下措辞吗?
B:我敢肯定,至少不才一代人里,英语将连续保持现在的地位,毕竟,眼下全天下就有数亿儿童正在学习英语。但在那之后会发生些什么?这些孩子的孩子们还将学习英语吗?不一定。
二三十年后,如果他们以为自己的孩子把韶光花到别的地方去更有利可图,学英语的趋势就会逐渐低落。这样的事情从前就发生过。我祖父用法语给我父亲写信,由于他认为法语既有用又时髦。在我祖父是个小孩子的时候,也便是20世纪初,情形的确如此,可到了50年代,也便是他给儿子写信的时候,法语早就不复当初盛况了。这样的转变贯穿全体人类文明史。
A:这便是为什么虎爸虎妈们如今会让孩子学习汉语。他们做得对吗?
B:他们相信普通话本日有用,来日诰日会更有用。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中国将成为下一个超级大国,把赌注押在它上面肯定不会输,以是,会说汉语必定是一项值得拥有的技能。但如果你的意思是,“汉语会成为环球性的通用语吗?”这就完备是另一回事了。很多人认为,经济上的主导地位将导致政治上的主导地位,而政治上的主导地位又将导致措辞上的主导地位。但措辞学家大多并不认同这样的不雅观点。
A:为什么会这样呢?措辞的推广不正是跟国力的壮大挂钩吗?
B:不完备是。大卫·克里斯托(David Crystal)和约翰·麦克沃特(John McWhorter)等著名措辞学家认为,从前推动一些措辞成为通用语的旧有政治和经济机制,这一回很难发挥浸染。缘故原由之一是,汉语太难了。不只对我们难,对东亚以外的大多数人都难,乃至对他们自己也很难,由于汉语的笔墨书写效率比较低。
A:还有别的什么缘故原由吗?
B:那便是临界值。过去,哪怕是最成功的通用语,要么仅在部分地区利用,比如中东的亚拉姆语或西罗马帝国的拉丁语,要么仅限环球精英利用,尤其是18—19世纪的法语,它是当时的环球外交措辞。它们的遍及,有赖于利用者的权力。
等阿拉伯人征服中东地区,阿拉伯语取而代之,亚拉姆语便衰败下去,仅作为部分民族的母语存在了。法国在拿破仑败北之后失落去影响力,外交官们也逐渐用英语取代了法语,只管两者之间存在一个世纪的韶光差。
然而,本日的英语已在环球各地传播——这是一张由利用者构成的环球性网络:在西方和英联邦诸国拧结得紧密一些,在其他地区则较为疏松。而措辞跟其他各种通信设备一样,利用它们的人越多,它们就越有用。我疑惑,英语已经跨过了一个阈值,任何其他措辞都没有机会成为新的通用语了。
A:那便是说,还是英语赢了?
B:暂时如此。
A:又来了!
你刚刚才说没有任何其他措辞能击败它。
B:我是这么说的。但英语现在的胜利并不一定意味着终极的胜利啊。还记得西欧的拉丁语碰到了什么样的情形吗?
A:它演化成了多种罗曼措辞(Romance Languages)?
B:是的,它变成了法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和其他一些措辞。但这只是故事的一半。故事的另一半是,略经简化的拉丁语,在此后的1000年里连续保持了通用语地位,只不过,仅限于宗教精英和知识精英利用。英语的未来可能也与此类似。
一方面,它可能会发展出地区变异版,在当地措辞(比如印地-乌尔都语、斯瓦希里语或韩语)的影响下,终极变成彼此分离、互不理解的措辞。就像如今众所周知的印度英语(Hinglish)、乌干达英语(Uglish)和韩国英语(Konglish)一样,兴许这便是英语未来的前兆。
另一方面,随着英语母语人士所占比例越来越小,这种国际通用语的繁芜性大概也会随之削弱。许多晦涩的习语,如“to nail one’s colours to the mast”(公开表明自己的主见并坚持到底)或“not to put too fine a point on it”(打开天窗说亮话)等,将不再被视为这种措辞的一部分,它们仍是本土英语的一部分,但不属于国际通用英语。如果说,到了一定阶段,某些语法特例会遭到抛弃,比如swim的过去式变成了swimmed、sheep的复数形式变成sheeps,我也并不会以为惊异。我猜,这在你听来切实其实像是对英语处以极刑……
A:真胆怯。还有什么其他更随意马虎接管的场景吗?
B:有一种技能上的补救办法:即机遇器翻译。
A:哈,巴别鱼!
《银河系漫游指南》里的宇宙翻译机!
B:完备精确。或者,更确切地说,它的硅质替代品:巴别芯片。你对我说马来语、葡萄牙语或旁遮普语,我从耳机里听到的是我所选择的任何措辞。唯一的问题是,我们现在还没法完备确定,它是否会像科幻小说或者谷歌的科学家宣扬得那么顺畅。一些措辞的机器翻译越来越好,但另一些措辞的机器翻译还相称糟糕。而且,这些都基于书面文本。如果输入的是自然措辞,又带有地方口音,还来自喧华环境,那么,如今的软件就会摔跟头了。
A:这些问题在几年内肯定会完善起来吧?
B:大概吧。经事实证明,机器翻译比预期中要繁芜一些,但大型科技公司彷佛的确在大步提高。如果巴别芯片成为现实,英语的通用语地位就将不保,由于不会再有太多人费心学习母语之外的任何措辞。
A:那么,跟讲外语的人互换就像在看配音电影一样?
B:有一点不同:你同时还能听到原版语音。或者,更确切地说,会提前听到原版语音,由于我猜机器翻译会略有迟滞。
A:这样说来,人工智能有望脱手援救。要不然便是汉语取而代之,要不然英语会一贯占上风,直到天下末日。再或者,它会变成一种缺少特点的“环球语”,外加各种地方变体。你会怎么押注?
B:从中期来看,我认为,英语将连续保持主导地位,同时经历着地区性变革,外加巴别芯片将发挥越来越主要的浸染。从长远来看,我估量人工智能将会取代它——在措辞方面,当然还有许多其他方面。
A:那时英语的末日就到了吗?
B:不一定。本土式英语可能仍旧是政治家、外交官、知识分子和商业上层人士等环球精英的标准用语。与此同时,亚洲和非洲国家的地方英语将变得越来越具有局部地域特色。但是巴别芯片可能会妨碍环球语的兴起。感谢上天创造了科技的奇迹,只不过是不太可靠的奇迹。在我想来,机器翻译得到完善的韶光不会太短,但是,再用10年旁边的韶光,它大概就足以让大量的人相信学习英语并非必要——而且,它险些肯定会强化许多英语母语人士的信念:除了英语以外,不必再学其他措辞了。
A:这难道不是一件好事吗?
B:这对双方来说都是巨大的丢失!
和现在一样,大多数英语母语人士将错过节制双语的乐趣——思维的敏捷性、对其他文化的更好理解,以及第二措辞带来的无尽惊喜。但依赖巴别芯片来理解英语的人也会输。哪怕你是荷兰人,英语也是一种学起来颇为恼火的措辞,可一旦节制了它,便是一件了不起的事。你可以阅读来自天下各地的经典文学作品,亲自体验很多最棒的电影。伊丽莎白一世的莎士比亚英语,或许会让我摸不着头脑,但假如给刚刚才牢骚满腹地抱怨英语词汇量太多的我塞上一本20世纪初诙谐作家伍德豪斯的小说,一翻开书就碰到这样一句话,一定会让我乐不可支:Intoxicated?The word did not express it by a mile. He was oiled, boiled, fried, plastered,whiffed, sozzled and blotto.(这句话可译为:“喝醉了?这个词根本没说到点子上。他微醺了,晕乎了,翻滚了,踉跄了,上头了,烂醉了。”)
原作者 | [荷]加斯顿·多伦
编辑 | 申婵
导语校正 | 李世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