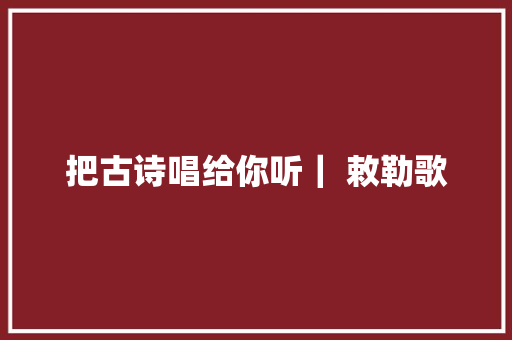人的灵感每每在不经意间涌现。
那天打开电视,正在播放蒙古族歌手腾格尔演唱《敕勒歌》。腾格尔的演唱辽远豪放、声情并茂、荡气回肠,自然赢得了耐久不息的欢呼和掌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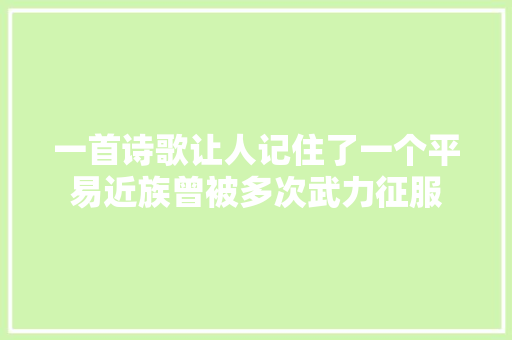
对《敕勒歌》的喜好与生俱来,缘故原由很大略,由于它是歌唱家乡的歌,歌中唱到的敕勒川便是我的故乡。可惭愧的是,已到古稀之年,对《敕勒歌》的留恋依然勾留在耳熟能详、随口吟咏,以慰乡愁的层面。
一个可以产生不朽之作的民族,自然会引发人们的兴趣。探究《敕勒歌》,当然要理解这个很多人并不熟习的敕勒族。
敕勒族原居贝加尔湖一带,秦汉时称“丁零”。东汉往后,蒙古高原上的匈奴族逐渐衰落,一部分南下融入中原,一部分西迁欧洲。“丁零”人乘虚南下进入漠北草原。敕勒人由于利用一种“车轮高大,辐数至多”的车辆,中原人称其为“高车”。在历代中原王朝著述的文献文籍中,多用“高车”而鲜用“敕勒”。至今在内蒙古草原上仍有牧民们利用的勒勒车,听说便是敕勒人的高车演化而来的。
很长一段韶光,蒙古高原生动着许多游牧民族。匈奴往后,比较强大的便是鲜卑和柔然,敕勒族属强胡夹缝中的杂胡之一。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敕勒人赶着勒勒车,吆着牛马羊,哪里有草哪里牧,哪里有水哪里住,在运动中求得生存和发展。他们的活动办法好似流浪者,对老天有着极大的依赖性,而不断的追逐又带有一定的主动性。敕勒人是牧马养畜的好手,加之长于造车,熟于工匠,因此他们活动的地盘人丁茂盛,“马畜弥山”。这便使得鲜卑人和柔然人垂涎三尺,成为他们劫掠的目标。
陶牛,北魏,现藏敕勒川博物馆
据《晋书》《魏书》记载,公元357年、367年、390年、399年,前燕和北魏曾对敕勒人进行过多次武力征服,每一次都抢夺了大量的人口和畜生,还有其他财物。北魏拓跋政权把从漠北掠来的敕勒人强迁到漠南,称之为“敕勒新民”。“新民”有别于战俘,不按奴隶和奴婢对待,而是当作普通百姓。《魏书·高车传》中记述了这样一件事,世祖拓跋焘征讨柔然大胜回朝,听说一千里外的高车人居住的地方“人畜甚众”,就派一支军队去征伐,“高车诸部望军而降者数十万落,获马、牛、羊亦百余万,皆徙置漠南千里之地。乘高车,逐水草,畜牧蕃息,数年之后,渐知粒食,岁致献贡,由是国家马及牛羊遂至于贱,毡皮委积。”这里讲到两个数字,“数十万落”和百余万头畜生,似难以置信。“落”在当时是指帐落,属数量单位,即是户。一落大体上指三至五人,那数十万落,最少有上百万人口。一个小小的高车部落,在1500多年前生产力不发达的草原上,一下子被掠走了上百万人口和百余万头畜生,这数字自然是有些浮夸了。
况且,我对《魏书》中的一些数字也多有迷惑。比如《世祖纪》中记载,世祖“行幸漠南,十一月丙辰,北部敕勒莫弗库若于,率其部数万骑,驱鹿数百万,诣行在所,帝因而大狩以赐从者,勒石漠南,以记功德”。这里讲的敕勒酋长率“数万骑”“驱鹿数百万”均不合常理。天子行猎,一个部族酋长带几万骠骑来这还了得,至于驱来数百万头野鹿更是天方夜谭。天空飞来数万只大雁也会遮天蔽日,那地上赶来数百万头野鹿是何等景象?
不过,从《高车传》中那段话里,倒是可以得到这样的信息,便是北魏政权对劫掠来的敕勒人还算宽容,一没屠戮,鸡犬不留,二没把他们当作奴隶,剥夺他们的人身自由,而是把他们作为“新民”安置在漠南的千里之地。我推测这千里之地便是阴山下黄河边的千里沃野,中央地带便是现在的土默川和河套平原,也便是当时被敕勒人称之为的敕勒川。
那时北魏王朝的统治者们可能还不睬解生产力的道理,但他们懂得人是宝贵的,有了人,又有这么好的草场,让这些敕勒新民乘高车、逐水草,便会喂养出更多的骏马、牛羊,创造出更多的财富。因此,没过多少年,敕勒川上便涌现了“风吹草低见牛羊”的繁荣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