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骗子能懂爱情吗?」
从欺骗到装扮,从谎话到戏院,在虚情假意中碰撞出真情流露,朴赞郁的《小姐》无不勉力地皮旋在「真/假」命题树立,并且以这个「真/假」分类再转化为独属于两人情意互换的戏剧性风格。就此而论,《小姐》分成三个段式的形式呈现,就不仅只是为了剧情反转上的需求,也便是说,我们对这三段体的理解不应勾留在「第一段是假相,第二段是原形」这样的认知,这种认知背后所预设的「真/假」二元对立,实在反而正是这三段体的构造意欲瓦解的目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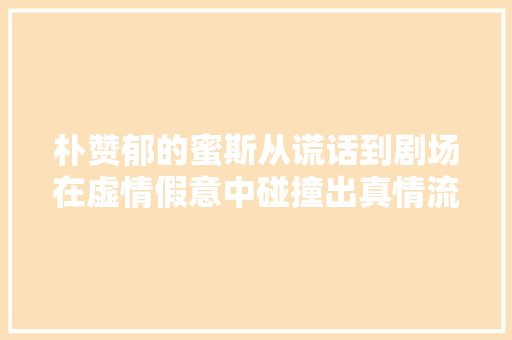
深层来看,朴赞郁实在是在第二段的翻转原形的过程中,让「真/假」的分类成为两人之间感情互动的戏剧风格,进而松动「真/假」固定的边界,让其在不同脉络中有被重新划定的可能。
《小姐》剧照
原来两人分别都认为,自己才是知道原形的人,并透过欺骗的行为去利用对方。但是当两个人决定互助往后,他们反而是透过「连续扮演」自以为知道原形的人,去欺骗当初付与他们进行角色扮演的伯爵。透过「拷贝」让「正版」损失了他的「真实」。
这种透过拷贝去解消正版的逻辑,正是两人在剧中第一次性爱画面的互动核心:两个人由于各自被给与的角色分配,将伯爵对两人的想像配置在互动当中。女仆作为伯爵情欲的代言者,仿若装扮成伯爵试探秀子的心意,秀子则进入到伯爵暗示给她的身体希望的配置与边界,原来两人欺骗对方的行为,反而转变成一个人装扮成伯爵,另一个人装扮成伯爵希望的工具,架设出两人情意互换、角色扮演的戏院。
《小姐》剧照
著名的女性主义学者巴特勒主见:当身处在将希望异性恋化的生产机制中,面对着将性别的划分给均值化,同时让人误以为此划分是「天生自然」的系统编制时,我们能做的,并不是去勉力探索、对「建构」之前的「原初」进行复归,而是必须透过「装扮」的手段,将当下被视为自然的事物给戏院化,以揭示出这些被视为自然的事物本身的虚构性,拆除掉正版与拷贝的主从关系,将自然转化成为一种「风格」。秀子和女仆正是透过「装扮」来剥夺异性恋自然性和原创性的流传宣传,将压迫者给与的受压迫者身份转变为两人同道关系中的展演风格。
巴特勒认为,当我们企图设定一个超越文化历史的阳性主义时,我们所想象出来与之反抗、作为阳性主义「异己」的「女性」,实际上仍旧殖民于犹如阳性主义一样平常、代价单一化的预设之中。「殖民」不仅只是历史上侵略者管理被侵略者的关系,同时更意味着地缘上的「中央」与「边缘」──更深一层来看,它还代表一群人笼罩在一套以单一化代价为「中央」的讯断体系中。
因此,巴勒特认为在单一化代价的殖民状态下,我们与之面对的办法并非是透过设定另一个超越不同脉络的环球化主体与之对抗,也不是设定一个全面反对异性恋的女同道主义,而是将我们以为是自然的性别身体及由之延伸而来的性别身份,在不同的脉络中重新表意,去揭示出我们对身体的感知模型与行为表现如何被文化与政治形塑,而详细的操作正是透过装扮与模拟的性别屡践,将既有被视为「自然」的性意识、性别身份,变成戏剧性的风格展演。
「换句话说,女同道婆希望的目标(而且明显她不但一个),既不是被抽离脉络的女体,也不是界线分明且强加其上的男性身份,而是两者进入情色的相互游戏(erotic interplay)时的不稳定性。」。
《小姐》剧照
这种透过「重复」、「拷贝」、「变装」来重新展演对付「正版」、「真实」本身的建构,渗透在这部电影的所有细节当中。正是由于我们不能去脉络地设定一种超越脉络的女性主体,或是各个文化都一体适用的自然女体,以是我们应该把稳:整部电影面对的帝国主义并不仅限于「性别」这个主题,我认为导演朴赞郁更是故意将这样子的故事放置在韩国本土的历史情境当中,《小姐》将原版小说中的故事移植至韩国的日本殖民统治期间,只管是在日英稠浊风格的邸宅空间中展开,但是故事开头的行军画面却早已提醒我们,不能打消掉日本殖民的背景对其进行理解。
在整栋建筑空间中,日语是符应于整栋建筑物运作的官方措辞,主人讲日语,主人与伯爵沟通讲日语,秀子朗读书籍时讲日语;相对而言,韩文则是作为一种私密措辞而存在。日语的「官方」对应的是诉说日语时,人物状态处于被权力的法律系统形塑的身份之中(亦即,人物正表现出他所处在的代价讯断系统中视为合法、乃至是空想的身份),因此在剧中,当人物「作戏」时,利用的这天语,但是当人物暴露至心时,利用的却是韩文。
《小姐》剧照
这样的设定有趣之处,并不在于将韩文诉说的情境与「至心」进行贯串衔接时、看似展现出的对韩国主体的认同,而是透过人物「欺骗时利用日语」这件事,将「日语」与「装扮」的意涵贯串衔接在一起,戳穿出推动人物「应然行为认知」背后的角色身份,本身便是被建制出来的。
秀子的朗读教诲,表示的正是措辞如何建置出人物行为的疆界、禁忌与自我认知,只管他阅读的素材看似都是打破禁忌的情色作品,但是禁忌从来就不对立于希望。实情反而是,禁忌与希望是共生关系,禁忌不但创造了希望,同时给定了希望的边界,规训了身体与情欲的感知模式,同时让人认定这样的感知模式是「天生」的。
《小姐》剧照
然而原来在朗读过程中受到规训的秀子,却倒转她犹如舞台傀儡般的身份,一手主导魅惑在场所有男人的戏码。确实,原来她在舞台上的魅惑行为,不过便是为了勾引坐下的搜藏者信以为真购买赝品,但是当秀子念着萨德风格的作品时,当她阅读着《金瓶梅》女女试探彼此心意的桥段时,被朗读被展演的文本内容,与文本外的情节穿插,仿若便是念着文本的秀子正在主导着现实事宜依照文本内容发展。
当小姐在舞台上扮演着叔叔要她上演的变态戏码时,当她按照情节惟妙惟肖地成为既是说书人、又是演出者,既察看犹豫又参与地演出双手逐渐勒紧脖子的剧码时,坐下的伯爵仿佛参与个中地涨红起脸来;当她手起刀落演出鞭笞的情节时,下一幕正是伯爵为了达到取信的目的而忍受一次又一次的鞭鞑。
《小姐》剧照
你说,在这里,究竟是众位意淫的男性迫使着秀子上演着迎合他们的苦情剧码,还是实在是秀子(不愿定这里要说小姐还是秀子)在这个装扮的过程中,真正地操控那些身陷个中的痴傻男人?
当秀子窥视着伯爵和叔父的对话时,伯爵说:「她的身体冷得像是尸体。」在一旁隔着墙壁窥伺的秀子,彷佛将计就计地将这样的身体想像移植到自己身上,演出一场迎合伯爵想象的剧码、以勾引伯爵自以为可以用这套想像操纵自己的绝顶好戏。伯爵口口声声说这场诱骗戏码是为了钱财,而不是觊觎秀子,但是当他们成功逃到日本时,他却用了韩文对秀子做了告白的暗示──你不禁会疑惑觊觎钱财的诡计,才是伯爵掩饰笼罩自己追求秀子所精心打造的布局。就此而论,你也会喜好上伯爵这样一个可爱又故意思的角色。
《小姐》剧照
究竟是谁操纵了谁?《小姐》剧名是将焦点集中在秀子身上。秀子在姨父的阅读教诲中被规训出了「禁忌」的边界;在男人们的瞩目下被配置了身体希望的边界;在殖民情境下,被作为能够分发「身份」给男人的交流物,被众人认为是养在深闺几于发疯的空壳傀儡,一个来自不同阶级窃盗集团的纯挚少女,在她交杂着诡计与纯挚的行动中,适值地撬开了秀子的心房,说是谁诱惑了秀子,还是从头到尾,都是秀子上演让大家以为她被诱惑的剧码呢?
当秀子穿着男装经由海关,当秀子拿掉胡子在船上转身对淑姬露出甜美的微笑,是我整部电影最被触动的一个画面。装扮成异性恋的淑姬与秀子,成功骗过了这套讯断系统,移离于其外,就符号意义的层面而言,她们完成理解构、离题、「偷走」了性别角色的既故意涵,解开单一代价中央的殖民束缚。而面对殖民情境乃至是殖民留下来的影响效力,《小姐》彷佛也在表明:真正的应对之道不是虚设一个在殖民影响之外的「原初」去进行复归,而是透过将殖民情境下被迫植入的身份不断「重复」的过程,去考试测验进行重新表意。
正由于身份是在重复制约的过程中被生产出来的,身份的颠覆,也仅只能在重复之中去探求越界的能动性。
《小姐》剧照
回归到秀子和淑姬之间,这个诱惑众生的大好戏码,对外是欺骗压迫自我的牢笼,对内却是她与淑姬两人情意戏院的角色分配。秀子领悟了天真与蛮横的戏精形象,与淑姬的纯洁烂漫相互补衬。秀子的作戏引发出婌姬自以为成功欺瞒的纯洁,而婌姬自作聪慧的纯洁反而转化秀子的作戏、成为一种纯洁,只是为了凸显对方纯洁而非欺骗对方的作戏。她们在两人关系里头重复了一次他们原来的人格形象,但这一次的重复,却是既有的形象被放置在两人情意互换上,产生了裂解、离题、交融,仿若他们原来的形象,便是为了嵌合对方而量身打造的。
「骗子能懂爱情吗?」婌姬不屑地看着伯爵。「骗子能懂爱情吗?」秀子冷眼听着伯爵的告白。角色扮演是虚假的,但这个问题的答案不在反面的「老实」,而在于碰着了「我的他/她」之后,才创造,原来我虚假的角色扮演,都是为了等待和造诣和与对戏的情意游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