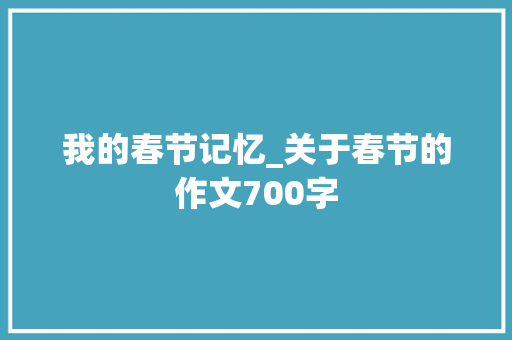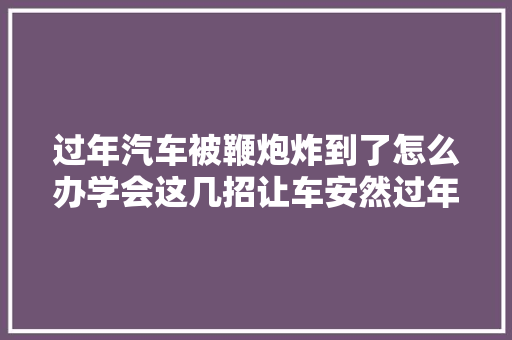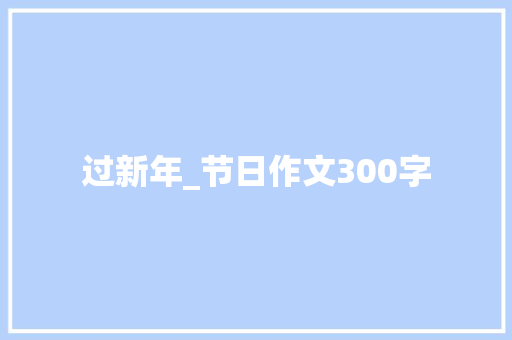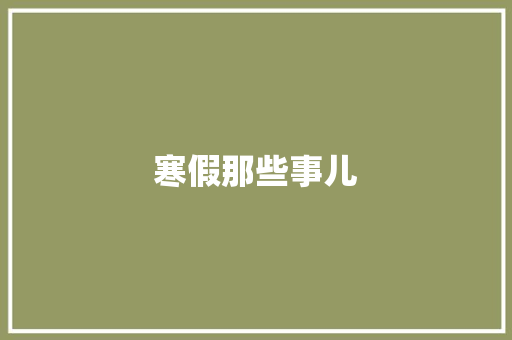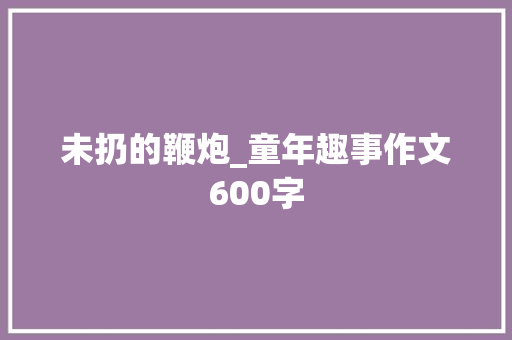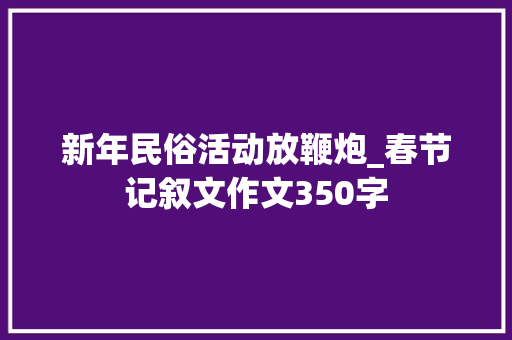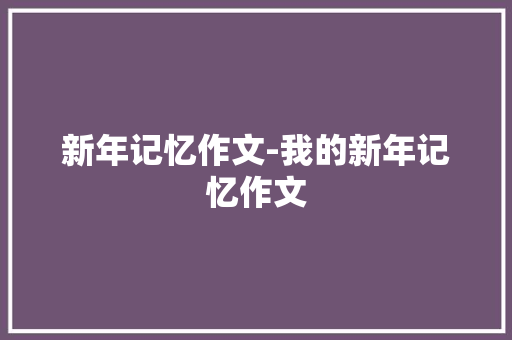除夕夜当晚,在河北地区很多村落都有 “烤把子、放鞭炮”的习俗,图得一个避邪消灾、喜庆、吉利的寓意。
今年,随着“禁燃令”的下发和履行,村落里大部分居民不再燃放鞭炮,“烤把子”的人数也随之骤减。在很多村落民眼中,不烤把子、不放鞭炮,这个年的年味就淡了许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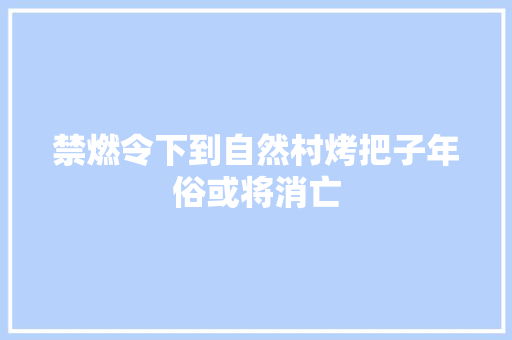
影象:
世代流传的火崇拜仪式
2018年除夕那天,62岁的王有忠带着6岁的孙子来到村落西的河沿割芦苇。他在为一年一度的“烤把子”做准备。
在河北省黄骅一带,有水的地方生满了这种高大的芦苇、禾草。到冬天,芦苇干枯变黄,常被人们割来当柴禾烧。而在除夕这天,芦苇的浸染则不同,是当地居民“烤把子”的首选。
不仅黄骅,连同附近的沧县、盐山等地,很多自然村落在过年时多有“烤把子”的习俗。彷佛是与古代先民们在野外围着篝火舞蹈歌唱相仿,“烤把子”带有火崇拜的味道。除夕那天,家家户户会把芦苇扎成腰粗的捆(没有芦苇也可玉米秸秆代替),竖在自家门前,待到傍晚天色一暗,将芦苇把子点燃,让火舌高高蹿起来。
炮竹与篝火是“标配”。每家都会为这个篝火仪式准备十几串乃至二十几串鞭炮,与火把一并点燃,家家户户的鞭炮声噼噼啪啪连成片,讨得避邪消灾的寓意。全体过程持续半小时到一小时,待“把子”燃得剩不到半米高时,家里老老少少都围上来烤火,“烤烤手,年年有”“烤烤腚,不生病”,图得吉利、喜庆。
火把将燃尽时,火把倒向的方向也有讲究。那一天,会有精通玄学的老人们研究清楚各路“神仙”所在的方位,如果火把倒向财神的方位,则预示着来年家里将“财源广进”。
“这个传统是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的。”王有忠回顾。
现实:
电子鞭炮替代炮竹,“烤把子”人数骤减
今年,这一传统被政府一纸“禁燃令”冲破了。
年前,黄骅所属地河北省渤海新区发布公告,不许可燃放烟花炮竹,违者将做罚款、拘留处理。“三十和月朔,到处都有警车和警察盯着,抓得很紧。”刘老汉听说,村落里有个甲姓的村落民,燃放炮竹不听劝阻,被拘留了5日。
“放鞭炮、烤火确实污染空气太严重。”刘老汉描述道,烤把子时,一家一个“把子”冒烟,加上鞭炮,全体村落庄被一塌糊涂笼罩,迟迟难消散。风一吹,还会把污染物吹到相邻的北京、天津。
在当了一辈子教书匠的刘老汉心里,这种传统文化带有一定迷信和愚蠢色彩。他今年既没有放鞭炮,也没烤把子。别人烤的时候,他骑着自行车在村落里转了转,创造“烤把子的人家只有70%了。”
然而,对付烤把子的人数骤减,刘老汉心里仍以为“多少有点遗憾”。“过年了,没有鞭炮、不烤把子,没有什么年味了。”
王有忠今年没有准备任何炮竹。他买了一串电子鞭炮。与真鞭炮比较,电子鞭炮就像个玩具,遥控器一按劈啪作响,高等一点的电子鞭炮还可以选择模式是“小红炮”还是“震天雷”,但不冒烟,不会对空气造成污染。他的不少邻居也采纳了同样的办法。
转变:
年轻人眼中“烤把子”年俗不再主要
“烤把子”对张萍来说很主要。她今年25岁,从小随父母在天津市终年夜,而每年过年,也都会随父母回黄骅乡下老家,团圆在爷爷奶奶身边。“烤把子”成为她对过年、对亲情、对故乡最深刻的影象。“烤把子意味着家乡和亲情。”
但从小生活在村落中的年轻人和孩子们则不太相同。问起烤把子,王有忠的小孙子和小孙女都连连摇头:“我怕被火烧到。”
刘老汉也创造,“年轻人逐步不在乎烤把子了,甘心看手机。”对付年俗,不同代际的人们不雅观念也在淡化。刘老汉说,自己的小孙子对“烤把子”很陌生,“往后我们这代人不在了,可能都不会有人提起烤把子这回事。”
王红芬是刘老汉的亲戚,家住市区,从没见过烤把子的民俗景不雅观,但早有耳闻,心生好奇,去年他提出,想到乡下看一看这样的热闹景象。而今年他的欲望落空了。刘老汉感叹:“千盏灯火,万堆火把,这种壮不雅观景象他往后很丢脸到了。”
随着禁燃令愈来愈严格,王有忠也不知道,烤把子这个年俗还能延续多久。
(文中王有忠、刘老汉、王红芬等均为化名)
新京报 冯琪 编辑 潘灿 校正 李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