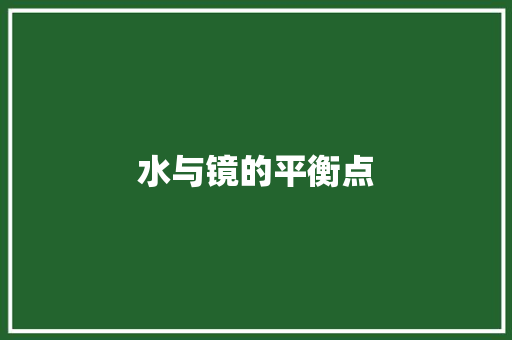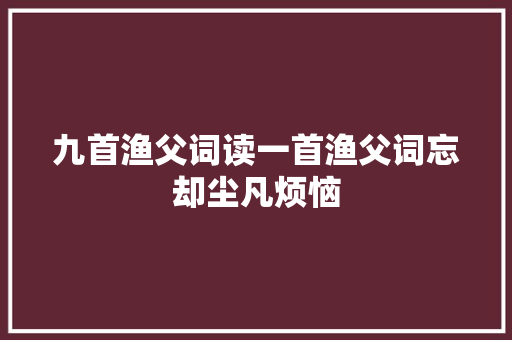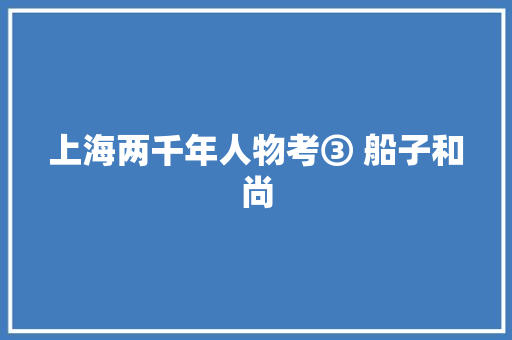经历了五载春秋,海南省全国第一次可移动文物普查于不久前落下了帷幕,共普查可移动文物数量108856件,收藏于全省6个行业系统的51家文物收藏单位,个中有字画2002件。
一叶扁舟,山水隐于一片白茫茫间,鸟绝,鱼沉,人无,远远看去,只有一点,清旷孤绝,既像柳宗元的《江雪》,又如张岱的《湖心亭看雪》。在一些古画爱好者看来,绘画的魅力不在于技艺,而在于从中读到生命走过的印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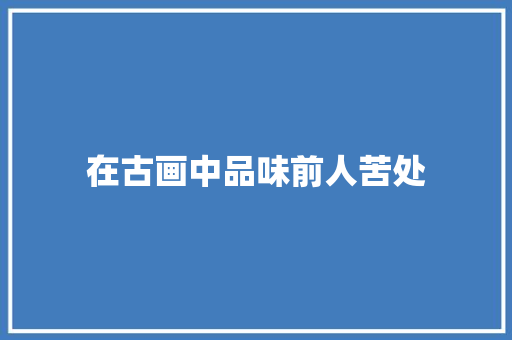
磨墨添喷鼻香,铺纸洗笔,这些略显庄严的仪式感表示了古人对字画艺术的虔诚恭敬之心。作为当代人,我们应若何欣赏古画之美呢?古人的这些笔墨中又隐匿了若何的苦处呢?
清代虚谷色绿竹扇面
古画之美 美在荒寒之境
古画是指古代的绘画作品,是中华文明的主要组成部分,是中国艺术的宝贝。从美术史的角度讲,1840年以前的国画,我们都统称为古画。
元代的《寒柯双鸟图》现藏于海南省民族博物馆,但见景象阴沉,地下蓑草倚靡,古木寒林的萧瑟环境中,两只惆怅的雉鸟畏缩在古木上。画家林先动认为,这幅画表示了中国绘画视觉审美的最高境界——荒寒之境。
古画中的荒寒画境,于冷寂中表示出身动的生命,用禅宗的话说,看似“去世搭搭地”,却是“活泼泼地”。比如在这幅画中,鸟的外轮廓很美,枯树以干笔为主,树干画完后,用干笔点苔,和上面的枯树形成比拟,就生动多了。“点苔、湿墨用得比较多,这样就增加了块面感,与鸟的块面感形成呼应。”文物鉴定职员韩惠娇说。
“在荒寒中追求活气,在活气中更见荒寒,活气是希望,荒寒是寂然,个中所包含的奇妙情怀,正是古画荒寒之境最值得重视的内涵之一。”在林先动看来,古画的荒寒寂历通过枯拙生冷的境界创造,着意于无买卖处,颠覆买卖的美学追求,到花着花落的背后去谛听落花的声音,在长河无波的宁静中感想熏染意绪的旷达。
“中国古代绘画中所蕴含的境界每每折射了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与儒释道的精神一脉相承。”海南学者戴文认为,儒家文化影响下的美学不雅观属于“看天下活”,而受道禅哲学影响的画家,并不着意于形式本身追求活意,而是放弃我执,放下对物质形式的执着,让万物清闲呈现。
比如深受道禅哲学影响的倪瓒、陈洪绶、八大隐士等画家的绘画不是“看天下活”,而是“让天下活”:不是画出一个活的天下,那是物质的,而是通过寂寥境界的创造,荡去遮蔽,让天下清闲活泼——虽然没有活泼的物质形式,却彰显了天下的本原的真实,以是它是活的。
十八罗汉图
古画之美 美在有生命的笔墨
关于绘画,《习苦斋画絮》记有一则有关东坡的趣闻:东坡在试院以朱笔画竹,见者诧异,“世岂有朱竹耶?”东坡反问,“世岂有墨竹耶?”
梅兰竹菊是花中四君子,也是古代文人喜好用诗字画描摹的工具,现藏于海南省民族博物馆的清代虚谷的《色绿竹扇面》具有光鲜的个性,画面中笔墨用笔简逸,流利秀雅,竹子则给人空灵、冷隽、瘦削的觉得,令人过目不忘,尤其是画面中流露出超凡脱俗、空灵稚拙、清虚冷逸的意境之美,仿佛置身于大自然中,让人的心灵为之澄澈起来,得到一种熏陶,使民气旷神怡。
东坡的反问,是中国古代绘画史上的惊天一问,所突显的便是古画中所描述的事物像不像的问题。戴文认为从海南省民族博物馆收藏的明代《圉人洗马图》也能略窥东坡的反问。此图中一古装圉童在引马入池,用笔疏松简放,干笔略皴马体,但马驱过于简化。
他说,同为画马,这幅画的马就与清代外籍宫廷画家郎世宁、中国当代画家徐悲鸿的画法很不一样,他们笔下的骏马维妙维肖,而这幅画以意笔画马,极善捉住动态和神色,这也从侧面解释,中国古代绘画并不看重像不像的问题,比起写实,更看重写意,用笔墨讲述自己一时的心境。
诚如曹操在《步出夏门行·龟虽寿》所言:“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义士晚年,壮心不已。”戴文从这匹马的眼神中读出落寞与诗意,他说,这是一种拟人的画法,画家画的不是马,而是自己,只是借由马来表达自己某种失落意,使人遐想到“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的感慨,在这里,画中的形式只是一种表达人情意天下的媒介。
在中国哲学“言无言”“不立笔墨”的整体哲学背景之下,如何建立一种超越于形式本身的措辞,成了中国古代绘画的关键。林先动认为,中国古代绘画发展的主要特点,便是将笔墨、丘壑(指古画中的具象性成分)、气候三者融为一体。也正由于此,中国古代大家之作才会有一种超越形式的思考,画中的笔墨不仅仅是技法的笔墨,更是作为绘画生命整体的笔墨。
墨分五色,以水调节墨色多层次的浓淡干湿,有浓、淡、干、湿、黑之分,也有加“白”,合称“六彩”的。中国人对黑白天下很入迷,就像围棋的黑白天下中,蕴藏着无尽的奥秘。戴文认为,古画中的笔墨不在于画得多少,就像倪瓒的画以简著称,每每几片石,几株树,一湾若隐若现的水,就构成一幅绝世佳作。
“以一木一石求云林,几失落云林。”明末清初的画家恽南田认为,笔下锦绣在于心有丘壑,只求形似反而南辕北辙。这与王家儒的意见不谋而合,他指出谈笔墨一定强调笔墨表示出的精神境界,谈意境一定从富有创造力的笔墨里才能达到,谈精神一定谈到人的精神品质、教化、境界,从任一个角度都可以欣赏古画,但一定要辩证的把它们关联起来,否则是无源之水。
古画之美 美在“扁舟一叶五湖游”
古画笔墨的背后,是画家所创造的一片心灵氛围,表现的是他关于天下的理解,他的人生体验,他的独特的宇宙意识和历史感。就像现藏于海南省民族博物馆的清代《渔乐图》,画中描述湖山相接,渔舟停泊的港湾景象,人物、景物描述生动、优雅,表现出画家对安居乐业的宁静生活的神往。
渔父,是中国古代哲学和艺术的永恒话题。楚辞和《庄子》都有《渔父》篇。楚辞《渔父》中的屈原洁身自好,“全球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渔父却认为,君子不应凝滞于物,应与世推移,任运而行。庄子杂篇中的《渔父》,则是庄子思想的化身,提倡顺化统统,通过孔子与渔父的对话,讽刺儒家欲以仁义来教养天下的入世不雅观。
戴文认为,在这两段的对话中,渔父俨然成了运化自然思想的代言人,其后,渔父险些成了“渔隐”的代表。“‘元四家’之一的吴镇创作过大量渔父图和渔父词,他继续了张志和、荆浩等首创的渔父艺术的传统,将它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许多人在先容吴镇的时候,都喜好称他平生好道禅与易学,绘画多哲思。听说他会算命,晓机微,说他晚年以此为生,生前还为自己预建墓地,并命名为梅花和尚墓,兵荒马乱时,诸墓被伐,唯此和尚墓幸免。
正好是这一智者要扁舟一叶五湖游,他要做浩荡乾坤一浮鸥,在辽阔的天涯自由翱翔。
王家儒认为,中国画精神气度里面最讲究的便是格调,而格调又常常与人的品质绑在一起,故中国画理论中特殊强调人品、品质,将“逸”品定为最高品质。
这是一种自有情怀,不同于隐匿山林,渔民的生活常常伴随着凶险,以是渔父的隐逸不是失落意的躲避,而是性灵自由的人生选择——我是自己生命的掌舵者,驾着自己的人生航船,走向自己乐意去的地方。(徐晗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