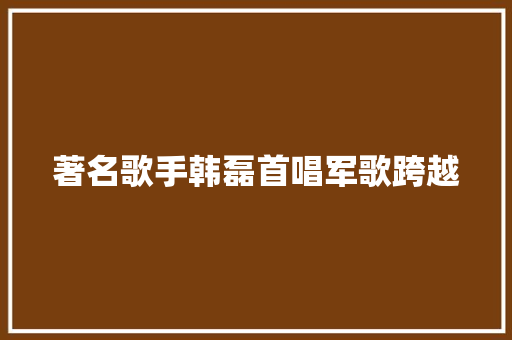张西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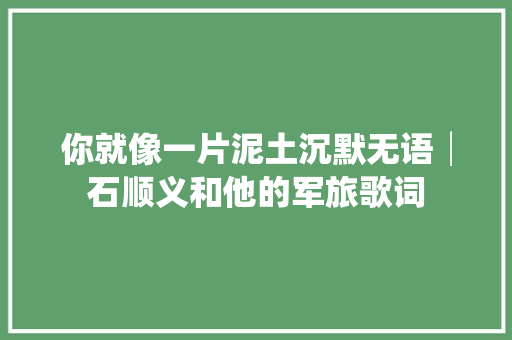
石顺义
当提及新中国军旅文艺的影象,自然就会想到那些滋养过我们发展的小说、电影、戏剧,进而会想到那些与青春相伴的诗歌、散文,还有那些竞相传唱一贯留在心里的歌,但对在音乐文学的原野上默默耕耘的词作家们则每每随意马虎被淡忘,石顺义便是这样一位创造过辉煌而又不事张扬的军旅歌词作家。
上世纪80年代末,在预备《公民军队爱公民》大型文艺晚会时,石顺义作词、王锡仁作曲的新歌《父老乡亲》受到各方面好评,石顺义的名字开始被中国歌坛所关注,我也是在那台晚会彩排的现场第一次见到石顺义。乔羽师长西席夸奖他,并预见他将成为新一代军旅音乐文学的代表人物。所谓“新一代”,是与当时部队文艺军队中的张永枚、阎肃、陈克正、邬大为、魏宝贵、刘薇、洪源、石祥等专业词作家比较,不仅是年事和资历的差异,更是创作不雅观念和题材开掘的不同,军旅音乐文学已呈现出新气候。
重新中囯成立到上世纪60年代中期,再从改革开放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两个不同的历史阶段形成军旅音乐文学创作的光鲜特点。如果从题材来看,前者大都是歌颂领袖、歌颂英模和歌颂军营新生活,明朗、欢快、荣光成为那个阶段军旅歌曲的主体色调;后者随着改革开放进入军队“忍耐期”,军旅歌曲的题材逐渐转为奉献的主题,从正面抒发军人的家国情怀,但比以往喜悦乐不雅观的感情明显多了一些深奥深厚但仍不失落高昂的基调,尤其是把军人埋藏在心底的情绪通过歌曲表达出来,寄托出“捐躯我一个、幸福十亿人”的诚挚欲望。前者歌词创作军队披着沙场的硝烟,以新中国成立前后参军的专业文艺事情者为主体,同时还有部队的业余作者加盟,如《志愿军战歌》《打靶归来》《铁道兵志在四方》《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等影响深远的歌词,都是由一线基层官兵创作,专业创作和业余创作互为补充,成为那个期间军旅音乐文学创作的又一光鲜特点。后者歌词创作得益于军队文艺军队历经“文革”年夜难后重获新生,一批沐浴着东风春雨的新生力量崭露锋芒,开始形成了一个以老带新、新老并举、渐趋稳定的专业歌词创作群体。便是在这样一个历史和时期大背景下,石顺义作为共和国的同龄人,既受到30后、40后军旅歌词传统的熏陶,又受到50后一代得改革开放风气之先的传染,使他处在承上启下、承前启后的位置上,必须以不同于他的前辈的视野来不雅观察生活、表现军营,探索军旅音乐文学创作新的路子。
这既有天赐良机让石顺义顺势而为,更有他与生俱来相承一脉的乡土文化基因,使他的歌词浸润着一种朴实而又浓郁的乡愁,成为军旅音乐文学中抒写“田舍军歌”的开拓者。石顺义自幼生活在屯子,对农人的情绪和对地皮的眷恋有着切身的感想熏染,对同是田舍子弟的战友丰富繁芜的内心天下有着透彻的认识和强烈的共鸣,同时从士兵到班长、排长,经历了一个完全的军人发展的低级阶段,基层官兵的喜怒哀乐印在他的心上,军营生活的春夏秋冬为他的年轮刻满印痕。这也是石顺义和他同代的歌词作家的差异所在,正是这种差异授予他的作品纯天然的“土味”和“兵味”,达到了一个深入浅出、返璞归真的境界。比他更年长的那一代歌词作家,不少也是“曾在家乡开荒地”“地皮连着我的心” ,而石顺义对故乡和亲人倾情歌唱,更在看似有一丝伤感或悲惨之中,渗透出对他嫡亲至爱的长辈朴拙而深厚的愧疚和戴德之情。这就使石顺义杜绝了标语口号,也避免了媚俗的表浅和公式化的套路,收视反听地对乡情亲情和儿女情,作真实细腻的刻画,从而塑造出了“白发亲娘”这个当代子弟兵母亲的范例形象,把公民军队“树高千尺也忘不了根”的朴拙初心表现得感天动地、荡气回肠。
正是这种渗透到石顺义骨髄和灵魂里的乡土文化,使他把自己所认识理解的军营文化比喻为胡琴的两根弦,“一根系着火热的军营,一根拴着我那远方的家”。“我的胡琴拉的是二泉水,军旅的生涯荡起浪花;我的胡琴拉的是良宵夜,月下的故乡你是否刚睡下……”(歌曲《我用胡琴和你说话》)这些带有明显田舍烙印的部队歌曲,很随意马虎就拨动军队中足够多数的田舍子弟的心弦,并且认同歌词表达的便是他们的心声,心弦与琴弦、心声与琴声,遥相呼应,同频共振,每当唱起这样的歌曲就能让他们的顾虑和思念得以释怀。比较而言,有些一贯成长在大都邑特殊是“大院”里的和出身文艺世家的歌词作者,虽然也希望营造出浓浓的“兵味”,但他们更看重当代化军队的节奏感,追求那种“风在呼啸军号响”的气势,习气把新式武器作为“士兵的形象”加以描述,把分外的演习、作战办法作为气氛渲染加以强化,使他们的“兵味”有了更伟大的气场,就如铜管乐队演奏出金戈铁马,气势是大了不少,韵味却淡了些。须要指出的是,这些歌词作家及其作品致力于具有当代化军队特色的歌曲创作,主不雅观上是希望贴近部队的生活使其更加多姿多彩,但由于创作的根在乡土文化的土壤中扎得不深,客不雅观上局限了反响生活的广度和深度,阻碍了官兵情绪的表达与通报,难以做到让他们尽情地歌唱,缺少足够打动人心的力量。石顺义的名贵之处在于,始终聚焦作为人的官兵的实质属性,透视出绿色军衣包裹着的小儿百姓之心,“告别家乡的温暖,走向远方的风雨……把恋你的情和爱,都捧给南北东西”(歌曲《绿色军衣》),军营的气息和乡野的韵味贯通领悟,使我们从战士丰富充足的情绪生活中更加感想熏染到军旅的崇高和雄壮。
石顺义的走心是情到深处的自然流淌,看不见大话,听不到空话,也没有那些虚情、煽情的套话。或是不加粉饰、素面朝天的真善美,或是言简意赅、三言五语的短平快,都是原汁原味呈现生活的原生态。像歌曲《说句心里话》《军人本色》便是用大口语来表现士兵的内心独白,《想家的时候》《迢遥的拜年》更是用大实话来抒发士兵柔肠百转的思念,《兵哥哥》则是用火辣辣的情话表现军嫂炽热的爱恋,《一二三四歌》竟是用犹如口令一样平常的军语表现士兵严明活泼的战斗生活,使他的歌词好听好懂,又能够入脑入心,深受官兵和大众的喜好,在军营乃至全社会广泛传唱。
石顺义
实在,石顺义原来便是一位很好的乡土墨客,他的那些带着乡野露珠和泥土芬芳的歌词,看起来信手拈来、绝不费力,实际上匠心独运、迎刃而解,若无出色的驾驭措辞的功力,就不可能用夷易的诗句勾勒出鲜活生动的人物形象来。正如20多年前乔羽师长西席所评价的那样,石顺义的上风就在于用自己的枝叶去承受明丽的阳光、新鲜的空气,这使他的笔墨产生了新意。
2007年年末,由于参加全军抒怀歌曲创作漫谈会,我才有第二次和石顺义当面互换的机会。那时的石顺义早已功成名就,但仍少言寡语,不愿出头露面,更不喜高谈阔论,直到他发言才彷佛提醒各位,石顺义也参会了。就这么一个低调的人,不说则已,说就要说实话,一点弯子也不绕,就军队抒怀歌曲的歌词创作存在的问题谈了自己的意见,犹如他写的歌词一样,朴实中有一种灵动,灵动中闪烁着一些光彩。
新中国成立70周年前夕,同为军旅歌词作家的王晓岭和他的夫人肖力来我家串门。晓岭说他下个月就70岁了,还有几位军队艺术家和他一样也是“共和国同龄人”,我的老伴江宛柳立时发起,那就到我们家来为你们过一个集体生日。就这样,过了国庆节后,晓岭、石顺义、王祖皆、仇非相约来到我家,老友相聚同贺生日。那天,石顺义是从珠海赶回来的,下了飞机就直奔我家。这是我们俩第三次相见,与上一次见面又过去了12年。我事先在家里的客厅挂起了一幅印有“与新中国一起发展”的红绸布,要他们每人在上面写一句话留作纪念。石顺义写了8个字:用我的心握你的手,这是大家都熟习的他写的一首歌的名字,一下子就引起了几位同行的共鸣,禁不住把歌词背了出来。“大家都是当兵的,同在从军路上走……风风雨雨皆是情,朝朝暮暮浓似酒……” (歌曲《用我的心握你的手》)寥寥数语,既表达出他们的人生和艺术与军营同行的星光岁月,也揭示了石顺义的歌词创作一往情深的光鲜风格,这不禁使我想起第一次见到石顺义时留下的印象,这么多年过去了,他还是当年那个淳厚厚道的样子,“憨憨的一笑多少情意,你就像一片泥土沉默无语”。(歌曲《我的士兵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