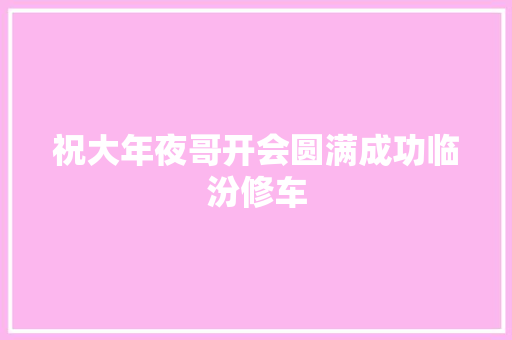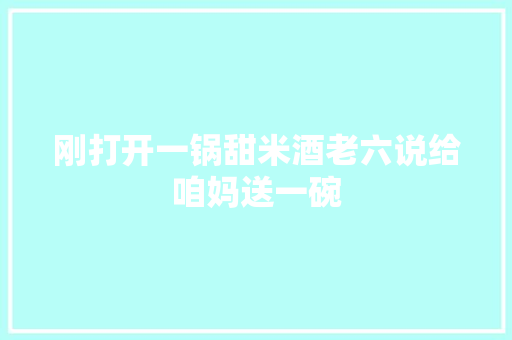端吃错了药。她患的是药物引起的脑紊乱,双目失落明,四肢瘫痪,而且严重失落语,只有听觉和知觉还未损失;经由一天一夜的抢救,她才有所好转,接着住院一周,方才康复。这一周内,桐像个大人似的,无微不至地关怀着她。他把自己的小人书搬到病房里,一本本念给端听;那些战斗故事、英雄人物,在他的童稚的朗诵下,变成一幅幅伟大的画面,展现于她的面前;随着病体减轻,端对桐的喜好远远超过了梧。
他们两家同住一个村落庄,以是桐还兼任了为端送饭的任务。

“大嫂,你猜我给你带来了什么?”即将出院的这天上午,桐从家里兴冲冲赶来,双手别在背后,神秘地笑对着端。
空气中弥漫着一缕沁人心脾的栀子花喷鼻香,这让端瞬间觉得神清气爽,禁不住笑看桐一眼,故意摇摇头:“我不会猜。”
桐头向左一偏,又一笑道:“是树上长的。”
“树上现在能长什么呢?果子都还没熟,可能是叶子吧?除此还有什么?”端说罢,抿嘴一笑。
“不对,你看——”桐说完,一扬手,将一束乳白色的栀子花送到她的面前。
“呀,栀子花都开啦?”端惊喜不已,她的视力已能清晰地瞥见那些绽放的花瓣,嗅觉也规复正常,能够闻到栀子花浓郁的喷鼻香气,于是接过那一束芬芳扑鼻的鲜花,情不自禁地惊叹道,“真喷鼻香呀!
”
桐又兴致勃勃地说:“大嫂,你知道不知道我哥来信了?他说,等栀子花开的日子,他就会探家来了。哈,哥很快就要来了呀!
”
端一听梧要来了,心下一沉,脸上也失落去笑颜。她对梧存着一肚子怨气,这是不能对小孩子说的,只好冲桐摇摇头,表示不知道。
桐坐到病床前,天真地问端:“你不喜好我哥吗?”
“谁说我不喜好你哥呢?”端强颜欢笑说道。
“刚才见你不高兴,我还以为你不喜好他呢。我听人家说,你看不上我哥,是真的吗?”
“不要听人瞎说。”端脸一红,低下头,见告桐,“你哥是军人,没人看不上他。”
“那就好了,哥这次回来,你一定要和他去逛县城、看电影、照合影像,好吗?”
“你是小孩子,怎么关心起大人的事来?人小心大。”端伸手刮他鼻梁,羞他,接着宽慰他,“好吧,我答应你。”
“大嫂,你真好!
”桐由衷地对她赞许道。端又捏了捏桐的小鼻子,“机灵鬼,尽会谄媚人。”
桐愉快地笑了,露出两颗洁白的小虎牙,很可爱。
“桐,本日出院,可没钱结账啊!”端犯难道。
“妈让我带来了,给你。”
端接过钱,心里不是滋味。她是生生让父母卖给梧了,有什么办法呢?生于穷苦,长于穷苦的她,二十多年来,只有和梧订婚后才穿上几件像样衣服。
“大嫂,别动,让我给你梳梳头,看你,头发都结在一起了。”
她心里一热,复又坐下,任桐那双小手在她的头发中梳理着,不一会儿,桐为她把头梳好,又从她手中那束栀子花中挑出两朵,别在她的辫梢,然后,拍手高兴地说:“看,多俊秀。”
“桐,我不喜好戴花。”
“我要你戴着,可好看了。”
“你这小孩,真油滑。”
桐的确还是个孩子,听了真个话。就揽住她的脖子撒娇,并在她的面颊上轻轻亲了一口,然后,“咯咯”笑着跑开了。
她抚摸面颊,摇头笑笑,想到梧还没有吻过她一下呢,倒让这小鬼抢了先。但她知道,桐是纯洁无暇的,十二岁的孩子,懂得什么?她比他大了整整十岁。
出院不久,梧探家来了。端病体刚好,没有跟他去逛县城看电影照合影像。桐却像个小尾巴,跟在梧后边,每天过来看端,那一双纯洁的眼珠中显出许多困惑来,这彷佛与他小小的年事不相称,可他一定在为他们担心着什么了,特殊是端和梧开着半真半假的玩笑时,桐总要红着脸,站在一边注目着他们的表情,彷佛很不理解他们的样子。
一天晚上,村落里放电影,桐半下午就跑来见告端:“大嫂,本日晚上有电影哩,我去占位子,你跟我哥去看好吗?”
端连和梧走在一起都不想,哪里想去看电影?但见这位小弟弟那么热心,她不能弗了他的美意,于是点点头,含笑答应了他。
桐愉快得跳起来,一溜烟跑向电影场占位置去了。端望着那天真活泼的桐的背影,心里对梧也有了缓和的余地。梧是个内向的人,不爱谈笑,一点也不像桐这么爽朗。
天已向晚,梧一个人悄悄来了,端正在自己的小房间里坐着胡思乱想,他的到来并未引起她内心的喜悦,反而使她产生了一丝淡淡的惆怅。端站起来,出于礼貌,让座给他,自己坐在床边。梧坐下后,目光忧郁地看着面前低头不语的端,一声不响。
室内的光芒逐渐暗下来,端轻咳一声,见告梧:
“桐去占位子了,他希望我们本日晚上去看电影。”
“你的身体受得了吗?”梧开口问道。
“我已经好了,多亏你家的帮助,还有桐的照顾。”
“那还不是该当的!
”
他俩客气地交谈着,没有更多的话题,又沉默。
天完备黑了下来,梧起身告辞,端轻声挽留:
“在我家用饭吧?”
梧又坐下来,表示留下。
端叹口气,以为梧太实诚了。
妈妈在锅屋做饭,梧陪端在不开灯的房间里缄默对坐,真个妹妹凤风风火火地跑进来,大声见告端今晚有电影,问她看不看,待创造姐夫也在,就“哎呦”一声,笑着跑了出去。真个心情逐渐爽朗,她笑对梧说:“凤像个疯丫头,就爱看电影,疯玩。”
梧在阴郁中动一下,顺着真个话说:“小女孩,高枕而卧的,正是爱玩的时候。”
“桐也这样。”端想夸夸桐,又不知从哪方面提及。
“桐的苦处挺重的。”梧叹口气见告端。
“他一个小孩子有什么苦处?”
“别看他小,他在为我们操心呢。”
“是吗?对了,我住院时,他也对我说过不少关于我们的话呢,他问我是不是看不上你。”
“是呀,这也是我想问你的。”
“亲事已经定下了,还问什么呀?我家接了你家的好多彩礼呢!
我也记不清有多少了,但愿你不要以为我看中的是钱就好。”
“当然不会。”梧负责地回答。
“可你,为什么不给我写信?”端幽怨地问。
“我的水平没你高,写不好,怕你见笑。”
端听他这么说,优胜感顿生,她大方地说:“什么水平不水平的,人,还不是平等的!
”
“你真的这么认为吗?”
“当然是真的,我是高价姑娘,但我的眼眶并不高,你一定误会我了,把我当成那种只认钱不认人的女子了。”
梧听了真个话,欣慰地叹口气。他没有再对端阐明什么,听见电影已经开始放了,喇叭里传来了黄梅戏的曲调,就低声说:“开演了,桐一定等急了,现在就去吧?”
“你不饿?”
“不饿,你呢?”
“我也不饿。”
“那么走吧,多穿件衣服。”
“不冷。”
他俩说罢,见告妈妈一声,没吃晚饭就出了家门,往电影场走去。
来到电影场,黄梅戏《牛郎织女》正演到动人处,看电影的人们个个聚精会神,都被牛郎织女那天上人间的朴拙爱情冲动并吸引着。他俩从人隐士海中找到了桐,他在前边正中间。当梧在边上涌现时,桐已瞥见他了,这时恰好换片,桐大声喊:
“大哥,大嫂,我在这里,快来呀!
”
可是人太挤了。梧作手势见告桐进不去,桐急了,要出来。端悄声对梧说:
“想法挤进去吧。”
梧只好在前边开道,端紧跟其后,费了好大劲才从拥挤的人缝中挤到桐所在的地方。
这时,电影又接着刚才的剧情放映。桐坐在梧和端中间喜不自胜,他已无心看电影了,而目光专注地看端。溘然,小家伙拽了真个衣角一下,悄声说:
“大嫂,我和你换过来坐吧,让你坐中间。”
端转向他含笑问:“刚坐好又要换,你坐中间不好吗?”
“不好。我看不见,被前边那个人挡住了。”
“好吧,你站起来,我坐过去。”
换好座位,端才领会桐的意思,她紧挨着梧坐下,桐也紧靠她坐着。电影中的牛郎织女结为夫妻了,梧的手碰了真个手一下,接着将她的手握住。端触电一样平常,想抽回来,可他牢牢捉住不放。这个小动作没有让任何人创造,端还是紧张的旁边看看,见别人都在心神专注看电影,连身边的桐也没把稳她和梧的事,这才略略放心,舒口气,觉得被他捉住的愉快,浑身有点酥麻,也有点燥热。
银幕上的牛郎织女的故事到了高潮,梧的热血也在沸腾,他捉住真个左手,将五指伸开交错握紧,暗暗用力,把心中的渴望向端通报。端心驰憧憬,想到夫妻之间该当有一种朴拙的感情,虚情假意是成不了夫妻的。她和梧的婚姻已定,将来一定要结合,如果现在不以诚相待,等做了夫妻也是同床异梦。于是,她相应着梧的亲密表示,与他的手握的更紧。暗下决心,要和梧加深理解,并希望与贰息息相通,将来做一对恩爱夫妻。
看完《牛郎织女》,他俩提前离开电影场。桐还想看下一部战斗片,就留下了。端临走时,被桐拽住衣袖,她转头笑看一眼桐,桐小声对她说:
“大嫂,你跟大哥去我家玩吧,没人去打扰你们。”
端伸出食指刮了桐的鼻梁一下,浅笑笑,轻声说:“小孩子别管大人的事,看你的电影吧。”
离开闹哄哄的电影场,梧问她:“去我家吗?”
“不去,我想去村落外走走。”
“好吧。”他陪着她,肩膀时时碰到她的肩膀,却没敢再捉住她的手。
端举头看看繁星点点的夜空,一阵夜风吹过来,她觉得清爽多了。订婚三年,她也曾渴望过这一幕。能和他在夜晚出去闲步,多少填补了她昔日的遗憾。过去,每当看到别的女子天一黑就穿着整洁地去与男子约会时,也曾倾慕过人家,暗暗愿望着自己也会有这么一天。这一天终于来了,她有点恍恍惚惚的,以为不大真实,自己的一颗心还无缺地保留着,身边的这个人有权得到她吗?他那么蕴藉、沉默、不动感情,就想得到她的温顺,那是不可能的。
两人默默地走在村落外的小路上,路边的草丛中有萤火虫在飞舞闪耀,远处的水田里传来一阵阵蛙鸣。端呼吸着夏夜的新鲜空气,觉得越来越清爽了,回忆与病魔斗争的那些日子,那种紊乱、沉疴,一去不复返了,这都多亏了桐的照看那!
为了这可爱、机警、善解人意的小弟弟,她也不能与梧疏远。
来到一座小桥上,桥下流水淙淙。端停下来,侧目看梧,只见他的白衬衣的领口洞开,在夜风中抖动着,把他全体人衬托得洒脱俊逸;那一头乌发剃得短短的,在这黑夜中显得更黑;而那双深邃的眼睛却穿透阴郁,默默地把她注目。端靠近栏杆,和他面对面凝望着,她心里开始颠簸,泛起层层荡漾,有好多话想对他说又不知从何提及。
贰心里在想什么?
“端,我还有两天韶光陪你,两天后我就要回部队了。”他低声见告她。
“是吗?可我们还没有……”她不想说下去了。
梧彷佛领会了她的意思,向她靠了靠,又一次捉住她的手,将她拉近,低声说:“我知道,你心里很苦,还有一年,我就转业了,到时,我每天陪你闲步。”
“要常常给我写信。”
“好的。你也写给我,好吗?”
端点点头,手儿任他紧握着,仰视着他的脸孔,他正低头注目她,喃喃地问:
“我是个穷当兵的,你真的不嫌弃?”
端想说“不”,可嚅动嘴唇,怎么也说不出口。她由抵触到认命到现在的认可,乃至对他产生少有的感情,这可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三年的韶光,把一个心高气盛的她彻底改变了。当初高中毕业回来时,带着一名高中生的一身骄傲,何曾想到要与梧这样的青年订婚呢?在学校里,爱慕她的人那么多,可她一个也没有联系。现在,她生活的圈子越来越小了,要命的是,自打和梧订婚,真好比名花有主了,没一个异性青年敢走近她这位军人的未婚妻。梧知道她这些黑幕吗?体会到她所受的孤单吗?
“你彷佛苦处忡忡的。”
“你不也一样吗?”
梧不再说话,猝然间伸开双臂牢牢地拥住她,在她的脸上、头发上狂吻,又牢牢地吻住她的嘴唇,令她透不过气来。他这突如其来的打击,吓得她错愕失落措,无处可躲,下意识地想解脱他的拥抱,却让他抱的更紧了。
他们内心的间隔在一点点拉近。端心头上的沉重感在逐渐肃清,取而代之的是感官上的陶醉,那种从未有过的甜蜜逐步渗透内心,在心底下形成海一样平常的波涛,这波涛彭湃澎湃,将她全体儿淹没了。
“梧,你多粗鲁啊!
”端得以喘口气时,轻轻捶打梧的肩膀,心情愉快地靠在他的胸前,谛听着他有力的心跳,很知足地叹了口气。无需更多的措辞,她已理解到他是一个诚挚而又激情亲切似火的青年,别看他一向含而不露,可他的感情多么丰富啊!
“端,我思念着你时,你也思念着我吗?”他注目她,动情地问。
她不语,由于她过去没有对他思念过,只有怨恨和无可奈何的等待。
“你可知道,我是多么的害怕失落去你。”
“现在,你认为自己是不是已经得到我啦?”她故意冷冷地问道。
“我不知道,我......”他结结巴巴,说不下去。
端溘然想笑,她想,当兵的人真故意思,感情会像火山爆发一样来得溘然、剧烈,可他还说不知道之类的话,他不理解她怎么敢亲近她的?这个盲目的家伙,真像他表现出来的那么淳厚诚笃吗?这时,她还想考试测验被他热烈亲吻的滋味,他却又君子君子一样平常只拥着她说话。
“端,我走了,你会想我吗?”
“不知道!
”她微微一笑,推开了他。
——写于 1984年10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