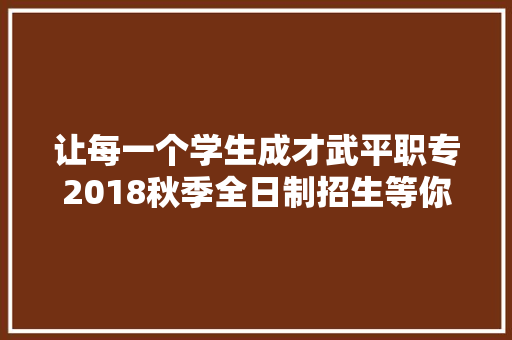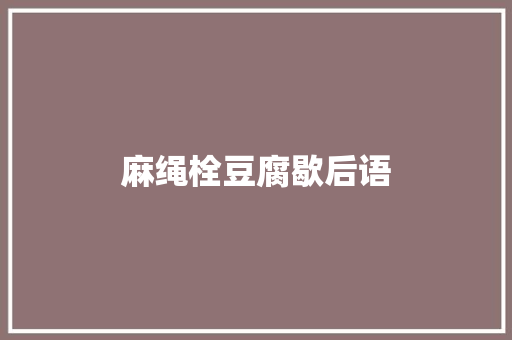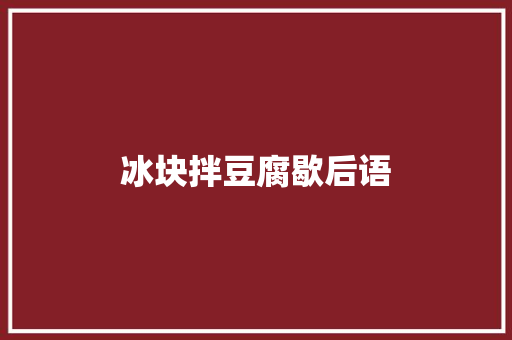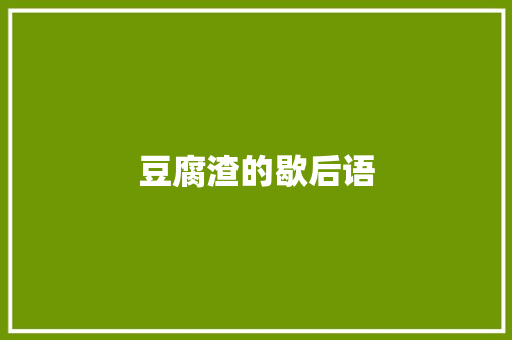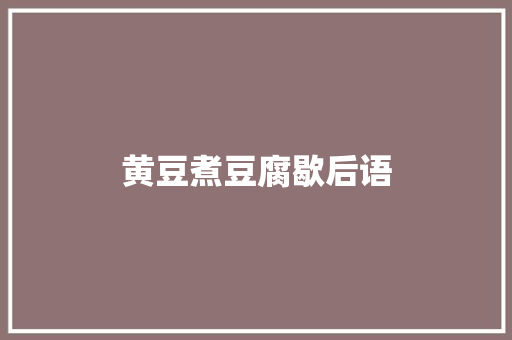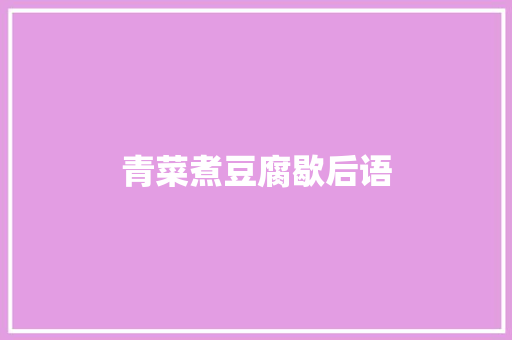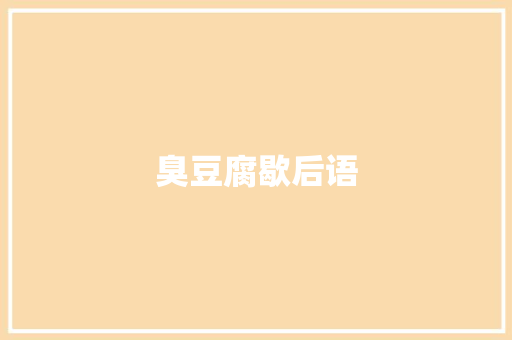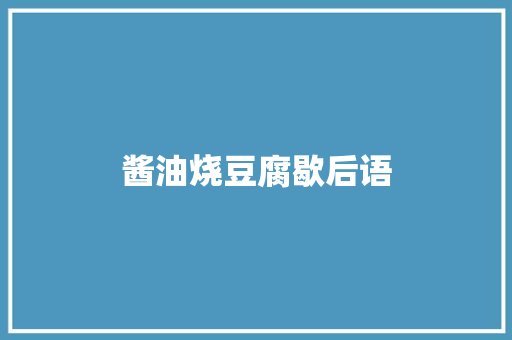文/李向群
在“读万卷书”和“行万里路”的“千”之空档里,我杜撰了一句“吃千家饭”。不因“食为先”、“食为天”做注脚,就为大快朵颐,更为味蕾绽放,于是,在唇齿留喷鼻香的美妙回味中,甘之如饴的美感怡然荡漾于心,不留神又丰裕至笔尖。 到一个未曾去过的地方,尝一些未曾听过和吃过的可称为菜肴、美食、佳肴、美馔,那可是人生一大美事。驱车往武平,那是厦门以西300多公里的一个山区县份,此前,我还没去过。很想去的动机,多年来屡屡萌生,其间最大的一个成分便是知青情结使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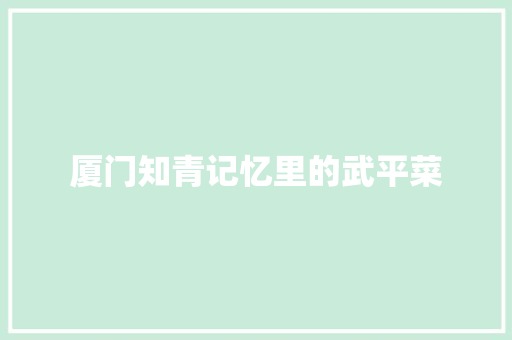
武平县是1969年户籍在厦门思明区老三届知青的着落点、下乡插队的所在。我家住在中山路旁南田巷,周遭邻里的老三届哥姐们基本上同一指向,都到武平,只是所在公社不同、所在村落不同。到了旧历过年前,陆续回厦门过年的老三届知青哥姐们都会给我们带来一些武平的事。他们阐述着在荒山中跋涉出工,在凛冽的山风中吞咽凉透的米饭就着很咸的咸菜、萝卜干。他们会唱歌,唱知青的歌,印象最深的一首老三届知青的歌谣,那是用《我爱我的台湾岛》曲调改编的“歪歌”,个中有一句歌词是“兄弟啊,朋友啊,你‘咸巴浪’(闽南语,一种鱼的名称)寄些来”。现在再回放当年的影象,厦弟子齿头禅的“好料”,彷佛在当时很少涌如今他们的言谈中,这就给我的脑海里蒙上一层阴翳,形成一个彷佛难以逆转的思维定势,山区武平,没有“好料”。
当年的“食为天”之食,该当因此果腹为第一要素,物资匮乏的年代,近乎原始的饮食构造,便是当年人们的生活皈依、生活的必需、生活的写实。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充饥式的“吃三顿”,在当年实在难以唤起所谓对生活的美好神往,对“好料”的些许追求。那时可能做到的事,便是在逢年过节确当口,极吝啬、又不很宁愿地将较好的食材送出,作为敬拜先人后亲朋好友会聚的一顿饱餐。待隔日天明,又开始那周而复始的充饥式“吃三顿”。荏苒光阴穿梭而过,到了现在,那个时期的情状已经由去多时,当年勤恳、勤俭的人儿终于得到温饱的庇佑,终于摆脱食俗的桎梏,终于得到“食为先”“食为天”的权利,终于可以放开肚皮、甩开腮帮子了,这都是由于时期的变迁、社会的进步、不雅观念的更新、条件的改进和需求的增加,当然还有日益自我强化的食欲的增长和对所食之物的选择、挑拣以及“择其善而从之”的多多情由。
车行一起,我的脑海里捣鼓闹腾的便是这些,给“这些”作结的便是下车,走进餐厅,走近餐桌,瞄上桌上的锅碗瓢盆之中之食。顷刻间,鼻翼已被一桌佳肴的综合喷鼻香气充满,钵满盆满的蒸、炸、炖、炒的菜品目不暇接。如何下筷?一韶光却有所困顿。一起上的思绪飘飞终于有了一个着其实实的落点,这便是,开吃!
土鸡土鸭土菜,次第摆上桌来,一色的乡土味,淳厚得再也不过,本色得难以形容,脑海里倏然蹦出的一个词“原生态”,继而,自己立马嫌这个词故弄玄虚,还是用最朴素的词汇来表达、来形容这面前丰硕的菜肴,那便是纯“原味”。
可不,“原味”便是土,土得有趣的便是这道道上桌之菜,原味菜色。
白色大瓷碗盛满洁白的猪蹄,一块足有二三两,这可是武平的特有做法,与闽南的酱色烘猪脚大相径庭。除了烹制熟透的猪蹄颜色不同之外,关键是口感也大有差异,武平的白猪蹄不像闽南的烘猪脚讲求烂熟熟透,烂熟至猪皮的胶质都要化开似的。武平的白猪蹄皮质的嚼劲适中,略带弹牙之感,带筋道的腿肉的肉涓滴不塞牙缝,猪蹄中的蹄筋则是此道菜肴的主打,一根根象牙色的筋条已经被炖煮熟透,用牙一咬,胶质的黏乎、蹄筋质感的绵密便可全然感想熏染。这道菜的精华部分是味觉受到统合,猪肉的源喷鼻香被山中的草药味细周详密的包裹着,咀嚼少焉,味蕾都被这原乡土韵征服,再咀嚼,合着齿颊留喷鼻香的惊叹,这美食,就美美地收入腹中,再度漾起的饱嗝里,少不了的便是这极美的土土的原味。
这土鸡土鸭的做法也兼具武平的自有风格,这样的自有风格从何而来,我感到姜葱蒜韭芹等微荤素食素菜的加入,起着点化的奥妙浸染。这是一盘白切土鸭,半爿的鸭肉按照每条半寸宽切好、摆盘,撒上老酒,最主要的便是在这半爿鸭肉上覆盖满姜葱蒜的细丝。鸭肉的鲜美、老酒的醇喷鼻香,再加上充满田园清新气息的、有调味去腥功用的菜蔬,实在令人食指大动。其趣还在于将家常的食材加上最一样平常的配菜,摆出最一样平常的菜式,烹煮出最实在的口味。其结果是半爿土鸭一上桌,一人一筷、一人一块,送进嘴里,让味蕾去全打仗,让味蕾的各个分区去探求各自的味源了。
用大大的土瓷碗送到我们面前的是红焖野猪肉,土中带野的态势便是那一块块桀骜不羁、都还两头翘的野猪皮。听说,吃野猪肉的精妙之处,便是吃野猪皮,那熟透的厚厚的快一厘米厚的野猪皮不很烂,却有脆脆的口感,咀嚼中可以享受着纯野味的质感和纯山野美食之风,好有怡然自得之感。
这武平菜还真土得有味。我思忖着,这原村落夫所聚拢的土味,都是源自于对传统食材、天然食材的疼惜和敬畏。此话彷佛有点凝重感,再想一下,却也如此。对这样的融汇所得,为何不尊重它,并将其代价发挥到极致,品鉴出个中所有的味道、纤维、营养元素。这样,才能使人与自然的和谐度提升到最高点;这样,我们就能心安理得,尽享大自然的赐予,尽享劳动和丰收的欢愉;这样的味道虽土,但绝对合口味。
我创造芫荽是武平菜肴的紧张配角,或可以称作最佳配角。一海碗黑木耳上桌,是不很起眼,在有点不以为然打量之后,我把视点对准在覆盖于满碗黑木耳之上的那一大撮鲜绿的芫荽。这碗黑木耳带有汤水,高汤加黑木耳,本来就有点土味,纯纯的汤头、脆脆的黑木耳,本已有滋有味,那芫荽“插一脚”,缘何而来?那就试试,舀一勺加汤的黑木耳入碗,再把芫荽一两支同时放进碗中,将芫荽按入汤底,不一会,热热的汤头焐热、焐熟了芫荽,此时,一种前所未有的味道涌现,芫荽的特有喷鼻香味足以令邻座侧目,一种原来不易领悟的食材相处,彷佛是不和谐的和弦,却能调适出一种别样的和谐、一样的和美。芫荽算不上是主要的蔬菜,属于配菜,黑木耳充其量也只能叫做佐餐的小菜,都不起眼,而在武平,却成了一道好菜佳肴、养生之选,究其因,就在于虽土犹荣,土中见奇,虽土却味真,是完完备全的本色菜肴。
那一盘菜彷佛叫做三瓜合一,这道菜将武平菜的理念表现得十分到位。纯自然的食材、最大略的烹制、极朴实的摆盘,提领出很实在的乡土气息。何谓“三瓜合一”,只见一大土碗上桌,汤汤水水、热热乎乎、清清淡淡的觉得随之而来。这大碗里有三种瓜:丝瓜、南瓜、冬瓜。每一种瓜都切成角状,都以方便入口之大小为宜,经清炒熬煮一番,加入高汤,再勾芡,便可上桌。如此一道菜的菜式实在是平朴无奇,味道属原汁原味型,没有过多的调味,只有三种瓜的自有味道在悄悄“三重奏”,馨喷鼻香适口,一入口,那一派乡野的纯自然风便荡漾心腹之间,淳厚、真实的觉得更使味蕾做一次真实的回归。
留恋餐桌上的纯自然美食,让味蕾寻求最佳的绽放机遇,是我武平之行的最深感知。就在惜别武平的末了午餐,有一道菜却让我的武平菜谱增长了兼之有分外影象的一笔。那是一道名叫“红菌豆腐渣”的武平菜肴。
这是一道极具武平地方人文风格的菜肴,我是这样为它定义的。勤俭朴实的武平乡民能够发明、制作、命名、流传这道菜,便是优秀传统的传习、朴实民风的延展。这与当年厦门穷汉家节俭食用、现在登大雅之堂的面线糊,这与同安人家中克勤克俭制作的地瓜粉果、现在成为银城名菜“芋圆”一样,都包含着勤俭的元素和聪慧的基因。
“红菌豆腐渣”是道菜,菜名刀切斧砍,对食材和身分绝不掩饰笼罩。确也如此,其食材便是磨豆浆完过滤后余下的豆渣,这些残渣一样平常是做喂猪饲料。精明的武平乡民从前就对此刻意为之,据称,从前武平乡民的做菜调味靠的便是用豆渣造就的红菌,红菌就长在发酵的豆渣上层,红得有点可爱,嫣嫣的红。据手头拿到的武平县资料先容,“红菌豆腐渣的制作方法很大略:将新鲜豆腐渣倒入铁锅中以文火烤焙,待豆腐渣干至手捏成团,指缝有湿痕却不溢水,而抛之即散时,即铲起,置于已铺好芭蕉叶的米筛或糠筛的背面,用手压紧压平压匀,厚约寸许;待冷却后,即在豆腐渣表面撒上菌种,菌种的根须很快伸入豆腐渣中,使渣变得既结实又柔韧,同时渣面长出一层红毛,此即为红菌。”这的确是一道特色别具的菜肴。一盘上桌,满座都为之停筷,不住地探寻其出身与身家。武平文联的郑副主席奉告,无论煮肉、煮豆腐或是煮点菜蔬,放一点红菌豆腐渣,口味一下子就提上来,鲜美非常,其提鲜的浸染令人侧目,就由于这一提鲜因子是土法的、自然的、天然的。还有这样一说,许多旅居南洋的武平人氏对此十分眷恋,返乡前,都会叮嘱支属到乡下、购得红菌豆腐渣,为防变质,还要将红菌豆腐渣烤熟晒干,封装带走,还成为武平乡亲在外洋赠送亲朋的伴手礼。
就这样,我对武平菜的感想熏染有了新知,食材的鲜、配搭的巧、火候的准、摆盘的美是一方面,而人文元素的融入、乡土气息的包裹,悄然造就,也悄然流播这一纯纯的、真切的饮食之美、山乡之美。最美的该当是我和同行者的味蕾,千滋百味已经使其极度绽放,几近极致。
收笔之时,溘然想起闽西八大干之武平猪胆干,没有猪胆干现身的武平菜,武平美食之旅缺了它,就彷佛有点缺憾。再一想,实在也不然,或不以为然,我们所遍尝的每道武平菜,虽没有武平猪胆干的名气,但是实实在在的每一道菜肴引发了我们的灵感、绽放了我们的味蕾,还不是给了我们悠悠的回忆吗?
(作者系厦门知青文学沙龙成员)图片来源于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