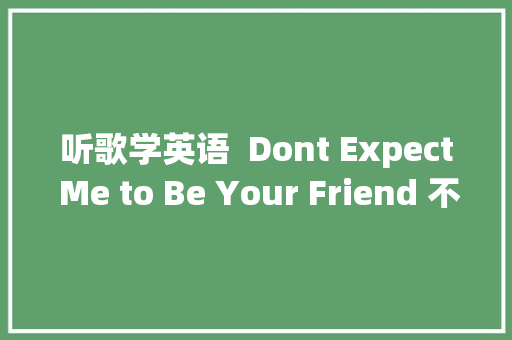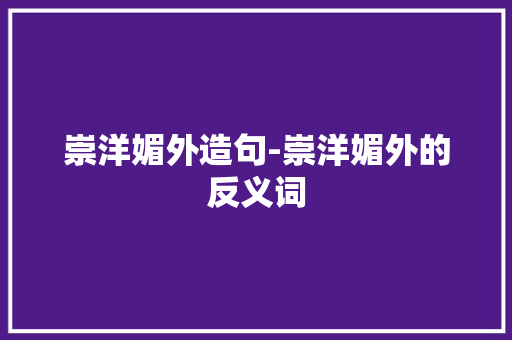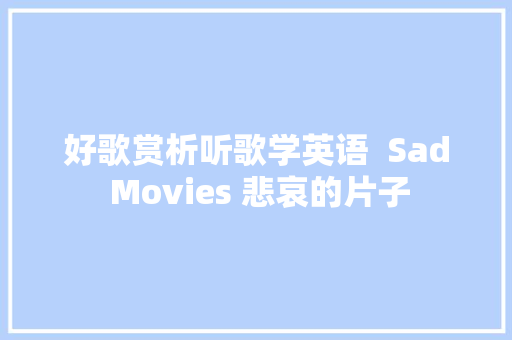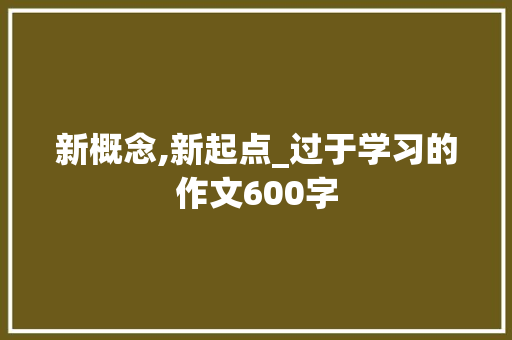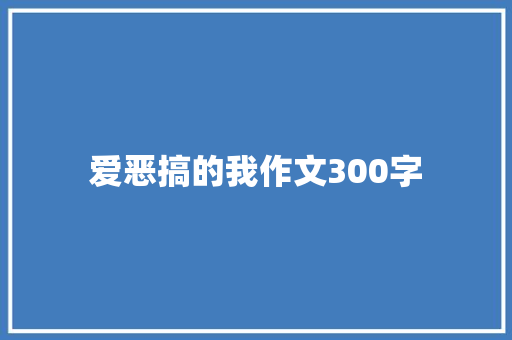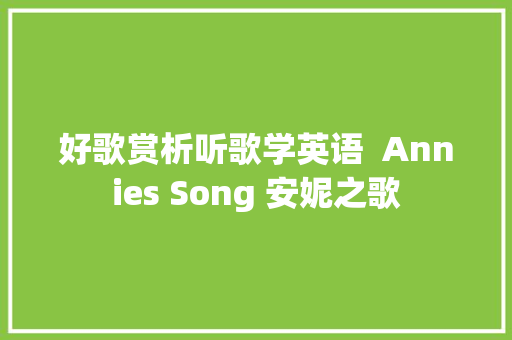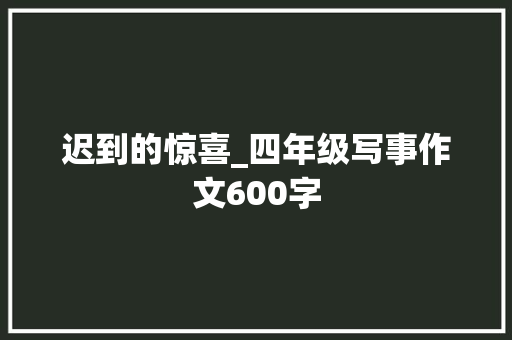很明显,基洛维奇改用英语写作是明智的职业决定。由之带来的丰硕报酬为营销添上了俊秀的一笔——惯常的炒作套路是说书稿被拒了多少次。不过他的故事也不新鲜,事实上,作家靠外语写作致富的传统相称悠久。有些作家写外语为了得到更多的读者;有些出于政治或个人缘故原由;还有些纯粹出于措辞风格的考虑。
可能最出名的用英语写作的作家是波兰人约瑟夫·康拉德,他是商船船长,快三十岁时加入英国国籍,说英语带着浓浓的波兰腔。英语乃至不是他的第二外语(他的法语更好些),但他说自己很享受学来的外语的“可塑性”。康拉德的笔墨有时候很拧巴,迂回曲折、支离破碎、句法别扭,但在这表面的混乱之下,是一种小心翼翼的词典般的精准,同时他那意识流风格是早期当代派文学的最佳典范。用英语写作给了康拉德解脱习俗的自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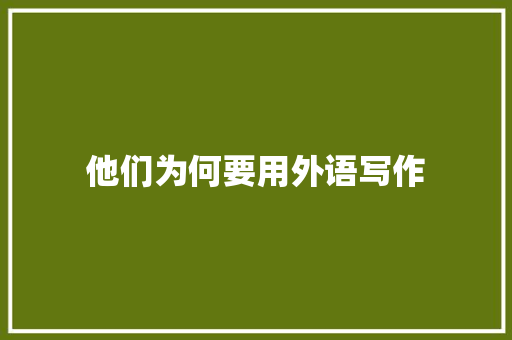
另一位出名人物该当是纳博科夫。在布尔什维克革命前夕,他被迫逃离俄国,来到剑桥学习,移民美国前还在德国住过。到美国后他将自己的英文打磨得标致俊秀。纳博科夫热衷于研究蝴蝶,他总是能找到最准确的词汇描述情境。他的写作丰裕着词汇的快感,这种快感是作者没有把母语视作天经地义而产生的。纳博科夫最出名的小说《洛丽塔》明明是一个精通多语的人写给英语的情书,却猥琐地假装成恋童癖对忧郁小女孩的畸恋。
与纳博科夫和康拉德采纳不同技法但达到同样精准效果的是塞缪尔·贝克特,这个爱尔兰人选择用法语写作,总爱说自己“没有风格”。在贝克特看来,做出放弃母语写作的决定是干预式的:不论从生理、措辞学、情绪上说,英语都太冗杂了;用一种外语写作让他能够去粗存精。贝克特总会让你以为他的终极目标是沉默,抛弃母语只是迈出了第一步。
贝克特是自主选择了措辞上的自我流放,许多其他作家是被迫的。雅歌塔·克里斯多夫(Agota Kristof)1956年逃离匈牙利,移居瑞士,然后开始用法语写作,不是出于审美缘故原由,而是国外很少有人能读匈牙利语,且她在祖国出版作品已经不可能。她的法语形成了一种谨严的极简主义风格,造诣了一系列关于战役和匮乏的朴实小说。
克里斯多夫的同胞阿瑟·库斯勒(Arthur Koestler)离开布达佩斯去了巴勒斯坦,然后住在德国,末了来到伦敦。库斯勒用外语写作彷佛变帽子戏法,先是匈牙利语然后是德语再是英语(他还说过自己做梦时讲法语)。还有一个用英语写作的匈牙利人是乔治·米凯什(Georges Mikes),二战中他搬去英国,以用英语嘲笑别人而著称。
人们很随意马虎忘却,最范例的美国作家杰克·凯鲁亚克并不天生讲英语。他成长于说法语的加拿大家庭,直到青少年时才节制英语。他从前的两部小说乃至都是用法语写的,个中一部叫《在路上》(Sur le chemin,2008年魁北克Gabriel Anctil创造了该手稿。虽然与英语成名作同名,这部法语短篇实在是未揭橥的小说Old Bull in the Bowery的雏形——译注),这两部今年都会出英译本。扬·马特尔也是说法语的加拿大人,选择用英语写作;南茜·休斯顿则是英语母语、选择用法语写作。
本日有一批母语非英语的作者用英语写作,比如艾莉芙·夏法克的母语是土耳其语,纳迪姆·阿斯拉姆的母语是乌尔都语,加里·施特恩加特和鲍里斯·费什曼的母语都是俄语,李翊云和郭小橹的母语是中文,亚历山大·黑蒙(Aleksandar Hemon)是波斯尼亚人,二十多岁游历美国时恰好碰上家乡爆发战役,于是他滞留在美国,花了三年韶光用英语写了第一部短篇集。米兰·昆德拉是捷克人,用法语写作;塔哈尔·本·杰隆、雅斯米纳·卡黛哈和阿敏·马卢夫都是母语阿拉伯语、用法语写作。
当我问基洛维奇为何用英语写作,他给了几个缘故原由,情绪的、文学的——但最主要的还是商业缘故原由。他成长于铁幕时期,一贯以为英国和美国代表自由,这刺激他遍览英美文学经典。不过最关键的是,他对我说:“如果你想当国际作家,就必须用一种国际通用的措辞写作。现在英语便是新环球通用语。”
当然他是对的。一想到英国图书市场的翻译作品少得可怜——仅占百分之三,我们很难怪他功利。但在措辞守旧主义者训斥这会威胁措辞多样性之前,值得提醒他们这也并不是新征象。
五百年前,一种截然不同的通用语开始盛行:那便是拉丁语。为了谄媚最广泛的读者,托马斯·莫尔用拉丁语写了他最有名的著作《乌托邦》(1516),这书在他被处决后好几年才有了英文版。莫尔并非独行侠,与他差不多同时的弗朗西斯·培根也用拉丁语写作,还有霍布斯、笛卡尔、弥尔顿和斯宾诺莎。
即便将来肯定会有越来越多的作家选择用英语写作,但小语种爱好者还算幸运,由于用外语写作毕竟总是个别征象。作家爱怎么写都好,只要他们别用环球语(Globish,母语为非英语的人用的一种大略英语,该措辞仅包含最常用的词和短语,多用于国际商务会谈——译注)写小说就成。哪怕你是贝克特式的极简天才或是纳博科夫式的华美天才,恐怕也没法用这种措辞写出一部精品来。
(盛韵 译)
录入编辑:王建亮
更多阅读:
浙江某乡众筹80万修古道 认筹者没有回报只有风景
博物馆“变形计”:从文物宝库到创意试验场
咖啡、文创、图书 逛书店到底逛什么?
马连良偷师余叔岩 在余宅墙外从夜里两点站到五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