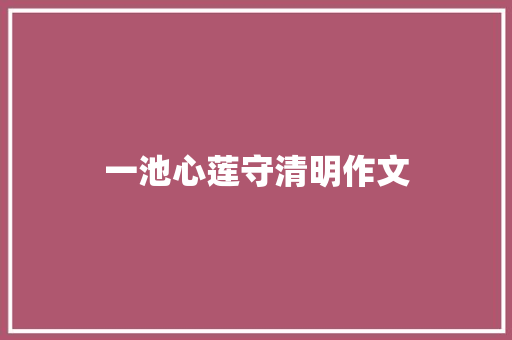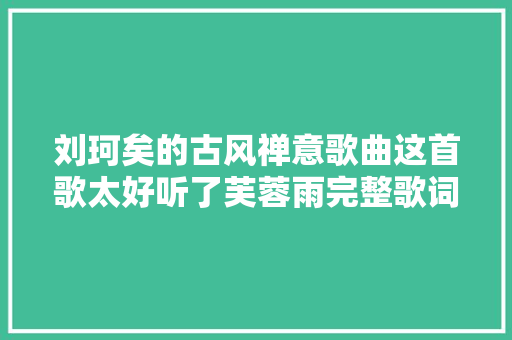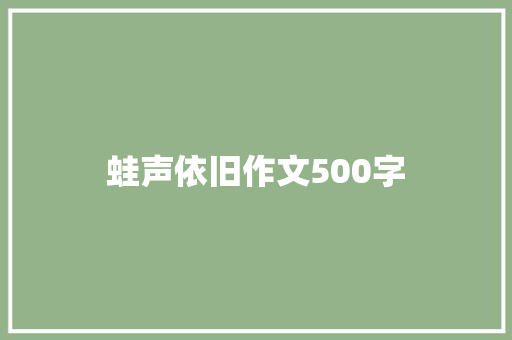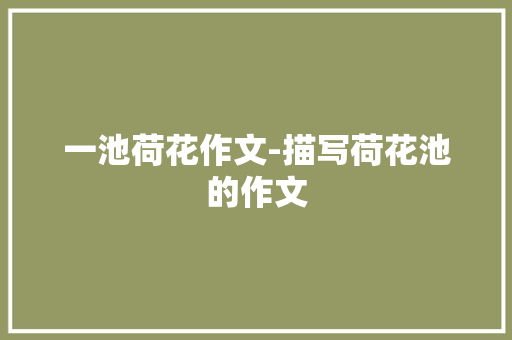附:《芙蓉雨》歌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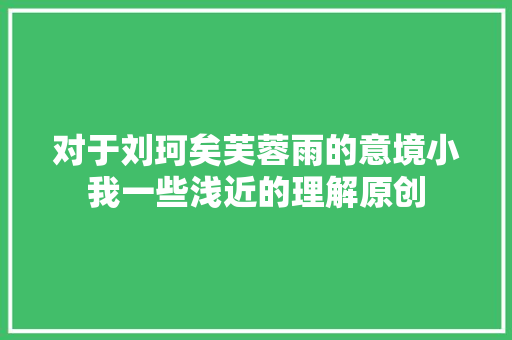
藕花喷鼻香 染檐牙
惹那墨客纵步随她
佩声微 琴声儿退
斗胆了一池眉叶丹砂
画船开 心随他
谁不作美偏起风沙
倚蓬窗 月色轻晃
偶闻得渔翁一席话
(试问)多一份情又怎地
站在别人的雨季
淋湿自己空弹一出戏
空望他 功成名就又怎地
豆腐换成金羽衣
岂不知你已在画里
画船开 心随他
谁不作美偏起风沙
倚蓬窗 月色轻晃
偶闻得渔翁一席话
(试问)多一份情又怎地
站在别人的雨季
淋湿自己空弹一出戏
空望他 功成名就又怎地
豆腐换成金羽衣
岂不知你已在画里
多一份情又怎地
站在别人的雨季
淋湿自己空弹一出戏
空望他 功成名就又怎地
豆腐换成金羽衣
岂不知你已在画里
这一搭 莲蓬子落地 几次迷
首先声明一点,我不懂音乐,只喜好音乐,喜好是一种觉得,来的自然,行的从容,重点在于享受,关键是没有束缚,也没有包袱。以是敢在这里大放厥词。
先说一下歌手刘珂矣,我不想对她的外面妄作评论,这也是对别人最最少的尊重。俊秀和俏丽是两个观点,俊秀是纯挚的形体描述,最大的仇敌是岁月。俏丽却是一种气质,大略的说便是给人的一种“净水出芙蓉”的印象,却又永久是那种“只如初见”的觉得,始于第一眼的寻觅,也终于第一眼的回顾。没有比拟,不需缘由。
然后我要说一下歌曲的创作。从来没有机会面对面的和一个音乐人聊过这个问题,也因此这个问题一贯困扰着我。我想歌曲的创作无非有两种情形,一个是“先曲后词”,一个是“先词后曲”。至于“先曲后词”,我个人认为这种情形是少见的。一首音乐首先依托某些乐器把意境演绎出来,然后才能引起某些音乐人(词作者)的共鸣,继而“闻者有其言”,变成一首流传甚广的歌曲。这种情形不是没有,而是很少。比如曾经风靡一时的歌曲《太多》,它的旋律来源于大提琴家杰奎琳▪杜普蕾演奏的《殇》。这算是比较成功的案例了,但是如果你在听过陈冠蒲演唱的《太多》之前就曾被这首大提琴曲深深的迷恋过,我想你不但没有冲动和惊喜,乃至会以为很失落望,由于这首改版演绎的歌曲完备没有把原曲要抒发的情绪和意境表达出来。我推测不是“先曲后词”另一个更主要的缘故原由是:历史传承下来的乐曲保有量太少,如果大家都是随着旋律去谱词,那么我们的音乐天下就太单调、太匮乏了,我们这些亟待着新鲜音乐给养的“爱好者”们岂不是活活饿去世了。有人会说,那些随处颂扬的“宋词元曲”不正是“先曲后词”的经典案例吗?我想说,“词”倒是随着岁月的流转不断的推陈出新了,乃至大有“长江后浪推前浪”之势。但是“曲”呢?或许早已经不能再叫做“曲”了,剩下的只是生硬冰冷的格式罢了,从某种意义上说,叫“八股词”或者“八股曲”更得当。如若是我们还能从某些洞窟或坟茔中发掘出某些残缺不全的曲调,再把那些经典传颂的词曲按照原来的曲调(词牌或者曲牌)有板有眼的演绎出来,估计也是两败俱伤。原曲作者或者词作者如果都能同时听到这首所谓的“歌曲”的话,我想他们肯定也会狂吐不止吧。
因此我认为,大部分歌曲的创作还是“先词后曲”。有了一篇至善至美的诗文,然后勾起我们一段至真至美的回顾,再开释出我们珍藏在心底的那份铭心刻骨的情绪,末了利用上我们得心应手的专业知识,一首有血、有肉、有灵魂和骨骼的歌曲就产生了。我预测,音乐人创作歌曲便是把歌词、情绪和旋律领悟在一起的过程。就像我们创造一个人一样,歌词是骨架,旋律是血肉,情绪是肌肤,然后再通过歌手的喉咙授予他丰富的神态和表情。当然,塑造是个相互适应的过程,骨骼(歌词)太过分明了,就要进行适当的圆润;肌肤(情绪)太过细腻了,就要进行合理的裁剪。以是,一首好的歌曲,你单把歌词拿出来粗略的看,很完美。但是禁不住细细考虑,有些词句乃至不符合措辞逻辑和习气,这是可以理解的。就像古人诗歌中常用的“兮”字,语文老师说是为了表达某种情绪,我以为便是为了唱诵的须要,当然它也能增加情绪的长度。比如,我们总能从“我想你啊!
”中读到比“我想你!
”更加绵长和畅快的觉得。
我为什么要啰里啰嗦阐明这么多呢,由于我以为我们在试图理解刘珂矣的词曲时,不要过分追求细节。我们只是考试测验着经历和刘珂矣当月朔样的心境和情绪,从而使我们更好的理解歌曲和刘珂矣本人。我们只是想着远远的望着,有如梦境和诗画一样平常的刘珂矣挽着她的歌曲从面前逐步经由,只是安静的欣赏,不打扰,也不惊醒梦中的自己。
下面步入正题。我以我浅近的理解、粗糙的情绪和笨拙的笔触,阐述一下本人的一些感想熏染。不喜勿喷。
“藕花喷鼻香,染檐牙。惹那墨客纵步随她。佩声微,琴声儿退。斗胆了一池眉叶丹砂。画船开,心随他。谁不作美偏起风沙。”这一段向我们描述一场俏丽的重逢。假设主人公是珂珂(暂且这么称呼吧,珂珂比刘珂矣更适宜意境)。韶光该当是心情和温度都一样炙热难耐的六月,地点是江南某个水乡,芙蓉遍池,雕樑画栋,风景如画的湖边公园。珂珂坐在画船上,玉指轻操琴弦(该当是古筝吧,这样才应景),琴声与岸上的蝉鸣百无聊赖的轻和在一起,琴声越是急匆匆,内心愈是暴躁,但是珂珂又不敢停下来,由于她心里清楚,一旦回归于宁静,内心就更加难以平复。此时,能够梳理自己凌乱如麻心情的,唯有遇一知音,对席而坐,打愉快扉,与之倾诉。而正在此时,岸边的回廊里适值多了一位“翩翩美少年”,只见他,轻摇玉扇,峨眉轻锁,面对一池荷花若有所语。似惊叹,似感概,仿佛正轻吟诗篇,诉与芙蓉听。举止间透露出一种令人难以谢绝的优雅和魅力。正所谓“才比子建,貌若潘安”。珂珂也是看得着迷了,琴声溘然变得凌乱无章。这恰好引起了公子的把稳,他溘然将目光转向画船的方向,腰间的玉佩和喷鼻香囊轻轻的触碰在一起,微微作响。同样是充满渴望和深情的两缕目光就这样不期而遇了。珂珂顿时方寸已乱,琴声也骤然停了下来,两人隔水相望,脉脉含情。眉目之间只剩下相见恨晚、两情相悦的倾诉,一池如画的风景也瞬间失落了颜色。怎奈天公不作美,风雨忽来,画船开动,彼此的身影在越来越远的间隔里逐渐模糊。只可惜,最美好的相遇总是在不经意间就发生了,残酷的是,没等你来得及细细体味,就又瞬间失落去了,只剩下干瘪的影象,在漫长的岁月里,一点点的侵蚀和折磨自己。
这样的情境是美好的,也是痛楚的。我写过一首诗,也是描写这种情境的,只是和珂珂的恰好相反,岸上是仕女,船上是公子。拿来和大家分享一下,见笑了。
过客
你是桃花坞旁,杨柳堤下,身披彩霞,脚履落英,待嫁装扮的少女;
我是乌篷船上,琴瑟声中,独酌自饮,愁肠寸断,行色匆匆的过客。
你用婀娜羞却散落在水中干瘪的桃花,
我用哀愁嘲笑缭乱在风中轻浮的杨柳。
你的眼里浸渍的全是泪水,
我的心里侵蚀的只剩忧伤。
你朱唇未启,灵雀之音已在我耳旁萦绕不散,
我仰天长啸,鸿鹄之慕安能抵达你优柔的内心。
你峨眉轻挑,鼻翼微浮,无情卷走一江的倾慕,
我捶胸顿足,眉头紧蹙,渴求赠你一池的爱恋。
你渐行渐远,飘渺融化了罗衫,
我愈奏愈急,琴声沸腾了思念。
“倚蓬窗,月色轻晃。偶闻得渔翁一席话。(试问)多一份情又怎地,站在别人的雨季,淋湿自己空弹一出戏。空望他,功成名就又怎地,豆腐换成金羽衣,岂不知你已在画里。这一搭莲蓬子落地,几次迷。”
这一段描写了珂珂在偶遇之后极其繁芜的心情。歌词里的“空望他”的“他”我以为有两种可能。一个是刚刚偶遇的“公子”,一个是珂珂的“旧情人”。这个选择很主要,决定了全体歌词的意境。如果是刚刚偶遇的公子,由于之前并不相识,珂珂想表达切实其实定是“要不要(和偶遇的公子)相识?要不要为了幸福去主动捉住这场缘分?”。如果是“旧情人”,那么珂珂该当是“触景生情”,由于这场偶遇,想起了曾经的某段感情和某个人,刚刚偶遇的公子,也算是身披“金缕衣”功成名就的成功人士了,碰着“我”尚不能把持情绪,只是“一壁之缘”就想入非非、跃跃欲试,遐想到“旧情人”,一旦他功成名就,我是不是也会被绝情的抛弃,成为那个“画里”的人呢?以是,歌词中的“他”如果是“旧情人”,那么珂珂该当表达的是“要不要等(旧情人)?他会不会变心?”这样的意境。这也恰好回应了上文中珂珂为什么心烦意乱的一个人在画船上操琴的情景了。由于她对和“旧情人”感情不足自傲,不足武断。对自己将来感情的归宿出息未卜,茫然而不知所措。
结合高下文,我更方向于“他”是“旧情人”这个选项。下面我推测下这段心里描写的详细内容:风云骤起,又瞬间消散,仿佛是看不惯这一场风花雪月的缘分,又像是故意摧残自己,让自己本来就破碎不堪的情绪散落一地。珂珂倚在画船的蓬窗前,心绪就这样在“偶遇”和“陈年往事”之间来回的徘徊。不知不觉中,天色渐晚,月上柳梢头。珂珂全然忘却了韶光在缓缓的流逝。这统统让坐在一旁的渔翁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他深知感情的纠结岂是一两句话就能让人释怀的,他自己尚不能做到“众人皆醉,我独醒”。于是,他只是无奈的摇了摇头,然后喃喃自语道:“唉,感情这种东西,多一分沉重,少一分洒脱。不要总以为自己付出了,便可以得到。不要总活在抱负里,心甘情愿的编织着只有自己存在的梦想,还乐此不疲的一个人陶醉,难道你不知道感情是两个人的事情,只是一个人默默的付出,到头来只会让自己被半夜惊醒的泪水浸湿。如果至心爱一个人,就不要一味的抱负和等待,无论他贫穷与富有,只求拥有现在,享受当下。感情怎能耐得住韶光的煎熬?只怕真的等到他功成名就的那一天,你也成为了别人影象中的画卷了。就像这湖水中的莲蓬一样,瓜熟蒂落,一捧莲子又能有几个修成正果,来年长成为亭亭玉立的出水芙蓉呢?”。
末了,我想针对吧友的一些见地表达一些不成熟的意见。有吧友认为刘珂矣是禅境音乐的代表人,不应该有过于儿女情长的意境在里面。我想说,禅境不即是禅,禅不即是道,道不同于佛,纵然是佛,也没有哪条规定不能食人间烟火。如果你涉及过佛教故事,你会创造,里面也有很多儿女情长的事情。各种宗教的宗旨便是让人积极向善,面对挫折和困境无畏而豁达。至于戒律,我认为是修行到了一定程度,自然而然形成的人生不雅观。如果反过来,先行戒再修行,我以为违背神佛的意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