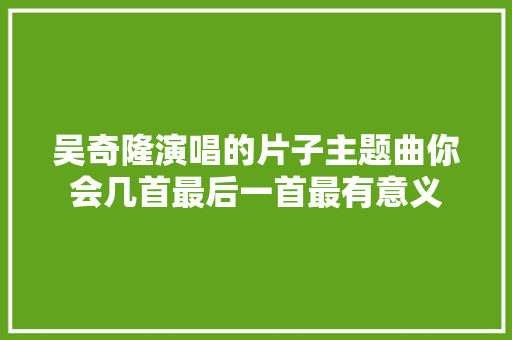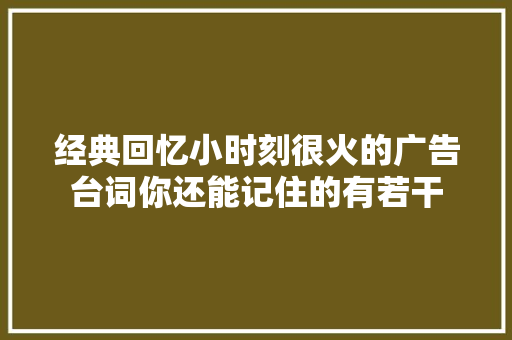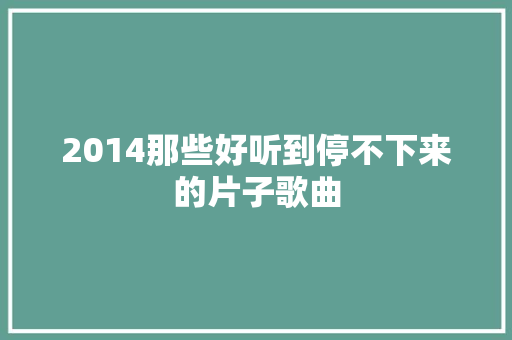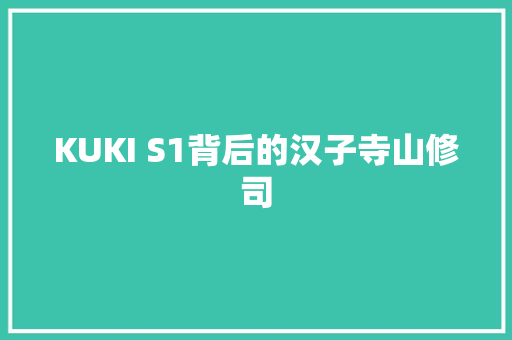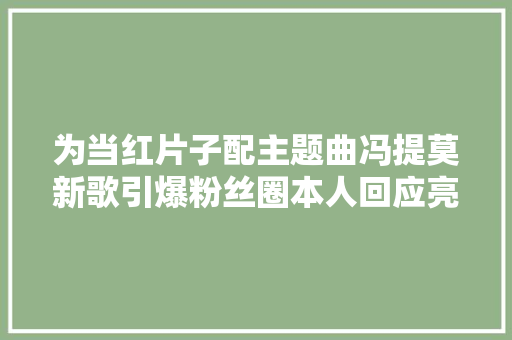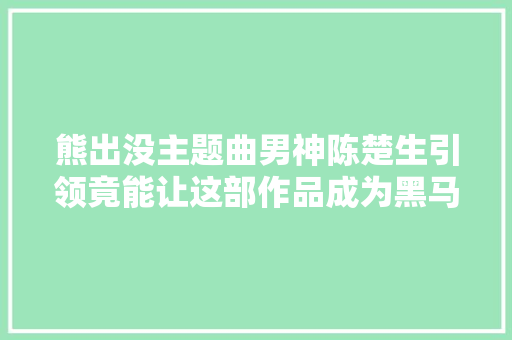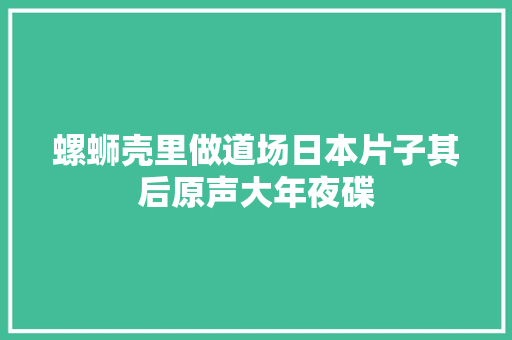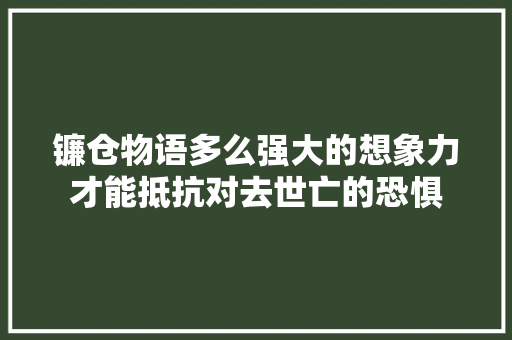电影,如同一条大河,奔驰不息。
20世纪70年代出生的人,险些都是看着电影终年夜的。数不清的黑白老电影、风靡一时的《大众电影》杂志、精彩的中外译制片原声录音剪辑、泛黄的电影连环画……这些东西,曾经与我们如影随行,承载了多少童年影象。电影讲述的家国、日月和山河,不知不觉形塑了这一代人的人格、气质和情绪。

电影于我,犹如故乡,同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1975年的夏天,在青海天峻县的草原,部队为唱样板戏搭建临时舞台,露天放映了《闪闪的红星》,这是我影象中看过的第一部电影。这部电影险些包含了小朋友喜好的所有元素:故事引人入胜、人物维妙维肖、画面色彩通亮,还有精彩的“斗地主”主题。看完电影,父亲用修地窖的木头边角料为我做了一把红樱枪,母亲教我学唱《红星照我去战斗》和《红星闪闪放光彩》。我一拿起枪,唱着歌,急速精神抖擞,以为自己便是潘冬子。
20世纪80年代,我回到上海念小学,家住淮海中路武康大楼下的1950弄。早上去菜场买菜,常能看到孙道临、黄宗英等电影明星;放学后,去常去武康路看达式常和梁波罗,那里有上海电影制作厂的演员剧团;还会途经高安路的建安公寓,上官云珠曾那里一跃而下,喷鼻香消玉殒;当时,宁静的西区到处住着电影人,年长一点的邻居见告我们,夏天纳凉,弄堂口走过的还有赵丹、白杨和冯喆等,在这里碰着大明星,一点也不稀奇。也是在这条弄堂里,挤在12寸电视机前,儿时的我看了这一辈子最多的黑白老电影,一遍遍重温《出生入死》、《马路天使》和《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
中学时期,我对电影的认识渐趋理性。在番禺二中,我加入了学校的影评小组,开始学着用笔墨评说电影。在《小花》中感悟“意识流”技法,在《城南往事》中体味“散文化”叙事构造,在《庐山恋》中不雅观察对位式演出,在《高山下的花环》中寻觅海派现实主义,在《少林寺》中见识武打类型电影……,80年代的中国电影像喷薄而出的朝阳,像山间奔涌的溪流,电影是文化启蒙的第一缕光,映照在我们这些孩子的心中。也正是那个期间,我们打仗了以《流浪者》、《大篷车》为代表的印度电影,领略到南亚次大陆的他乡风情;认识了以《人证》、《追捕》和山口百惠系列为代表的日本电影,触碰到来自东瀛的影星热度;重温了《简爱》、《尼罗河上的惨案》、《王子复仇记》为代表的欧隽誉篇,聆听到上海电影译制厂“黄金一代”的大音绝响,电影为我们打开了天下的大门。
最难忘确当属大学岁月。90年代初,复旦校园社团多彩、热烈而旷达,中文系作为文科系首,素是学生社团的活力之源。由于主持复旦影视协会的机缘,我能以更专业的角度,不雅观察和欣赏中外电影。3108教室的电影文化讲座、相辉堂的新片首映式、电化教室的专题录像周、学生社团的油印小报……,通过这些媒介,我广泛打仗了从法国新浪潮、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德国新电影到中国台湾乡土电影等多种流派,更以学术研究的办法,阅读了大量奥斯卡获奖电影和中国喷鼻香港商业片。宿舍熄灯后,从巴赞、杨德昌聊到小津安二郎,都是我们夜谈的“热门话题”,不知共度多少不眠之夜;在电化教室,不知看坏了多少盘录像带。至今,我仍记得1991年的深秋,电视剧《围城》在复旦首映引发的轰动,连映三天,同学们差点把文科大楼电化教室的门挤破。映前,黄蜀芹导演把十盘录像带交给我,我脱下外套,把它们小心翼翼地包好,绑在自行车后座上,从漕溪路一贯骑到邯郸路。彼时海内影视界有个好传统,导演们拍完新片,每每会把作品拿到大学校园试映,听取大学生的见地。在相辉堂,影视协会先后组织了张艺谋导演的《红高潮》、白沉导演的《落山风》、滕文骥导演的《黄河谣》和李歇浦导演的《开天辟地》等影片的首映,请谢晋导演来给大家讲斯皮尔伯格及其作品,还自办了复旦校友的电影展映,出版了校园影评学术刊物《燕园影谭》。
大学毕业,我的论文方向选定了电影。因电影之缘,我被论文辅导老师周斌推举到电影人汇聚的《文申报请示》,成为一名。在那里认识了梅朵、徐春发、汪澜等一批我十分敬仰的前辈,更有幸和文新报业集团的许多精良青年才俊共事。在十三年的媒体生涯中,我深受这张人文大报的浸润,饱吸儒雅、思辨和忧患之传统,辗转海内部、文艺部和政法部等多个部门,跑遍了全国三分之二的省份,饱览了海内险些所有的戏剧曲种,视野从电影拓展到文旅家当,笔触从新闻通讯延伸到调查评论,主题从人文深入社会经济,唯独未曾改变的是: 一颗小儿百姓心。用它,不仅看电影,也看天下。(金涛)